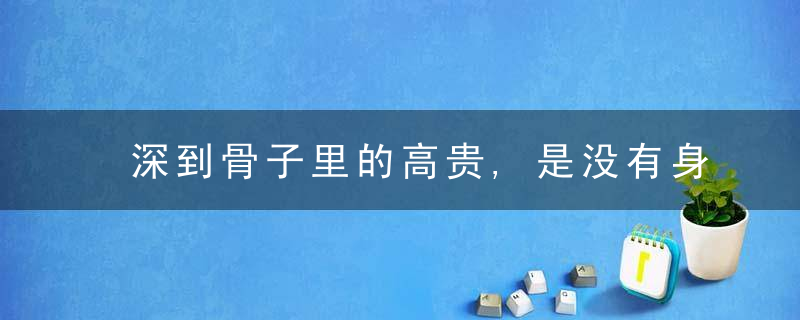季羡林

谈起季羡林,大约所有人都不会感到陌生。
他是著作等身的学者,活到98岁高龄,精通12国语言,通晓14门学科,在梵语、吐蕃语等研究领域的造诣少有人企及;
他一生笔耕不辍,有两千万字的作品留存于世;
他提出“教育必须破除重理轻文的理念”,让莘莘学子尤其是文科人才受益终生;
他推崇的“天人合一”“天下大同”“文化自信”,至今仍不过时。
在季老先生的一生中,刻着“天道酬勤”,也刻着“高洁自守”。
他是一位大师,也是一个传奇。
1
寒门出贵子
季羡林幼时家贫,6岁时,父母把他过继给经济条件较好的叔父,由叔婶抚养长大。
叔父见他天资聪颖,便送去读私塾,私塾里的国文老师是前清状元,这让季羡林从小就接受到最好的精英教育。
考大学时,季羡林成绩优异,只报了清华、北大,被两所顶尖高校同时录取,他选择了清华,专修德文。尔后,被派往德国留学。
他原本打算在德国镀两年金就回国,没想到遭逢二战,阻断归途,季羡林回不来了。
这一待,就是十一年。
在此期间,音讯隔绝,国内的亲友甚至不知季羡林是生是死。
他的老师上了战场,他就跟着学识渊博、精通各个语系的师爷,心无旁骛,苦学11年。
季羡林学生证
季羡林形容那时的自己,
“无家无国,无可依傍”。
由此观之,季羡林儿时受到传统国学教育,少时深得西方文化浸染,深厚的学养来自博古通今,中西贯通。
在他的生命中,没有一年是被浪费的,最好的青年时光,一直或主动、或被动的处于求学状态,并始终接受最优质的教育。
因此,人们说
“百年之内不会有第二个季羡林。”
正是这些传奇经历,成就了独特时代下无法复制的泰斗大师。
2
我放下过天地,放不下你
因6岁离家,寄人篱下,季羡林养成拘谨内向的性格。
读大学时,亲生父母相继去世。
从辞别母亲,到母亲离世,其间十几年,他只见过母亲两面,这在季羡林心中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直到耄耋之年,谈及母亲,他泪眼婆娑:“这世上的任何荣誉地位,都比不上在母亲的身旁更加幸福。”
过早承受分离,没有享受过父爱母爱,童年时几乎没有体验过亲密与依恋,这使季羡林的感情道路十分坎坷。
高中毕业后,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季羡林与长辈包办的妻子结婚。
妻子没有文化,跟国学修养深厚、渴望精神交流的季羡林毫无共同语言。
这在那个年代是普遍现象,很多文豪才子都放弃了结发之妻,转而寻求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女性,如鲁迅许广平、徐志摩陆小曼、郁达夫王映霞等。
但季羡林始终没有逾矩。
青年季羡林
也不是没有遇见过怦然心动的女子。
在德国时,年轻的季羡林与房东女儿情投意合,书稿、文件总是女孩帮他用一台老式打字机打出来,整整齐齐地放在书桌上。
但此生,他们只牵过一次手,再无其他。
季羡林生于礼仪之乡山东,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的洗礼,对妻子怀有强烈的责任心,纵有过心动,却恪守底线,坦荡忠诚。
感情本就是求仁得仁的事。
战争结束,季羡林离开德国,房东的女儿终生未嫁。
若干年后,是否会有一个白发苍苍的德国女子,守着圆桌,桌上有一台老式打印机,凭吊往事呢?
季羡林写道,
“所有的幸福、美与爱,都与我无关。”
房东女儿伊姆加德
回国后,季羡林把妻子从老家接来北京,但因感情稀薄,两人一个住客厅,一个住卧室,就这样住了一辈子。
对她,他只知责任,不知爱情。
从季羡林身上,不难看到传统士人君子的精神,尽管留洋多年,骨子里依然固守传统旧道德,用少年时代所学的四书五经约束自己,捆绑自己,不惜压榨个人幸福。
我不知这儒学塑造的士大夫精神是否值得颂扬,但季老先生,大约当真是中国最后一位士人了罢。
3
天道酬勤
放弃了喜欢的女孩,和在剑桥任教的高薪职位,季羡林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迎来了他的黄金时代。
他在北大,教学生、做学问,每天4点半起床,成为燕园亮起的第一盏灯。
季羡林戏称,
“我不是闻鸡起舞,而是鸡闻我起舞。”
他有一张破藤椅,每天中午在此午睡,因他担心睡床太舒服,会睡得太久,浪费时间。
由此,诞生了一幅著名的《三睡图》:藤椅上午休的季羡林,和两只卧在他身上的爱猫,此谓“三睡”。
三睡图
面对世人的敬佩,季老谦逊道,
“我这一辈子,只一个勤字而已。”
他穷尽古今中外做学问,不舍昼夜地与时间赛跑,一辈子勤于求知、勤于教学、勤于研究,是真正的学者。
他用生命创作,曾写下73万余字的《糖史》,堪称鸿篇巨著。
季羡林不是科学家,对科技可以说是门外汉,为何要写研究制糖历史的《糖史》呢?
他说:“我写《糖史》,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与其说写科学技术史,毋宁说写文化交流史。”糖,这一家中必备食品的背后,实则隐藏着一部遍及五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文化交流史,通过研究“糖”在世界传播的过程,便可揭示人类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方面。
而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竟是在季老70岁时开始写的,直到87岁方才写完。
他忘我地求知,甚至忘记了年纪和岁月。
4
牛棚杂忆
从十年浩劫走来,季羡林也曾被批斗。
但与那个时代诸多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季羡林从未心怀委屈、愤懑,他在思想上与彼时的国家保持高度一致,认为自己在二战期间,偏安德国,的确没有在国家最艰难时为国效力,尽管这并非他本意。
这也是季老先生十分独特的思想。
正因如此,他熬过了那段艰苦岁月,没有像其他文人学者,不堪其辱,逝如秋叶。
他写《牛棚杂忆》,说:
“我不传递仇恨,这只是一面镜子。”
阴云密布的年月,季羡林仍未放弃学习。
他每天将一句梵文诗抄在小纸条上,趁没人时,取出翻译,冒着生命危险,顶着政治高压,依然不放弃对文化的执着。
择一事,忠一生。
文革结束,他整理译稿,这就是总共七章、有24000对对句的史诗级著作《罗摩衍那》。
无论在情感、为人、做学问方面,季羡林都坚守着某种士人精神,压榨了自己一切的乐趣,自由,欲念,似乎只为了学术、尊严与精神而活。
顾城有诗,“一个人应当活得是自己并且干净”,季羡林堪当此谓。
他秉持高洁的精神,极端克己,在文坛、在学界、在政界,无论身在何处都受人尊敬。
尽管年事已高,被尊为“国宝”,季羡林仍平易近人,待人谦和。
所有学生到季羡林家中拜访,无论尊卑亲疏,走时,他都会把他们送到门口。
5
高山景行
季羡林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站在时代前沿,窥破大势所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浪潮汹涌,崇洋之风初开,季羡林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劝导国人树立文化自信,切勿“富裕之后骨头却软了”。
他断言,21世纪,东方文化定会重焕辉煌,因为西方追求的“用科技征服自然”,若不加节制,不重环保,必将走向毁灭。
而中国古人从不与自然为敌,倡导无为、和谐、天人合一,绿水青山便是金山银山。
他还提出“大国学”理论,即国学既包括汉家儒学,也包括少数民族的文化,甚至包括国际世界的文化,皆可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这将使地缘政治不再敏感尖锐,天下大同也会消灭战争。
这些不断被时代印证的论断,使季老成为永远的大师。
98岁时,季老辞世,书桌上摊着未完成的手稿。
临终前一周,他还在坚持创作。
一代大师季羡林,他的人生诗意,敏感,坚韧,充满了奇特的矛盾与碰撞,或许这恰是他的传奇之处。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