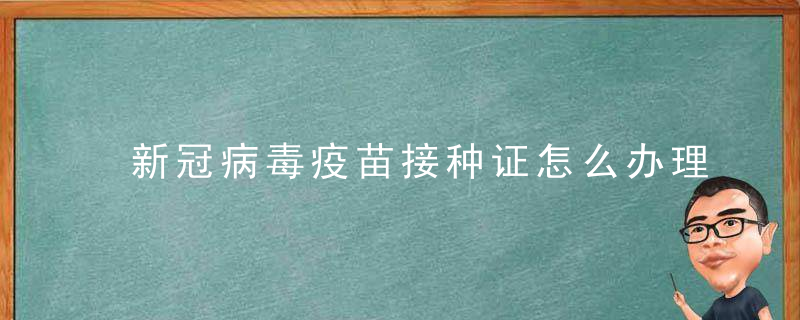那个吸毒狎妓、谩骂元首的民国第一狂徒

阅读全文约需9分钟
那个敢当面谩骂老蒋、被传言贬斥沈从文、
吸毒狎妓的民国第一狂徒
1
一提起刘文典,就称“国粹怪杰”“民国狂徒”。
从刘文典获得的这两项“荣誉称号”,我们或许可以粗略感知到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刘文典学贯中西、满腹经纶,专业素质过硬,但性格很桀骜不驯、行事乖张。有人甚至说出“刘文典一死,中国再无真狂人”之类的话,来形容他的“狂”(大概是那会儿还不认识李敖)。
刘文典的狂,主要体现在三个关于他的“奇闻”上:
在第一个奇闻里,刘文典曾狂妄地说:“古今真正懂《庄子》的,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就是我刘文典,其他研究《庄子》的人加起来一共半个!”
刘文典的第二个奇闻,与老蒋有关。
说是1929年,安徽大学生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老蒋让当时身任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到南京解释此事。刘文典对老蒋的措辞十分不满,跟他起了言语冲突。
老蒋一怒之下,甩了刘文典两耳光。刘文典马上飞起一脚踢到老蒋的肚子上,疼得老蒋直冒汗,老蒋当即下令把刘文典关了七天。
刘文典的第三个奇闻,与沈从文有关。作为国学大师,刘文典向来看不起新文学、新文化,自然也从不觉得沈从文写的东西哪儿好。
抗战开始,北大、清华、南开大学南迁到了长沙,后来又去了昆明,“中国大学里的珠穆朗玛”西南联大横空出世,刘文典、沈从文当时就在联大教书。
那时,昆明时常被敌军轰炸。
有传闻说,有一次警报响起,刘文典与大伙一道跑了出去,跑半路突然想起他最尊敬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就跑回去找到在路上视力不佳的陈寅恪,架起他就向外跑,一边跑一边喊:“保存国粹要紧!”
刘文典看到沈从文也在人群里,便上前讽刺道:“陈先生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可是你什么用都没有,跑什么啊!”
在西南联大野史上,还有一则关于刘文典看不惯沈从文的奇闻。说是学校想给沈从文评教授,但刘文典反对,甚至说出“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沈从文只配拿4毛钱”之类的话来。
还有一种版本,说是联大有一次开会讨论沈从文是否能晋升教授职称,刘文典当场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成了太上教授?”
这三则奇闻,把刘文典的“狂”体现得淋漓尽致,以至于让人觉得他已经不是狂,而是没教养。
为此,我专门查询了相关的资料,验证这三则奇闻的真实性,却发现只有第一则奇闻有来处。刘文典对《庄子》的研究,当时无人能出其右。
与老蒋会面时是怎么回事呢?刘文典见了老蒋,称他为“先生”而不是“主席”,就已经引起老蒋不快。
老蒋一再追逼刘文典交出肇事学生,刘文典毫不屈服,还怒斥蒋为“新军阀”,老蒋随即严令随从陈立夫将刘文典送交公安局关押。
事后,在学生、全国知名文化人的抗议下,老蒋把刘文典放了了事,只附加了一个条件:即日离皖。
看得出来,蒋对刘文典简直是厌恶之至了。
刘文典与老蒋起冲突的版本众多,但可查账的版本均只有言语冲突,因此,刘文典怒踢老蒋甚至因此导致他与宋美龄无法生育,应该是典型的“以讹传讹”了。
刘文典(说这话时还没到被批斗的时候)也说过:“我一生除了被一位老和尚打过,没有谁敢打我。蒋虽然把我关进牢房,并不敢动手打我。”这也从侧面证实了蒋并没有动手打他耳光。
西南联大遇空袭时,刘文典当面贬斥沈从文,更是无中生有的事。所有文字记录的传闻版本,都只是“听说”,并没有证人。
事实上,刘文典虽然对新文学、新文化意见很大,但跟沈从文的私交并不很差,甚至还曾邀请沈从文夫妇到家里吃饭。
为什么坊间会流传这么多关于刘文典的狂傲故事?很有可能是后人很欣赏刘文典的“狂”,所以虚构了几个传闻。
这些传闻看起来比较符合刘文典的“狂性”,又能满足大家的猎奇心理,让人津津乐道,所以听者深信不疑,一传十,十传百,传到最后大家都以为是真的了。
刘文典有蔑视权力、高官的一面,哪怕老蒋他也不放在眼里,倒应该是真的。
当年,老蒋去安徽大学视察,提前给刘文典发了通知,刘文典随手就把通知扔了。
老蒋来的那天,他甚至跑去打麻将,结果老蒋来了以后,发现安徽大学无人夹道迎接他,很是恼怒。
这就不难理解,后期两人再见面时,何以会起言语冲突了。
2
今天的人们,可能不知道刘文典到底有多牛。
他通晓英、德、日多国文字,后来见日军侵华,立志终身不讲日语。
他学贯中西,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文史大师。他讲历史,能从先秦时期一直讲到明清近代,能从希腊讲到日本,如数家珍。
他研究古代文学,拥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学生们都很爱听他的课。
讲《红楼梦》时,刘文典说:“凡是别人讲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讲过。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
刘文典的确是有这种实力的人。
《红楼梦》元春省亲一节,贾政带着贾宝玉给大观园各景所题匾额,匾额做好后让元春过目。元春唯独在看到“蓼汀花溆”四个字时提了点意见,说是“花溆”二字就好,又何必要加“蓼汀”。
很多人看到这里,完全看不出曹公多写这一笔有什么深意,唯独刘文典是这么分析的:“花溆”的“溆”字,形似“钗”,音似“薛”;而“蓼汀”二字,反切即一个“林”字。说明元春更喜欢宝钗,而不是黛玉。
反切是古人的一种注音方法,有一个基本原则是:把一个音节分成声、韵两个部分,然后第一个字的声母和第二个字的韵母组合在一起。比如“蓼汀”的读音是liǎo tīng,取L和in,就成为了“林”。
我就问你:刘文典能把《红楼梦》解读到这种程度,你服不服?!
刘文典教学生写文章,没什么长篇大论,只总结出“观世音菩萨”五个字。学生们听得如同云里雾里,而他解释说:“观”乃多多观察生活,“世”乃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乃讲究音韵,“菩萨”则是要有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
这样的解读和指点,玄不玄妙?
刘文典讲课,还最善于自嘲。
有一回正讲着课呢,刘文典忽然愤怒地说起人间的不平等现象,比如说有人坐车,有人拉车。学生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下课以后看他坐上一辆人力车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说的那个坐车的人正是自己。
放到现在,刘文典的课程绝对是门门爆满,几万块一节课估计也有人愿意去听啊。1
3
刘文典到西南联大之前的履历,比较简单。
他是安徽人,出生于1889年,和陈 独秀是老乡,早在1907年就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他两次赴日本留学,并曾担任孙中山秘书。
▲刘文典本尊
1916年,他从日本回国后,进入北京大学任教,研究诸子著作,学术成果引人瞩目。
1927年,他担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后来因得罪老蒋去了北京,在北大、清华执教。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刘文典未能及时离开北平,日军得知他曾留学日本多年还精通日语,对他实施威逼利诱,希望他能任伪职,甚至曾让做了汉奸文人的周作人来劝他,结果周作人也被他骂走。
软的不行,日本人对刘文典来硬的,两次派人抄他的家。刘文典和夫人身穿袈裟,怒目而视,但就是不搭理日本人的问话,说“以发夷声为耻”。
▲左一为刘文典夫人
那一年底,刘文典辗转了千里,从天津走海路到了香港,再从香港去到越南,再从越南去到云南,辗转了几个月才来到西南联大。这一路旅途奔波,不知道他经历了多少风浪、困难和危险。
据说当他赶到西南联大时,全身上下只剩一身破衣裳。看到联大校园里飘扬的国旗时,他忍不住泪流满面。后来,他说当时他为了能和西南联大的同事、学生汇合,“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
4
刘文典也不是对所有人都很狂的,也不是没有缺点的。
他一生敬仰陈寅恪,称之为“教授中的教授”。在陈寅恪面前,他立马化身“小粉丝”,常说陈寅恪才是大拇指,而自己只是小指头。对冯友兰,他也是真心佩服的,所以他曾说过这样的话:“(西南)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算半个,我算半个。”
刘文典有三个很狂的老师,一个是同样很狂的陈独秀,一个是清末狂人刘师培,另一个是有“章疯子”之称的民国狂人章太炎,对老师们他一直很尊敬。
刘文典与陈独秀、刘师培都是因为政见不同而慢慢疏远(刘投靠袁世凯,而陈后来建了个新政党),但刘文典却依旧感念恩师们的恩情,听闻陈独秀的死讯时他哀叹不已,刘师培去世时他回乡扶柩,并苦心搜索先师著述替他出版。
打过刘文典的老和尚,是北京西山香山寺藏经阁里的一个住持。那时,刘文典在清华教书,想弄清楚一些佛学问题,就跑去香山寺查阅资料。
有一回太困了睡着了,忘记了借阅规矩,还在别人床上睡着了,导致住持用扫帚“打”了他一顿。两人也因此不打不相识,成了好朋友。
刘文典后来回忆此事说:“我的脑袋虽然不太高贵,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
面对一个说他失信的老和尚,刘文典甘愿挨打;面对老蒋那么位高权重的人,他不谄媚、不迎合,一言不合就开怼。
看起来,刘文典颇有“竹林七贤”之风,但实际上,在生活所迫的年岁,他也曾干过给老蒋写贺词的事儿。
当时是1943年前后,抗战尚未结束,全国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民不聊生,西南联大老师们的日子也过得特别艰苦。
当时云南普洱有一个大豪绅听说刘文典精通国学,就赠他银两,请他为自己母亲撰写墓志,刘文典屁颠颠跑去写了,结果回来以后就被联大解雇了。
刘文典被联大解雇,主要是因为他去普洱,一去就去了半年。普洱当地盛产鸦片,而刘文典嗜吸鸦片,还经常下窑子嫖妓,在那边过得乐不思蜀。
去之前,他仅仅跟联大常委蒋梦麟等少数几个人打了声招呼,算是很目无法纪了。闻一多等对他的言行非常不满,联大“掌门人”梅贻琦也觉得他这回做得有点过,不得不忍痛“挥泪斩马谡”。
抗战胜利后,云南主席卢汉的秘书找到刘文典,让他为蒋介石六十生辰写贺表,他也写了。
这两件事,成为了刘文典的人生污点,也让我们看到大师比较不堪的一面。
5
抗战胜利后,联大很多老师回到了北平,而刘文典得罪的人比较多,只好投奔了熊庆来(云南大学校长),留在云南大学执教。
解放前夕,胡适邀请刘文典逃去美国,甚至为他一家办好签证、买好机票。刘文典说:“我是中国人,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新中国成立后,刘文典风光了一段时光。
当时李广田担任云南大学校长,对刘极为恭敬。云南大学定职称时,他是云南省唯一一名一级文科教授,还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届委员,在政协大会上发言,还受到领袖的接见。
1952年,全国上下各大高校开始开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刘文典首当其冲成为被改造的对象。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遭到批斗,此时他已经68岁了。
起初,他还挺硬气,直接跟批斗他的人说:“我不自杀,你们批不死我……我要自杀,也就一种自杀法,炊烟(吸鸦片)慢慢自杀。”
到后来,似乎是被批得身心疲惫了,直接在会上承认自己所有的“罪行”,还强制自己戒掉了鸦片。
交代罪行时,他说:“1950年抗美援朝,我作过国变诗。我认为帮兄弟国家的忙,应有个限制,打起来建设不成了。我抵触的事还多。如开会太多了,填表太多了……现在我感到自己非常空,我全错了。”
如今再看他的认罪词,你会觉得他“净瞎说大实话”。
1958年7月15日,刘文典因患脑溢血病逝于昆明,享年70岁。而之前,他已经被查出来肺癌晚期但拒绝治病,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死于一场病还是死于“自愿慢性自杀”。
钱理群曾这样评价刘文典:他的“狂”是真的。所谓“狂”无非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第一”,把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这门学科就没了!这种“舍我其谁”的狂傲、气概,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的。
刘文典的儿子刘平章谈及父亲,是这么说的:“与狂相比,我觉得他这个人还是比较傲的,相比之下,傲字更准确一点……他的傲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学问是可以传承下去的。所谓的狂就是因为傲,而傲又是因为他有本事。”
现代作家李敖也狂傲,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生平有两大遗憾,一是我无法找到像李敖这样精彩的人做我的朋友,二是无法坐到台下去听李敖的精彩演说。”其实,这样的“梗”刘文典早几十年前就用过了。
说刘文典是“民国版李敖”,或者说李敖是“现代版刘文典”,都非常不贴切,因为李敖完全没法跟刘文典相比。
刘文典的真本事,比李敖多太多;他小节有亏但从不失大节,颇有魏晋名士“嵇康”之风,而李敖在他面前只是一个比较会炒作的顽童。
文章的最后,我很想说一句多余的话:当年,刘文典对蒋不敬到那种程度,蒋也只是关他七天了事。学生和教育界名士一跑出来抗议、说情,就立马把他放了。
据说刘文典当时还很不情愿地出狱,为此还摆了好一会儿谱,说什么“你以为想让我进来就进来,想让我出去就出去的么”。
离开安徽后,他立马去了北京继续当他的教师。可是,到了那个混沌的、走弯路的时代……咱就不多说了吧。
“保钓(鱼岛)运动”进行得比较白热化的时候,我曾想起刘文典于几十年前说过的一席话。当时还是1944年,日本战败前夕,刘文典在《云南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中国战胜日本后如何对待日本的长文。
他说,战事终了之后,我们可以不索取日本的领土、不要赔款,但是有一点却不可不据理力争的,就是琉球这个小小的岛屿(包括钓鱼岛)必然要归还中国,这件事千万不可放松,否则,贻国家后日无穷之害。
▲战后,蒋和美国总统罗斯福
二战后,日本投降,中国果然“以德报怨”,没有要求赔偿,更没有要求割地(美国也不支持中国要赔偿、割地),但是,在英美两国首脑都主张将琉球归还中国的时候,蒋大概是国穷志短,思考了半天后答复道:“我觉得此群岛应由中美两国占领,然后国际托管给中美共同管理为好。”
蒋的目的是不想让美国人觉得中国太贪心,结果,到了现在,果真如刘文典所说,“贻害无穷”。
就冲这点敏锐的洞察力、独到的认知力、超前的判断力以及爱国情怀,刘文典就值得钦佩。
完美的大师是没有的,但大师们无需去阿谀奉承各种势力、不必见到个官员就得点头哈腰的时代是值得怀念和向往的。
全文完
一点碎碎念:
今天的文章,估计很多人不爱看,因为讲的不是热门人物,也没有讲到名人的情感纠葛。其实,不管写什么、怎么写都会被人骂,也顾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