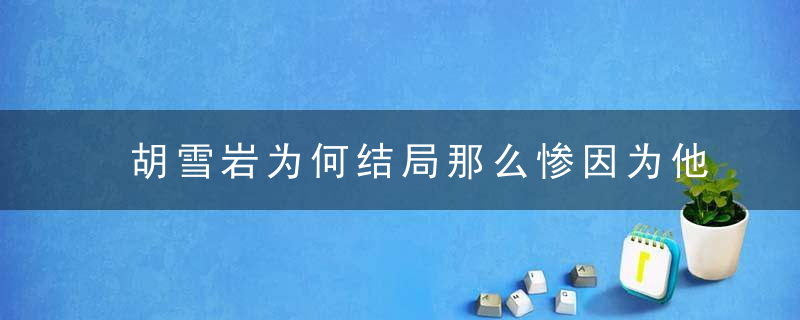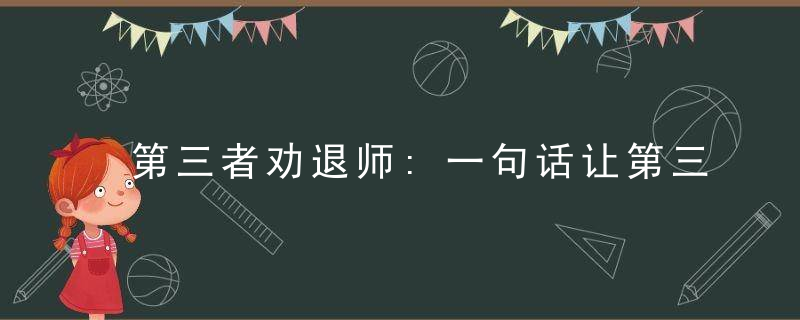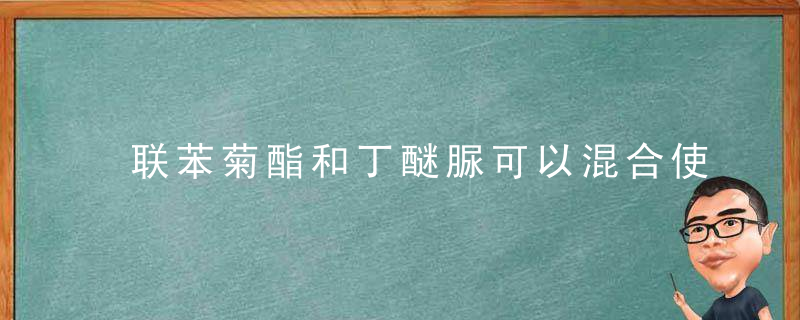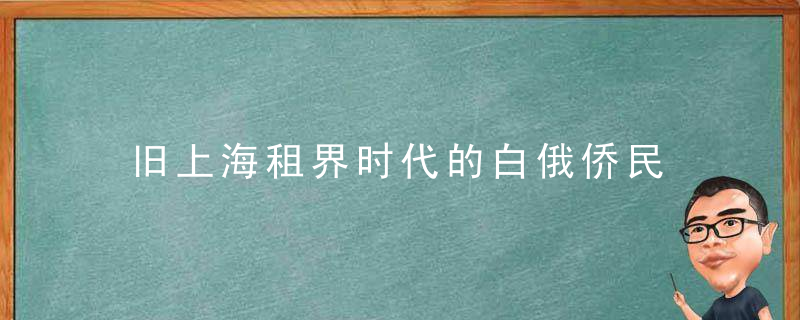左宗棠与樊燮

“宗资画诺,成瑨坐啸”——说的是一则历史故事,宗资与成瑨都是东汉人,宗资官汝南太守,成瑨官南阳太守,二人帐下各有一个亲信幕僚,即范滂[字孟博]和岑晊 [字公孝,晊:音至],所有政务,都交这两个幕僚处分,当时两地流传有歌谣说: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又说: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画诺”又称“画行”,即主管长官在文件上签字表示认可;“坐啸”即闲坐吟咏歌啸。意思是宗资和成瑨只是名义上的太守,平日工作只是圈阅一下文件,实权掌握在范滂和岑晊手中。因此,后人以“啸诺”比喻为官清闲,无事可做。事见《后汉书·党锢传》。
史学家孟森先生论及左宗棠与骆秉章的关系时,开头曾引用过这个典故,要说,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时的情形,与上述的那则历史故事还真的很相似。 ——按清代制度,行政长官每到一处,必聘请熟悉当地情形的文人为幕僚,又称“幕宾”,幕僚是没有编制、没有薪水的,须长官自掏腰包,因此,他与长官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宾主关系。哪怕就是当一个小小知县,也必聘一名钱谷师爷,一名刑名师爷,代县令掌管钱粮收支和案件的审理,平时为长官出主意,当参谋,至于京官,就不须师爷,但大官往往养一帮闲人,这叫“门客”或“清客”,平日与主人吟咏诗词,鉴赏字画,管理庶务等,像清朝咸丰帝宠臣肃顺,他门下就有六个著名的清客,都是湖南人,时称“肃门湖南六子”,左宗棠后来因樊燮一案被诬,“肃门六子”就从中出了力,当然这是后话。 另外,幕僚也好,清客也好,不是普通人可当得的,必须是文化人,甚至是名士,不但熟悉朝章、典故,且熟悉各项法律和案例,只因屡试不售,才去干这营生,所谓“科场失意,退而作幕”。操行不好的师爷,必运用自己身在官场的条件,暗通关节,包揽词讼,教唆长官干坏事,因而称“劣幕”——鲁迅的家乡绍兴,明、清两代,就出了不少“劣幕”,专恃笔杆子坑人,所以,论敌骂鲁迅时,竟也使用了“绍兴师爷”这个贬称。 清朝开国之初,皇帝个个精明,熟知官场底蕴,因此,对于地方官延聘幕僚,制定了严厉的惩处制度,《钦定六部处分则例》有:一,官员纵容幕宾出署结交者,照纵容亲友招摇例革职;二,督抚藩臬接用旧任幕友,令其始终踞一衙门者,照纵容幕友例议处;三,督抚于幕友,务宜关防扃钥,不得任其出署往来交结,若不遵功令[制度]致被参劾,或因事败露,将纵容之督抚治罪。 左宗棠三试礼部不第,在家中闲居,好友胡林翼、郭嵩焘等人一边向湖南巡抚张亮基推荐,一边力促左出山。据史载,左几次拒绝张亮基的邀请,避而不见,张亮基为延左宗棠入幕,竟以抗捐的罪名,扣押左宗棠女婿陶桄,迫使左宗棠出来找抚台讨说法——这比刘备的“隆中三顾”还要有戏剧性。 骆秉章是广东花县人,与洪秀全是同乡,道光进士,鸦片战争时,骆为翰林院编修,从他上疏主战并声援林则徐、弹劾琦善等种种行为看,此人为官正直,交结的也多为正人君子,出任地方官后,在湖南时间很长,自道光三十年出任湖南巡抚,至咸丰二年五月卸任,由张亮基接手,前后共两年,咸丰三年张亮基卸任,他再度巡抚湖南,这次一干就是八年,直至咸丰十年调任四川总督。 骆秉章品质可贵处,就是能知人、用人,且用而不疑,不怕大权旁落,不嫉妒他人有能耐,甚至容忍他人名声盖过自己。其时正逢太平天国轰轰烈烈之时,湖南首当其冲,军务、政务十分棘手,他知左宗棠才干强于自己,聘左宗棠入幕后,大小事情,概由左宗棠一语而决,他则不管不问,很是放心。 有故事说,某次骆秉章在后衙洗脚,听到前面炮声隆隆,急问左右,何事放炮?回答说:左师爷在拜发奏折——巡抚向皇帝奏报军情,奏折交差官出发时,须放炮表示恭敬,因而叫“拜折”。这里左宗棠以巡抚的名义,把奏折都拜发了,身为巡抚的骆秉章事先竟不知情。 又有一则故事说,骆秉章有一擅专房之宠的小妾,弟弟是个粗鄙之人,捐资在巡抚衙门候差,一直没有谋到实缺,小妾几次向骆秉章吹枕边风,要安排弟弟一个差事,骆秉章面有难色,说这事要左师爷开口才成,可据我所知,左师爷铁面无私,只怕不会循情。小妾央之再三,骆秉章无奈,一次趁左宗棠高兴,置酒与左宗棠小酌,酒过三巡,才期期艾艾地说,佐杂官某人,候差已久,是否给他一点事做?左宗棠闲闲饮酒,没有搭理。骆秉章又说,实不相瞒,这人是小妾的弟弟,向我说过多次,实在躁耳,不如随便寻个地方塞进去算了。左宗棠这才说,今天高兴,你何不再宴我以美酒,飨我以佳肴?骆秉章以为有希望,于是又下令,要后面重新置酒备菜,且亲自把盏。左宗棠连饮三杯,然后起身,向骆秉章抱拳一揖说,喝过三杯离别酒,左某告辞了。骆秉章大吃一惊,说怎么这样说呢,这里岂能离得你?左宗棠说,明人不须细说,既然意见不合,便当分手,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何必多说?骆秉章这才明白刚才说错了,连连认错,并说,那句话我收回,今后用人,一任你处分,骆某决不干涉。左宗棠当即慷慨陈词,说眼前局势,十分危急,要维系人心,亟宜整顿吏治,若乱例一开,学样的跟着来,致使小人得意,志士寒心,局面就不可收拾了。骆秉章再三道歉,左宗棠这才算了。 须知这种大包大揽、不徇私情的作风,是要得罪人的,像东汉的“宗资画诺,成瑨坐啸”,其结果就是得罪了地方豪强和宦官,终于酿成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被杀者达几百人,范滂先是被逮,然后被杀。 所以,湖南的官场早有谣言——按清代制度,总督和巡抚有纠弹通省文武官吏之权,因此,总督往往加都察院左都御史衔,巡抚则加右副都御史衔,左宗棠在湖南,大权独揽,连巡抚也对他惟命是从。明白人或许看得透,所谓非常之时,必得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小人却不这么认为,居然背地为左宗棠取了个外号,叫“左都御史”,意即左的官阶还在骆之上。至咸丰九年,终于发生了樊燮一案,左宗棠为此大吃苦头。
关于这事的起因,有多种说法,有为左宗棠辩解的,也有为樊燮说话的,据罗正钧所编《左文襄公年谱》一书记载:“咸丰九年十二月……公[指左]既久专军事,忌者尤众,永州镇总兵樊燮以贪纵为骆公[秉章]劾罢,因构于总督,首指目公[左宗棠],总督疏闻,命考官钱宝青即讯,召公对薄。武昌胡公林翼力解之,得不逮公,是年十二月,遂辞骆公,荐刘蓉自代,请咨赴京会试。”
寥寥几句,语焉不详,当然,《年谱》为左宗棠身后所作,其时左宗棠名崇位尊,作者罗正钧不得不有所掩饰。而骆秉章的《自订年谱》则说:
“永州镇总兵樊燮声名恶劣,同城员弁兵丁无不恣怨,八年赴京陛见,先参其私役兵弁乘坐肩舆,并声名访闻各款劣迹俟查实参奏,嗣据委员赴永查该镇署中零用,皆取之营中,提用银九百余两,公项钱三千三百余串,又动用米折银两,即据实参奏,奉上谕:“樊燮着即行拿问,交骆秉章提同人证,严行审办,钦此。”嗣有人唆耸樊燮在湖广递禀,又在都察院呈控永州府黄文琛商同侯光裕通知在院襄办军务绅士左某[宗棠],以图陷害。后奉旨交湖广总督官文、湖北正考官钱宝青审办,旋于八月廿五日将樊燮妄控奏明,将查明账簿公禀、樊燮亲供等咨送军机处,左君[宗棠]因此忧谗畏讥,遂定意于十年正月出署,请咨送赴京会试。”
骆秉章的记载,较罗正钧的要详细,起因都归结为樊燮自身的劣迹——即早在咸丰八年,骆秉章赴京入觐时,就亲自向皇帝谈到了樊燮的贪腐行为,并说回去后将查明实情,再据实参奏。回来后派人去访查,终于得到樊燮贪污公款的实据,于是正式提起弹劾,不料遭樊燮反诉,皇帝下旨让左宗棠去武昌对簿公堂,左宗棠以赴京参加会试为由,离开抚署——案发经过是说清楚了,但此后是如何结案的,却略而不详。 笔者细查史料,此事起于永州知府黄文琛,他与樊燮都是湖北人,一文一武,同驻永州,当时石达开离金陵出走,流窜湖南,攻城掠地。形势如此紧急,樊燮却不筹战守,日日与一班不肖之徒置酒高会,因文武不相统属,黄文琛只能苦苦相劝,毫无效果,于是,黄文琛亲自来到省城,向巡抚揭发樊燮,又将知府的印信交与巡抚,说自己才疏学浅,恐误国家大事,于是提出辞职。樊燮得知黄文琛赴省的消息,知与自己不利,也赶到长沙,向骆秉章解释,骆秉章说,你去跟左师爷说,樊燮到了左宗棠的房间,没有请安,左宗棠发怒说,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樊燮竟说,我虽是武官,却也是二品官也,朝廷制度,没有跪师爷一说。左宗棠火了,上前踢了樊燮一脚,又拍着书案骂道,忘八蛋,滚出去!接下来,立刻以巡抚名义具疏,对樊燮提起弹劾。 “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有这样的道理吗?不错,清代官场,重文轻武,最高一级的武官如步兵统领,俗称“九门提督”[首都卫戍司令],武职正一品,如果头上没有加兵部尚书衔,则只能着戎装骑马,不但不能坐轿,且见了兵书尚书仍得打千请安;步兵统领麾下设左、右翼总兵,如果没有加兵部左右侍郎衔,见了侍郎也得打千请安。道光朝的权臣穆彰阿的父亲曾任右翼总兵,就因自己向当时的嘉庆帝提出要加侍郎衔而被革职。不过,尽管有此一说,但左宗棠身为幕僚,并非朝廷正式官员,要求正二品的实缺总兵向他请安,这就有些过份了,这也反映出左的性格:恃才傲物,目中无人,且不按规则出牌。 因为巡抚宠着他,樊燮自己也确实有把柄被人捏着,眼看就无能为力了,不料中间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竟使樊燮峰回路转,这人就是湖南藩司文格。 骆秉章的《自定年谱》里不是有一句话吗,樊燮的反诉,是“有人唆耸”,这人是谁呢?骆秉章没说,但胡林翼毕竟是湖北巡抚,既然上诉于湖广总督衙门,总督官文是他的把兄弟,所以,他要查个水落石出还是容易的,事后,他曾写信告诉左宗棠:“间公者,湘人,非鄂人也,此沛公司马之类,何足介意。” “沛公”即刘邦称帝前的封号,“司马”即刘邦帐下左司马曹无伤,刘邦先入咸阳,派兵守函谷,曹无伤向项羽告密,说“沛公欲王关中”。于是,上演了鸿门宴一幕,刘邦几乎就被项羽杀了,后来从项伯口中得知是谁告密,脱险回营,“立诛杀曹无伤。”事见《史记·项羽本纪》。
这里的“沛公司马”是谁呢?有人猜测是文格,不过,胡林翼并没有点名。
文格是个旗人,自咸丰五年至同治二年,任湖南藩司达七年之久。藩司俗称“藩台”,即布政使,地位仅次于巡抚。按清代制度,藩、臬两司,一管民政和财政,一管刑事和交通,他们仅受总督和巡抚的节制,义务却直接向朝廷负责。 据史料记载,文格与左宗棠关系很融洽。估计只是表面现象,骨子里可能不满左在湖南的独断专行,于是,唆使樊燮上诉湖广总督衙门,又去北京都察院告御状。湖广总督官文得状据实上奏朝廷,朝廷于是下旨,此案交湖北学政钱宝青审理,其中有“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准予就地正法”的话。 左宝棠得知消息,不愿到庭受辱,乃以赴京会试的名义,告别骆秉章,取道京师,刚走到襄阳,得知长子孝威患病的消息——孝威是担心父亲的安全急病的,正进退两难时,时任襄阳道的毛鸿宾向他转交了胡林翼的信,胡林翼在信中劝他不要急于赴京。其时,为围剿太平军,胡林翼驻大营于湖北英山,曾国藩驻大营于安徽宿松,高屋建瓴,对下游的太平军取进攻态势。胡林翼又说,曾国藩也担心他的安危,与其冒险赴京,不如来英山或来宿松。 左宗棠于是顺流东下,由英山而宿松,又为胡、曾参谋起军事来。不久,京师传来旨意——皇上不但不再追究左宗棠的罪责,且令他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 按清代制度,“京堂”已跻身高级官员之例,一般是三品或四品,如都察院、通政使司、詹事府、国子监、大理、太常、太仆、光禄、鸿胪等寺的堂官,通称九卿。有专折奏事之权,即可直接向皇帝上奏疏。 左宗棠终于出头了。就像一艘巨舟,驶过急浪多滩的峡谷,行进到了宽阔平静的大江上,从此扬帆远航,畅行其志,开创自己的事业了。 皇帝先是下旨要法办他,且撂下狠话——如确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为什么转眼之间,又委他以高官,付之以重任呢?这过程后来众说纷纭,不少人归功于曾国藩、胡林翼等带兵大员的保举,左宗棠本人则只认潘祖荫和宗稷辰的人情,中间委屈了一个斡旋奔走的人,这就是郭嵩焘。 不错,曾、胡二人,确实对左宗棠的推荐不遗余力,但若细查史料,有一个“时间差”不容忽视——曾、胡的推荐,都是在左没出事之前,出事之后,有旨逮捕左宗棠,曾、胡二人,一在湖北,一在安徽,就是有心相救,一时也远水难救近火,更何况当时情况不明,曾、胡二人不无顾忌。 上面说到,清代功令[制度]对幕僚管制忒严,若对照《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左宗棠条条都触犯了。文格身为藩台,自然熟悉朝廷禁令,他唆使樊燮上控,案由就是:“湖南一印两官,政务为劣幕左宗棠把持”。这可是击中了要害,朝廷若认真核查起来,左宗棠和骆秉章都“小猫抓了热糍粑——脱不了爪爪”呵! 处此情形之下,骆秉章作为同案人,自然不敢置喙,而老成练达如曾、胡之辈,也不敢随意上疏,他们虽是带兵大员,正担当重任,但他们都是外臣,所谓“帘远堂高,君门万里”——君臣之间,隔膜殊深,有时当面尚说不明白,又何况路隔千里?他们若在内务的处理上公然上疏,提出与朝廷处置相反的意见,一旦让皇帝误会了,这可不是一般的越俎代庖,而是有拥兵要挟之嫌。 那么是谁最先向皇帝进言的呢?左宗棠认定是潘祖荫和宗稷辰,宗稷辰是浙江绍兴人,与林则徐是好友,他久闻左宗棠之名,但未见过面,他确曾向皇帝上奏,说左宗棠“不求荣利,迹甚微而功甚伟,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于胡林翼诸人”。可是,这事发生在咸丰五年,樊案尚未发生,不存在营救一说;至于潘祖荫,的确就樊案向皇帝最先进言,只是,他同样与左宗棠缘悭一面,何以管闲事?众人纷纷其说,其中以薛福成的《庸庵笔记》较为可信,也较详细。
薛福成,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初入曾国藩幕府,以文学见长,后出使英、法、比、意四国,为早期外交家之一。因在曾国藩幕府,所以,对樊案的来龙去脉,算得上亲历、亲见、亲闻,据他所记,樊案发生,官文奏报上来后,最早看到奏疏的是咸丰的宠臣、军机大臣肃顺,此人重才,尤其是对汉人文士,特别敬重,他早知左宗棠在湖南的作为,阅疏大吃一惊,出来后,立刻告诉了身边的幕客高心夔,高心夔告诉了“肃门湖南六子”之一的王闿运, 王闿运迅速转告在南书房任职的郭嵩焘,郭嵩焘赶紧将肃门六子:李榕、严咸、邓弥之、邓保之等人一齐邀来,赶赴肃顺府上,求肃中堂向皇上进言。 台湾历史小说家高阳先生写到这事时,很是生动,说郭嵩焘和“六子”刚进门,尚未开口,肃顺就呵呵大笑说,左宗棠的面子真大呀,竟然一下惊动了这么多的大名士。郭嵩焘于是把左宗棠在湖南的功绩细细向肃顺说了一遍,肃顺说,我也早闻左宗棠的大名,只是这事既然由官文奏报上来,我不便贸然向皇上说及,必得有内外臣工保举,我方可徐徐进言。郭嵩焘认为在理,心想,外臣曾国藩、胡林翼必然不会沉默;自己虽在皇帝身边任职,算得“内臣”,但作为左的同乡、姻亲,应该避嫌。于是,立刻找到同在南书房任职的潘祖荫。 潘祖荫是道光朝大学士潘世恩的孙子,十七岁就中进士、点探花,深为咸丰帝宠信,眼下受好友郭嵩焘之托,立刻去见皇帝,说起左宗棠,极力推崇,说左“才可大用”,还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其实这话是郭嵩焘向潘祖荫说起的。皇帝听后,征询肃顺的看法,肃顺于是将左宗棠在湖南的所作所为,向皇帝仔细陈奏,说戡乱以来,湖南首当其冲,可不但能守住本土,且筹军备饷,外援四境,凡骆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 皇帝这才回嗔作喜,改变了要严厉处分左宗棠的想法。接下来,传旨与曾国藩和胡林翼,商量对左宗棠的安排,曾、胡、骆等统兵大员这才有机会进言,自然是大力推举,交章保荐。 其实,郭嵩焘这次是在左有危险时极力营救,四处奔走,而他事前推荐左宗棠,更是不遗余力,据《郭嵩焘日记》载,早在咸丰八年,咸丰皇帝就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过郭嵩焘,询问左宗棠的情况,郭嵩焘回忆如下:初三日再召见养心殿西暖阁,温谕移时,问曰:“汝可识左宗棠?”曰:“自小相识。”上曰:“自然有书信来往?”曰:“有信来往。”曰:“汝寄左宗棠书可以吾意谕知,当出为我办事。左宗棠所以不肯出,系何原故,想系功名心淡?”曰:“左宗棠亦自度赋性刚直,不能与世合,在湖南办事,与抚臣骆秉章性情契合,彼此亦不肯相离。”上曰:“左宗棠才干是怎样?”曰:“左宗棠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曰:“左宗棠多少岁?”曰:“四十七岁。”上曰:“再过两年五十岁,精力衰矣。趁此年力方强,可以一出任事也。莫自己遭[糟]蹋,须得一劝劝他。”曰:“臣也曾劝过,他只因性刚不能随同,故不敢出。数年来却日日在省办事,现在湖南四路征剿,贵州、广西筹兵筹饷,多系左宗棠之力。”上曰:“闻渠意想会试。”曰:“有此语。”曰:“左宗棠何必以进士为荣,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他有如许才,也须一出办事方好。”曰:“左宗棠为人是豪杰,每言及天下事,感激奋发。皇上天恩如能用他,他亦万无不出之理。”
这则记载,同样见于《左文襄公年谱》和朱克敬的《瞑庵杂识》,内容大同小异,可见左宗棠的后人还是领这个人情的。个中皇帝期望左宗棠出来为他办事,郭嵩焘对左宗棠能力的推崇,对他人品的夸赞,一一跃然纸上。可见皇帝之所以在处理樊案时,态度能迅速转变,原因就是早在一年前,郭嵩焘已在皇帝面前为左宗棠作了大量的铺垫。 可惜的是,左与郭后来有了过结,一对生死相知的老友,竟然十余年不通音信,郭嵩焘晚年曾著《玉池老人自叙》,就以往之事,细说始末,其中虽也提到樊案,却只寥寥数语,与咸丰帝在养心殿的对话,一字未提。我想,一生遭人误会的玉池老人行将就木之际,大概对世事都看穿了,就是左的负恩,他也不太在意了,寥寥数语,不过向后人作个简单交代罢了。 接下来,该说本文另一主人翁樊燮了——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反诉,竟然成全了左宗棠,肠子只怕也悔青了。既然皇上如此器重左宗棠,用湘阴的俗话说,他还能“搬起石头去打天”吗?只好灰溜溜地回到了湖北恩施县城内的梓潼巷老家。 据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记载,樊燮回家后,曾置酒宴父老,说:“左宗棠一举人耳,既辱我身,又夺我官,且波及先人,视武人为犬马,我宅已定,敬延名师,教予二子,雪我耻辱,不中举人、进士、点翰林,无以见先人于地下。” ——樊对左是恨之入骨了,发誓要报仇雪耻,并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他膝下有两子,长子增陶早死,次子增祥,字嘉父,号云门,别号樊山,聪明好学,樊燮在家建“雪耻楼”,延聘名师教子,并在楼上立一块木牌,名“洗辱牌”,上书六字:“忘八蛋,滚出去”。吩咐儿子,不中进士、点翰林,无面目见先人于地下。又特制一套妇人的服装,令樊增祥穿在里面,说身为人子,不能为先人雪耻,算不得男子汉,必中了秀才方可脱下女式内裤,中了举人再脱女式样内衣。 樊增祥果然不负父望,十多年后,不但学问有了很大的成就,为清末民初的著名文学家、诗人,且于戏剧亦颇有钻研。同治六年乡试中举,同治九年张之洞任湖北学政,到宜昌视学,十分赏识樊增祥,推荐他为潜山书院山长,后又被张之洞延入幕府,颇见信任。所以,有人调侃樊增祥说:“恩怨两文襄”——怨,自然是指左宗棠,恩,则指张之洞,他死后清廷也是谥“文襄”。 光绪三年,三十二岁的樊增祥进京会试,终于考中进士。樊家宴客三天,当众烧掉了“洗辱牌”。据刘禺生说,他去恩施,曾探访樊燮故居,当年的雪耻楼巍然尚存,楼上木板壁上有稚嫩的笔迹,写“左宗棠该杀”五字,想是樊增祥幼年所写。又说,樊增祥后官陕西布政使[藩台],因朝廷有令,凡左宗棠立功省份建有专祠,春秋致祭,永享俎豆,这年祭日到了,陕抚将此事委托樊增祥,却遭到樊的断然拒绝,说:“宁愿违令,不愿获罪先人。” 刘禺生为同盟会元老,民国元勋,笔者手中的《世载堂杂忆》,扉页印有董必武的题词,上面的话,大致可信。[董与刘一同留学日本、又都是同盟会员] 樊增祥在清朝官至江宁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按清朝制度,督抚出缺,以同级官代理称“署理”,以低一级的官员代理称“护理”或称“护篆”],此时,左宗棠的四子左孝同正任江苏按察使,与樊同在一省为官,左孝同这官先是纳赀为道员,再由人推荐才当上臬司;而樊增祥则是两榜进士及第,且文名远播,胜左孝同多多,但笔者遍查史料,却没发现樊与左相互仇视、倾轨的记载。 左孝同思想倾向维新,反对革命,辛亥革命时,江苏巡抚程德全迫于形势,准备宣布江苏独立,脱离朝廷,左孝同依然不忘故主,在会上痛哭流涕,坚决反对;樊增祥却欣然步入民国,甚至还在袁世凯时代,去北京当过袁记国会的参议员,因官瘾大,故对袁世凯、黎元洪阿谀谄媚,所献颂词,读来让人肉麻,遭到他人的嘲讽,算是名人不保晚节之诫。 我想,樊增祥幼时写下“左宗棠该杀”五字,后来怎么又能和左孝同和平共处呢?是忘记了父仇吗?或者,是身处大变革、大动乱的时代,他已无法重修旧怨了?我想,樊增祥或可作逆向思维——若没有左宗棠那“忘八蛋,滚出去”的六字“箴言”,他或许就没有后来的成就。 有西方哲学家曾说:“苦难是人生的财富”。对照樊增祥的成长过程,你能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