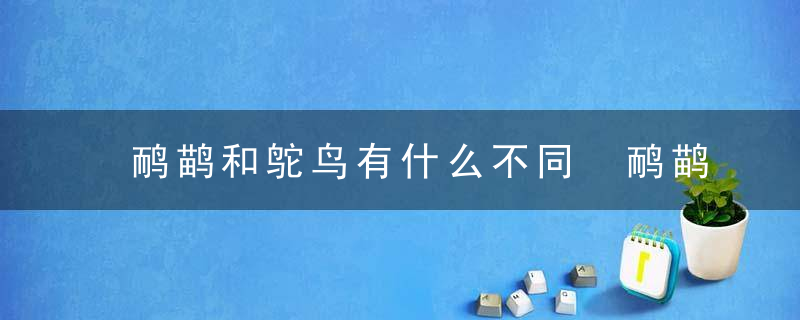清华简七《越公其事》第五章解析

【第五章宽式释文】
王思邦游民三年,乃作五政。五政之初,王好农功。王亲自耕,有私畦。王亲涉沟畛坳涂,日靓农事,以劝勉农夫。越庶民百姓乃㥄慴悚惧,曰:“王其有荧疾?”王闻之,乃以熟食鮨醢脯膴多从,其见农夫老弱勤劳者,王必饮食之;其见农夫稽顶足见,颜色顺比而将耕者,王亦饮食之;其见有列、有司及王左右先觉王训而将耕者,王必与之坐食。凡王左右、大臣,乃莫不耕,人有私畦。举越庶民,乃夫妇皆耕,至于边县,小大远迩,亦夫妇皆[耕]……□□□□□□□□□□□□□□□得于越邦,陵陆陵稼。水则为稻,乃无有闲草。越邦乃大多食。
【第五章释文解析[1]】
王思邦游民〔一〕厽(三)年,乃乍(作)五=政=(五政。五政)之初,王好蓐(农)工(功)。王亲自(耕),又(有)厶(私)(畦)〔二〕。
整理者注:“游民,流离失所之民,又作游民。《礼记·王制》:‘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参见第四章注一〇。”[2]如果按整理者的理解,则勾践让越民流离失所三年的话,如何还能出现《越公其事》第四章的“邦乃暇安,民乃蕃滋”?故游民当理解为游其民,即不以赋役等事劳民,而非整理者所说义,此点笔者《清华简〈越公其事〉第四章解析》[3]已指出。“思”当训使,“思邦游民三年”即“使邦游民三年”。
《越公其事》所说五政,与《逸周书·文酌》中的“五大”颇为相近,《文酌》言:“五大:一、大智率谋,二、大武剑勇,三、大功赋事,四、大商行贿,五、大农假贷。”《越公其事》则是“农功”、“市政”、“征人”、“五兵之利”、“敕民、修令、审刑”,两相对比,除顺序互逆、措辞略异外,整体上是非常相似的,故二者当有相当的承袭性。将《逸周书》与《六韬》比较,不难看出《逸周书》主体是源自齐地的《书》系篇章传承,因此《越公其事》此处的“五政”,当也是主要受齐文化的影响使然。
整理者在《楚文献中的教育与清华简〈系年〉性质初探》[4]一文中曾提到清华简“孔子言行等儒家类很少,只有一篇,这与郭店简、上博简形成鲜明的对比”,实际上更准确点说,上博简中“孔子言行等儒家类”也并不很多。虽然学界很多人的积习即是将各种涉及仁、义、礼、信的文献皆贴上儒家标签,行文也言必称孔子,但只要无视学界这种主观意识形态上的刻意渲染,客观直面先秦文献,就不难知道,先秦思想史的真实情况绝非学界这些人所描述的样子。笔者在《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一 虚词篇》[5]的附篇《议儒家在先秦的历史地位》中就已指出“实际上,在整个先秦历史时期,儒家学说就很难说真正有对历史进程构成任何具有积极意义的影响。所谓的影响,绝大多数是因为很多人都是从四书五经或者十三经这样局限而偏狭的视角而产生的认识错觉。”、“实际上直到战国后期之后,儒家学说才算得上真正得以侥幸厕身于诸家之列,之前基本上一直都窝在鲁国这个小圈子中,间或闻声于魏、齐、赵、卫等国。到韩非子着《显学》篇时,才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可见,一直晚至韩非子时期,犹儒墨并称,而非儒家独大,则之所以战国后期末期儒家学说才得以扩张,这一点和当时民众的厌战情绪及名家的偃兵主张恐颇有关联,更兼此时的鲁国,已如朝不知夕的风中残烛,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这时的真实情况,与其说是鲁的文化扩张、文化输出,倒不如说是鲁国众儒个个另谋出路更为适宜。”现在不妨将笔者此说对照清华简、安大简、上博简、郭店简等出土文献来验证一下。
清华简据整理者言“总计约2500枚……应在70篇以上”,而“孔子言行等儒家类很少,只有一篇”,仅为不到七十分之一;安大简据黄德宽先生《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概述》[6]一文所述,“竹简共有编号1167 个……第一组共有完简13支……辑录孔子的言论,每条皆以‘仲尼曰’引出。……第二组简共有33支……记载子贡入见孔子以及二人的对话。”是大致可确定为儒家的约两篇,仅占全部简的百分之四左右。而清华简、安大简都是以鲜明的《书》系、《诗》系和史系材料为主的,由此即不难看出,在先秦时期,不但《诗》、《书》绝非儒家私有财产,且对于真正的经史传承,儒家也绝非居于重要地位。
再看上博简,上博简至今出到第九辑,公布了约六十篇左右,可确定属于儒家的篇章据笔者印象似乎仅有十五、六篇的样子,也即只在四分之一左右,之所以人们会有上博简中儒家篇章比重非常高的印象,大概与上博简整理者团队整体选择了以儒家为主打材料有关,因此《上博一》至《上博三》所选内容才基本皆有很重的儒家色彩,这样给人们造成第一印象的行为,自然会导致很多人认为上博简儒家篇章比重非常之高。
最后分析郭店简,郭店简基本是道家、儒家、俗言短语类三种文献三分天下的局面,由墓葬形制不难推知墓主身份不高,约仅是上士或下大夫,这反过来说明,无论是《老子》等道家文献、还是《缁衣》等儒家文献,其性质都与被称为《语丛》的若干篇俗言短语类文献类似,只是下层统治阶级通俗读物的代表,其对养性修身等的强调与当今网络上流行的鸡汤文别无二致。郭店简中,《书》系、《诗》系、《易》类、史类文献皆付阙如,即已表明墓主的文化取向和趣味所在。因此上,郭店简在先秦学术史上的价值并不大,根本不足以反映先秦学术领域的真正情况。
以上对文献占大宗的当前出土材料分析表明,即使是战国后期、末期下层通俗读物,儒家仍非一家独大,也仅只是占有约三分之一的样子。随着各墓主随葬品中经史比重的逐渐增加,儒家在各出土材料所占比例就呈显着的递减趋势。这就足以说明,在先秦绝大部分时间段中,学术思想领域方面,儒家都仅只是诸子百家之一,不仅绝不是经史典籍的主要传承者,更不足以代表真正的先秦学术。
回到《越公其事》即可获知,就是因为上述分析是成立的,所以有明显越文化特征的《越公其事》篇,其主体是吸收了齐文化的影响而不是吸收了更近的以儒家为代表的鲁文化影响。
笔者在《清华简七〈越公其事〉第一章解析》中已提到“五政可溯源于士、农、工、商、刑,而士农工商即管子所倡四民,于《管子》和《国语·齐语》皆可见其说,由此可见管仲学派在先秦时期曾产生的广泛影响”[7],类似的说法尚可溯于《逸周书·程典》:“士大夫不杂于工商,商不厚,工不巧,农不力,不可成治。”由于“民”本是从有职司者中分化出的概念,因此四民本只有三,就是《六韬·文韬·六守》:“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此点于《左传》也可得到印证,《左传·闵公二年》:“僖之元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二年,封卫于楚丘,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笔者在《清华简〈系年〉1~4章解析》中已指出“所行即管仲之政。”[8]卫文公的“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正对应《六守》的“大农,大工,大商”,也即春秋前期时的农、工、商尚皆为士,士还没有特化出来而与大夫并称为“士大夫”。
整理者注:“,与九店简之‘’当为一字,李家浩释读为“畦’,详见《九店楚简》(中华书局,一九九九年,第五八页)。《说文》:‘田五十亩曰畦。’私畦,亲耕之私田。古书又称籍田。《史记·孝文本纪》:‘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9]私畦即《孟子》、《礼记》、《九章算术》中的圭田,《孟子·滕文公上》:“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礼记·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税;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夫圭田无征。”《九章算术·方田》:“今有圭田广十二步,正从二十一步。问为田几何?答曰:一百二十六步。又有圭田广五步、二分步之一,从八步、三分步之二。问为田几何?答曰:二十三步、六分步之五。术曰:半广以乘正从。”籍田的收获物原本主要是用于宗族祭祀,因此籍田是公田而非“亲耕之私田”,相关内容可参看杨宽先生《“籍礼”新探》一文[10],由《越公其事》下文“人有私畦”也不难看出“私畦”必非“籍田”。清代孙兰《柳庭舆地隅说》:“《九章·方田》有圭田求广从法,有直田截圭田法,有圭田截小截大法。凡零星不成井之田,一以圭法量之。圭者,合二句股之形。井田之外有圭田,明系零星不井者也。”因为零星不成井的田无法用井田制测量面积,只能用三角术测量,所以井田制一顷百亩,而圭田一顷只有五十亩,故《说文》言“田五十亩曰畦。”而整理者注称“私畦,亲耕之私田。古书又称籍田”将私畦与籍田等同,不知何据。
王亲涉泃(沟)淳(泑)涂〔三〕,日(靖)蓐(农)【三〇】事以劝(勉)蓐(农)夫〔四〕。
整理者注:“淳,疑指低洼沼泽。《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辨京陵,表淳卤。’《汉书·食货志上》:‘若山林薮泽原陵淳卤之地,各以肥硗多少为差。’淳与山、林、薮、泽、原、陵、卤并列,皆为不同之用地。淳可能是比盐碱地之‘卤’略强的低洼沼泽地。,疑即“泑’字。《山海经·西山经》‘不周之山,东望泑泽’,郝懿行笺疏:‘泑泽,《汉书·西域传》作盐泽。’简文之‘泑涂’或即盐碱滩涂。”[11]沼泽地不能为农事,因此整理者所说不确。“淳”当读为畛,字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