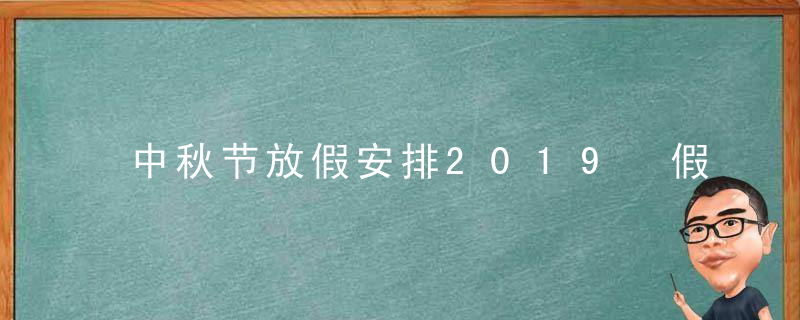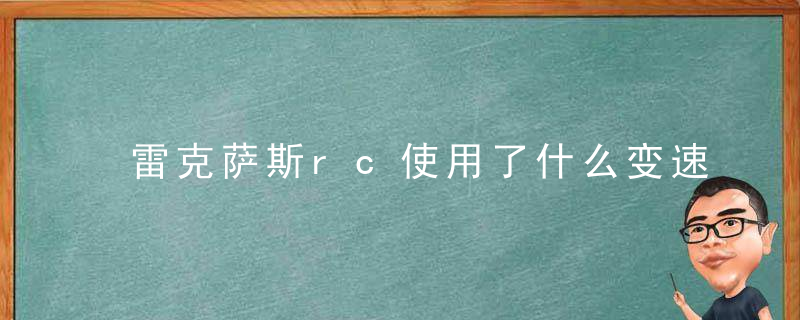冯骥才谈春节

春运完成的是中国人数千年来的人间梦想:团圆。
团圆,春节的第一主题
冯骥才
如今我们都是使用公历计日,可是一入腊月,特别是小年之后,却不知不觉改用起农历来了。尤其是从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十五,好似回到了两千多年前司马迁的《太初历》。
谁叫我们这样做的?不知道。反正只要改用这传统的历法与称谓,那一天特定的内容、含义、情感与滋味便油然而生。
我的外甥女在美国生活多年,只要她过年赶不回来,除夕之夜打来的越洋电话里,连声音都变了,一种异常的兴奋与亲切好似喊出来的,与平日电话的声调迥然不同。为什么春节总会给我们一年一度分外的人情的温暖与高潮?然而,正是为了这种非同寻常的“情感时刻”,我们中国人才会“每逢佳节倍思亲”,回家过年时才有归心似箭的感觉。
于是团圆成了春节的第一主题,也是春节最重要的情怀。
年画里阖家团圆的场景
杨柳青年画《新年多吉庆,合家乐安然》
现藏于跳龙门乡土艺术博物馆
其实团圆也是其它一些节日的主题,比如中秋和元宵。但由于春节还是一种标志着生命消长的节日,对团圆的心理需求就来得分外深切。因此,团圆一定要在关键的除旧迎新的大年之夜来实现。举家一同祭祖敬天,吃年夜饭,燃放爆竹和守夜达旦。团圆首先是家庭的。中国人把家庭为单位的血缘关系看得尤为重要。珍重骨肉亲情,鄙视六亲不认。一家人围着一桌五光十色的美酒美食,全家老小,一个不少,泯去嫌隙,合家欢聚,尽享孝道、手足、夫妻、子孙之情和天伦之乐,不一直是几千年来黄土地上的人间梦想吗?
于是,这情怀使得腊月里中华大地上所有的城乡、所有家庭都变成情感的磁场。而每一次全家欢聚都必然再一次加深这团圆的情怀。这不就是“年文化”吗?
谁说中国的节日都成了饮食节?节日的饮食也都是有主题的。年夜饺子决不同于一般饭店里的饺子。它和月饼、汤圆、春饼、腊八粥、子推燕、年糕一样,都是有“魂儿”的。我们品味的既是它们的味道,更是个中的意味。
进而说,中国人很会安排春节。从报信儿的腊八到压轴的元宵,其间长长的将近四十天。中国人是这样编排年的节奏的——
年前主要是从外边往家里忙。先是人们从四面八方往家里赶,然后是置办年货,打扫房舍,装点生活,筹划年夜饭等各类事项。这是从外向里使劲。
中间是过年,过大年三十。三十是高潮,高潮是团圆。
然后,进入新年,使劲的方向开始反过来,变为由里向外用劲。正月第一件大事是拜年。拜年先长辈后同辈,先近亲后远朋,逐渐扩大到社会的旧友熟人,最后便是全社会广场街头的元宵欢庆。就这样,年结束了,人们又纷纷回到各自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只有整体地看,才能看出团圆在年中间的位置,以及它在人间的必不可少。
当然,春节远不止一个主题。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迎春。
春节处在大自然冬去春来的时日。古人用辞旧迎新四个字表达对大自然一种很深切的情感与敬意。告别去岁的生命时光,迎接天地新的馈赠。未来的空间阔大而光亮,充满着未知,也一定福祸并存。人们便祈福驱邪,由古至今,莫不如是。
尤其在农耕时代,春是新一轮农耕生产的开始,也是与生产密切相关的新生活的开始。人们便对春字分外地敏感。春是未来一年生活的象征。
尽管春节时往往还是天寒地冻,但大多立春的节气在过年期间。我们祖先在“春打六九头”中用了一个“打”字,把春天表达得亲切可爱,充满活力。人们对春之亲昵则是立春时节习俗中“咬春”的那个“咬”字。就像抱着婴儿,轻轻咬一咬它细嫩芬芳的小胳膊小腿儿。倘若遇到暖冬一年,柳条会悄悄提早变软,像胶条那样能打过弯儿来,不会折断。在江南凉凉的融雪的气息里,往往可以冷不丁地闻到春的气味,精神为之一振。
人们在春节中呼唤春,巴望春,迎接春;因而称门联为“春联”,称酒作“春酒”等等,甚至在红纸上书写一个大字“春”,贴在大门上,表示对春的敬候。
广义的春是新生活的开始。所以,迎春也做迎新。那么年俗文化中一切祈福的内容莫不包含迎春的意味。
迎春和迎新是恭恭敬敬的。
这因为中国人的传统对天地是敬畏的。一是因为我们生活的一切都来自于天地,受惠于天地,自然心怀无尽的感激;二是天地有自己的规律与特性,不能违反,顺之则吉,乱之则凶,对其不能不敬畏;三是天地于人仍是秘密,多半不可知,故而吉凶难测。面对新生活,不能盲目的乐观,而要虔敬天地,善待万物,庄重地对待生活。先前过年都要立一块牌位,写上“天地君亲师”五个字,恭恭敬敬拜一拜。现在很少有人再拜了。其实,惟“君”不必再拜,如今世已无君。其它如天地、亲人、师长倒还是拜一拜好。
当然,春节的主题不止于此。还有祥和、丰收、平安、富贵等等,它们都是人们生活最切实的愿望。中国的春节不同于西方的圣诞。春节是个理想化的节日。这理想是一种人间生活的愿望。它经过全民族共同的创造与认定,约定俗成,成为年俗。
因此说,年俗所表达的是集体的精神情感及其方式。正是这种年俗保持了我们民族独特的精神情感的基因,一年一度增强了民族自我的亲和与凝聚。因此说,它是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深在的原故之一。这样好的年,不应该好好过一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