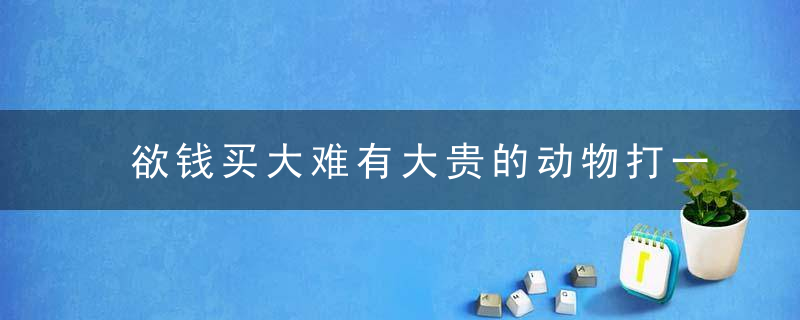报告,我要举报我爸

-这是真故非虚构大赛的第 21 篇入围稿件-
一
我和同事带着熊光军窝在一辆年头久远的桑塔纳车里已经两个钟头,空调失灵,热浪汹涌,困意阵阵袭来。从警十年,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疲倦,摸口袋准备抽烟提神。辉仔摁住打火机,冲着棚户区的入口努努下巴,向我示意:有人来了。
就在几个小时前,熊光军举报棚户区有人藏毒贩毒。
棚户区紧邻长江,位置极佳,交通便利,被两家综合性医院和一所重点学校包围。开发商很早就看中了这里,拆迁工程进展到一半,不知为何突然放弃了这个项目。现在从高处俯看,数十排已经被砸的和没来得及动工的红砖房,像留在地面的一块猩红伤疤。多年过去,管理部门人员更迭,又没有新的开发商接手,棚户区的荒草肆意生长,在潮涨潮落间失去了这座城市的宠溺。
在棚户区逗留的人越来越少,随后又发生过几起专门针对路人和夜跑者的抢劫案、性侵案。虽然案件很快侦破,此处却彻底沦为人们即使抄近道都不会选择的无人区,也成为那些渴望远离人群的罪恶栖身的地方。
二
那天早一些的时候,我和辉仔到某小区发传单。
随意走进一栋楼房,辉仔腋下夹着厚厚一沓彩印宣传单,抬头盯住显示楼层和日期的LED屏幕,日期与宣传单标题吻合——“6.26国际禁毒日,全球行动共建无毒品安全社区”。
梯厢到达一楼时,身后过来两男一女,均是二十出头的年纪。两名男性站在我的左后方,女性则刻意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站在右后方。梯门打开,两名男性紧随我和辉仔进入,女性稍作停顿,犹豫着踏步进来。
“去几楼?”辉仔站在楼层按键键盘旁问我。
“去顶层吧,从上往下贴比较轻松,多贴几张,提高视觉冲击,反正这东西也不值几个钱”。我一边说着“不值钱”,一边抽出一张传单,在手里晃了晃。
说话间,两名男性中个头较矮的那位正从我和辉仔之间探出身子,手指朝着顶层的按键戳过去,听见我所说的话,瞥见我手中挥舞的传单,瞬间偏移指尖方向,点在了中间楼层按键上。
电梯关门,履带与滚轮开始发出沉闷的摩擦声。厢顶灯带坏了一截,辉仔鼻翼翕动,脸色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不太好看。
电梯很快到达中间楼层,这一次女性没有迟疑,低头紧随两名男性离开梯厢。这栋公寓每层有三户,两名男性勾肩搭背拐向右侧那一户,而女性走出电梯后先是朝左侧方向迈出两三步,又尴尬调头,也向右侧那一户走去。
电梯继续上行,辉仔问我,“你没觉得刚才那三个人有问题?”
“哦?有吗?”
“不会错的,长期吸毒的人由于毒品进入内分泌系统,血液里、脏器壁都会附着毒品残留,散发出类似发霉的腐臭味,刚才那三个人身上就有,我闻得出来。而且,他们刚才明明是准备去顶层的,看到传单才临时改变了楼层,刚才他们下电梯的那一层,明显没有商量好该怎么走。”
越说越兴奋的辉仔拨通单位电话求援,并且撂下狠话,“信我一回,顶楼左边那户肯定有问题,错了责任我扛。”
两个小时后,开锁公司解除那户的反锁,厚重烟气夹杂麻古香味,从大门喷涌而出。散落打火机、锡箔纸和自制“冰壶”的地面上,歪七扭八地躺着神色迷离的两男一女。
其中矮个子的男性,就是熊光军,二十岁。据另外两个人交代,今晚溜冰的“货”,都是他提供的。
涉毒案件,挖毒源是关键。我在审讯室里递给他一支烟,试图以尽量亲密的姿态开始难度最大的“摸上线”的审讯。
熊光军一口嗦去半支烟,重重吐向半空,直说:“警官,不劳您费心。货,是翔子给我的,五十岁,真名不知道,没有联系方式,不知道住哪儿,但我知道他存货的地方,现在不到两点,过去守他,正好合适,他开一辆无牌照的银色奥拓,天亮之前肯定会到。”
熊光军的回答都是短句,声音利落,简洁清晰,没有丝毫犹豫,像朗诵私下练习过多次的腹稿,我在纸上只记录关键词都赶不上他的语速。
“存货的地点在哪里?”
“棚户区。”
“我怎么相信你说的是真话?”
“我带你们去。”
三
我们在棚户区蹲守到四点的时候,熊光军突然指着前面一辆模糊的车影说:“就是他。”那辆汽车背朝我们停在大约50米开外,这么远的距离,正常视力都看不太清楚,但他斩钉截铁地说自己不会认错。
吩咐协警给熊光军加戴脚镣之后,我和辉仔揣上警棍和手铐下了车。猫着腰靠近车辆,我往副驾驶车门方向移动,辉仔去了主驾驶一侧。在时间配合上我们出现了一点不默契,我刚走到车尾,辉仔已经动手拉了车门,车门并未解锁,驾驶人意识到有人在拉左侧主驾驶车门时,急忙发动倒车,试图把外面的人撞开。
辉仔向后弹起,躲开了车头,驾驶人却不知道车尾处还有人在。我被车尾刮倒,一支鞋子被车轮卷入车底,坐在地上大喊“停车!停车!”一边狼狈向后倒退。
辉仔意识到我处于危险中,扑上去掏出警棍连续击打主驾驶的车窗,直接击碎,紧接着迅速勒住嫌疑人颈部,向车窗外发力提起。他这才松开了踩在油门上的脚。我顾不上去找丢失的鞋子,光着一只脚赶到辉仔那边,把驾驶人从车窗拽出,死死压在地上。刚刚车轮扬起的烟尘还未散尽,三个人没有力气说话,自顾自地大口喘气。
“你他妈活腻啦,警察也敢撞!”缓过神来的我没忍住给了驾驶人一巴掌,还想打第二下时被辉仔拦住。上铐,搜身,检查口腔、头发和领口是否藏有刀片,一套程序走完,我的气也消了大半。
驾驶人的随身物品里没有身份证,但我们在车上找到一本驾照,姓名那一栏填写的是“熊凤翔”。我和辉仔同时发出低声地惊呼,这个名字,几个小时前在我们抓获熊光军、查询他的户籍信息时看到过,出现在标题为“父”的关系栏中。
“警官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是警察,我平时吸毒没少被警察抓,只能靠点水(举报其他吸毒和贩毒人员)来减免处罚,我以为你们是被我点过水的来报仇了,所以……”双手抱头蹲在地上的熊凤翔一边向我道歉,一边挑起右眼角,瞄了一眼顶在额前的警官证,反而松了一口气。
“今天找你不是为了吸毒的事儿,你自己想想还有什么其他事儿。”辉仔打断熊凤翔的解释,没有停下继续搜车的动作,同时直接进入正题。
“其他事儿?盗窃吗?我在派出所都交代过了。”
“爷们儿一点,上点硬菜。”我直接向他挑明有人举报他贩毒,并且明确指出棚户区就是他藏毒的地点。
天光微亮,熊凤翔脸色凝重地愣在夏日清晨温热的风里,全身竟瑟瑟发抖起来,不停用牙齿撕扯干裂的嘴皮。
沉默大约一分钟,熊凤翔问我要了一支烟,“我知道是谁举报的我,因为只有他知道这个地方。他的毒品确实是我给的,但只是给他,并不是卖给他。”
“真不是人!”已经知道他们关系的辉仔唾骂一句。
这层窗户纸既然已经捅破,情况属实的话也很难够得上贩卖毒品罪,就不需要保护举报人信息了。无论是否构成刑事案件,藏匿的毒品都必须交出来销毁,于是让协警把熊光军带下车来,一前一后押着父子二人进入棚户区寻找藏毒地点。
父子二人一路上没有言语,没有眼神交流。
四
走进一座尚未拆迁的砖房,屋子被油漆脱落的木质板分隔成客厅和里屋两间,外加一间厕所。砖房内有款式落伍的沙发和霉味浓烈的家具,锅碗瓢盆都有,但看得出来已经很久无人使用了。
从进门处一直延伸到里屋的地面上,散落或长或短、或粗或细、或新或旧的近百支针管,我们每一步都必须小心翼翼落脚。辉仔和协警带着熊凤翔在客厅搜查,而我带着熊光军进了里屋。
里屋有张木板床,熊光军进入里屋后似乎忘记了自己当下所处的状态,在没有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很自然的半躺在床头。他告诉我,这里是他的家,他的童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度过的,父亲熊凤翔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吸毒,最初吸食的毒品是海洛因,跟他同时期吸食海洛因的毒友,现在已经死的差不多了。
1992年,熊光军就在离这里不远处的医院出生。熊凤翔那时在广东打工,已经染上毒瘾,不敢回家,只在熊光军出生的当天出现了一次。再次出现,是这一片区域被市里规划拆迁的时候。
虽然当年棚户区的开发商中途跑路,但拆迁补偿还是及时发放了。当时有还房和货币两种补偿形式,熊凤翔选择了货币补偿,因为这些钱可以用来买毒品。“我妈就是那时候走的,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她长什么样了。”熊光军开始和我闲聊。
妻子走后,熊凤翔辞去工作,下决心戒毒,抚养熊光军长大。但当时本地没有专门的戒毒机构,熊凤翔只能按时到医疗部门领取戒毒药物美沙酮,在家自行戒断。
戒毒比想象中的难,熊凤翔没有成功。但出于保护儿子的目的,那时候熊凤翔每次吸毒,都会把熊光军骗进房间。“房间里放了好吃的”,这是熊凤翔惯用的理由,其实不过就是些廉价的饼干和果奶。熊凤翔并不知道,那时他还处于毒品依赖的低级阶段,主要采取烫吸(将毒品放在锡箔纸上加热)的方式吸食毒品,而高温炙烤下的毒品会进入空气,舞动着可以变幻成任何物质状态的触须,穿过房门,潜入里屋,吞噬着一具正在发育的躯体。
所以熊光军的童年记忆中,家里总有一股特殊的味道。
时间长了,年幼的熊光军会向父亲抱怨身体不舒服,熊凤翔只是说自己以后少在家里抽烟。直到熊光军读初中时,和男同学躲在厕所里抽了一支从班主任那里偷来的香烟,发现根本不是那种感觉,也根本缓解不了不时袭来的周身困顿。
年少的熊光军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有了轻微毒瘾,虽然经常会有精神恍惚和身体不适的时候,但可能因为年轻,身体恢复能力强,加上熊凤翔在家中吸毒的频率越来越高,间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二手毒害,所以熊光军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病症。
在长期的二手毒害下,熊光军的身心发育都不及同龄人,智力也低于其他孩子,愿意与他做朋友的人很少。因为姓氏是“熊”,老师和同学间明里暗里给他起了个“熊傻子”的外号。“我除了上学,几乎不出去玩。每次不得不听他的命令呆在这里的时候,我只能看窗外,外面全是高楼,全是人,全是车,我喜欢这种热闹”。
熊光军说这句话的时候,视线久久停留在窗外不远处林立的高楼之上。“有几次可能吸上头了,我觉得这间屋子好像变得热闹起来,客厅里屋都是人,妈妈也回来了,那种感觉真好。”
十八岁高中毕业,熊光军没有考上大学,也没有参加工作。一天无意在家中翻出父亲藏匿的冰毒,学着无数次从门缝里窥见的父亲模样操作一番,那些记忆里熟悉的味道、那些香烟从来给不了的过瘾、那些臆想出来的热闹,重新浮现。
八个月后,某天熊凤翔毒瘾发作,却找不到自已预先藏在沙发缝里的毒品,最后在熊光军的枕头下找到已经空空如也的PVC包装袋(一种经常用来分装毒品的自带封口的塑料袋),才知道熊光军正在重蹈他的覆辙。
熊凤翔揍过他、饿过他,还把他反锁在屋子里。可每次看到儿子毒瘾发作的样子,想到自己也难以忍受毒瘾发作的折磨,最后选择了放任。熊光军打开床头的一个小铁盒,“我的毒品都是他提供的,每次我回到这里打开这个铁盒,里面肯定有货。”
熊光军忽然意识到自己是一名被警察抓获的吸毒人员,急忙从床上起身,学着熊凤翔被我们抓获时的模样,双手抱头蹲下,轻声道歉。整个对话过程,熊光军没有使用过诸如“爸爸”、“父亲”这些字眼,始终用“他”指代熊凤翔。
五
屋内搜到的毒品不算多,辉仔用随身携带的电子称称重,客厅搜出冰毒0.6克、麻古1颗,里屋搜出冰毒2.1克、麻古2颗。“还真是一个另类的好爸爸,吸毒要把多的那一份留给儿子”,我暗自觉得可笑。
回到单位,辉仔也已经把熊凤翔的笔录做完,我一边翻看一边跟熊凤翔聊了几句。
熊凤翔90年代初接触毒品,早期主要吸食海洛因,期间也尝试过大麻叶和K粉,新型毒品出现后改为以吸食冰毒为主,吸毒方式也从早期的烫吸进化成注射。
此时被铐在审讯椅上的熊凤翔毒瘾刚刚过劲,惧怕光源,正扭动着身体躲避正面照过来的灯光。 他上半身穿篮球背心,外面套了一件深色薄纱外套,下身粗麻材质的长裤扎进袜子和套鞋里,与夏季极其不符。审讯室内空气不流通,熊凤翔向我申请脱掉外套,我同意了。
熊凤翔尽量让动作缓慢,屏住呼吸、咬牙切齿地隐忍住来自衣服内侧的撕裂感。外套全部褪尽,才发现他因长期吸毒已经导致体表溃烂,手臂、背部均有肉眼可见的血洞,流出血与脓的混合液体,散发轻微腐臭。不能接触阳光,又需要保持透气性,所以才选择薄纱这种与男性不相符的外套。
“我不希望儿子变成我这样。”熊凤翔通过大口呼吸的方式缓解疼痛,汗水还是顺着侧脸滑落。
熊凤翔发现熊光军吸毒后,两次自费送儿子去戒毒。熊凤翔已经丧失劳动能力,没有资金来源,只能通过其他犯罪方式获取。在医院里盗窃熟睡病人的手提包是常用手段,熊凤翔心里明白偷的很有可能是别人的救命钱,但转念一想这笔钱可以救自己的儿子,便无所顾忌。偷来的钱毕竟不是固定收入,两次自愿戒毒最终都是因为资金不够而中断,熊凤翔却没有因此停止盗窃的行为,这成了他后期除低保外,获取毒资的主要来源。
“看见儿子走上我的老路,真的很伤心,可惜我自己毒瘾太重,能帮他的不多。”熊凤翔说一直坚持两件事不让熊光军做,一是不让他接触供货的人,“以贩养吸”在吸毒圈里太普遍,一旦贩毒被抓,量刑很重,甚至可能死刑,因此熊凤翔坚持自己提供毒品给儿子;二是不让熊光军使用废旧针头,即使熊凤翔再缺钱,也一定会购买未拆封的新针头给儿子使用,他不希望儿子染上恶性传染病,始终保留儿子改邪归正的希望。
熊凤翔的行为不构成贩毒罪,不过考虑到熊凤翔在制作笔录过程中自称有盗窃案底,便给他拍了一张正面照,发在全局的QQ群里,让其他兄弟单位比对一下,看看是否还有没交代的问题。
不一会儿群里就有许多单位的同事冒出来调侃。“哟,这不是老熊嘛,又栽啦”、“老油条了,怎么还没学会一点反侦查意识”……不过也有同行提醒我,“熊凤翔患有多种严重疾病,没有地方收,关不进去的,别忙活了。”
那时候,我所在的这座小城因为一条《看守所在押人员“做梦死”》的新闻,把公安局推到了风口浪尖,之后包括拘留所、看守所、戒毒所在内的所有监管场所都出台了规定,对于身体患有严重疾病、传染性疾病的嫌疑人,一律不予收押。此类犯罪分子即使落网,也要强制变更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状态,实质等同于放归社会。(2016年,为解决此类矛盾,本地设立了监管医院,患有重大疾病的犯罪嫌疑人可以羁押在监管医院内)
收到同行的提醒,我便带熊凤翔去医院做了一系列检查,检查结果为:HIV阳性、双肺重度肺结核、二期梅毒。
熊凤翔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也知道自己得的这些病只需其中任何一条,就不会有监管场所敢接收,这也是他敢肆无忌惮犯罪的原因。从医院回单位的路上,熊凤祥并没有表现出如释重负的轻松,悄悄问我:“我是完了,可我儿子还有救,你们要想办法把他关起来,帮他把毒戒掉啊。”
辉仔说的对,吸毒的人确实有种味道,熊凤翔在我身边说话时尽管我戴着四层口罩,但还是闻到了,我有些厌恶地推开他。
“你儿子吸毒是你一手造成的,要是听我的,我建议你把车卖掉,花钱送你儿子去其他省戒毒,在本地戒毒所只会认识更多的毒友,出来复吸的可能性很高。
“另外最重要的,我建议你……从此以后不要再见你儿子了,如果你想他过上正常人生活的话。”
“警官,我听你的,过几天我把那辆车卖了,你们帮我把钱转交给他,让他在戒毒所里过好一点。等他出来,估计我也死了。”熊凤翔思考良久,信誓旦旦地点点头。
我给熊凤翔办理了监视居住,签字画押后他就可以离开。熊光军因为被认定为吸毒成瘾,办理了强制隔离戒毒,将在所里度过两年的时光。临出门前,熊凤翔向我申请再见一次熊光军。熊光军作为需要关押的违法人员,不能在办案中心随意见面。我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把熊光军带到辨认室的嫌疑人厅,而熊凤翔进入辨认人厅。
父子二人隔着一块只能单向透视的镜子面对面站立,并不知道在做什么的熊光军独自一人站在布满身高标尺的嫌疑人厅里,四下张望,好奇又不安。熊凤翔前倾身体,双手支撑在镜面上,被毒品摧毁的身体已经无法让他嚎啕大哭,只能轻声啜泣,镜面上留下呼出气体反复雾化的痕迹,和手掌缓缓握拳后的余温形状。
“儿子对不起。”这是熊凤翔留给熊光军的最后五个字。
此事发生大约半年后,听说熊凤翔死亡,而熊光军却从此失去消息,我有关注本市每一个被抓的吸毒人员,从未见过熊光军的名字,至今已经快六年。
*故事主人公均为化名
-特别声明:本文为企业作者上传发布,仅代表该作者观点、快闻网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作者 | 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