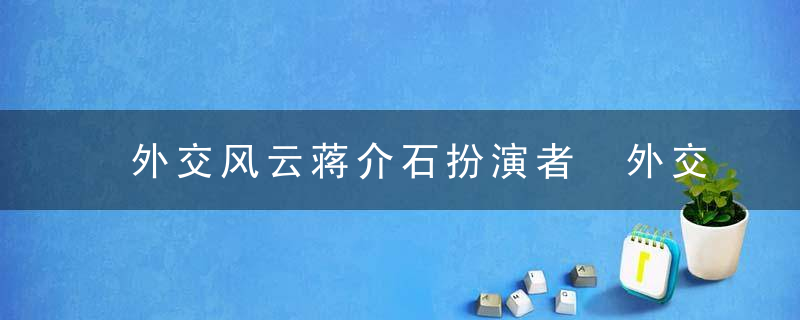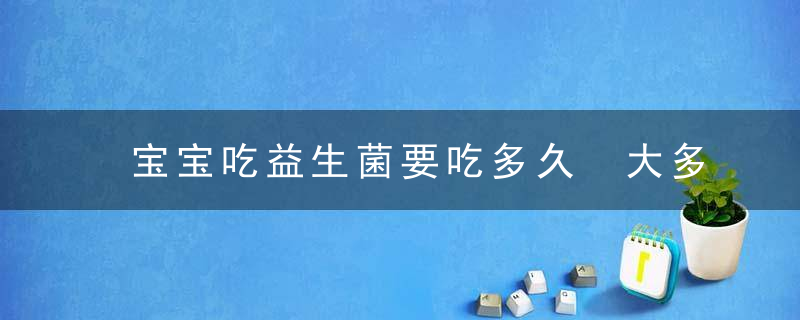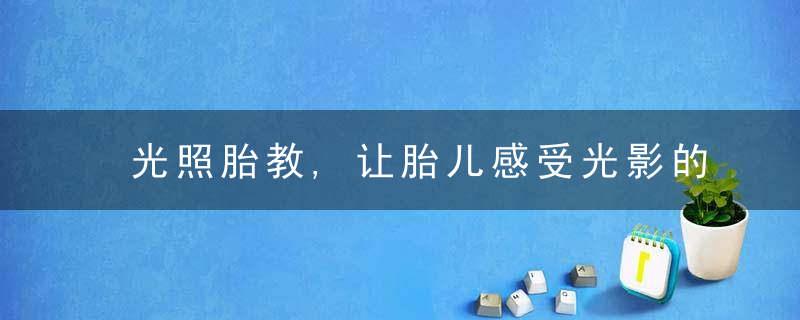中国结盟外交史上的诡诈与信用

中国结盟外交史上的诡诈与信用有几个特点:一是中国外交史上诡诈外交的出现同中国权术文化流行分不开;二是中国外交史上诡诈外交的出现同契约文化的缺失有内在联系;三是军事压力和道德感召相结合,是结盟外交成功的关键之一。
自外交产生以来,诡诈与信用的现象在外交事务中屡见不鲜。结盟既是重要的外交战略,也是重要的外交手段。中国千年外交史上的结盟,既有双边结盟,也有多边结盟;既有传统中国大地上不同政权之间的结盟,包括中原王朝与草原王朝、农耕政权与游牧政权之间的结盟,也有中国政权与域外政权之间的结盟。本文就中国结盟外交史上的诡诈与信用现象,做一个梳理,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春秋战国时期:诡诈外交与诚信外交并重
春秋时期,《史记》记载的国家有104个,另有义渠、大荔、孤竹、山戎,共计108国。春秋战国时代历时500余年,是中国古代外交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外交布局有板有眼,外交思想有根有据,外交谋略有招有式,外交成果有声有色,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了可圈可点的一页。春秋战国时期为外交提供了广阔的领域,外交艺术精彩纷呈,外交形式开始定型,周礼成为春秋外交的“国际法”。(见《中国外交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7页)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朝廷就是古代东方的联合国”,“甚至二十世纪才出现的‘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和‘联合国’(The United Nations)组织的构想,在我们的战国时代亦已萌芽。”“举凡今日西方所发展的,各种涉及国际关系的概念和实践,我国古籍中,无不行行具备”。“专司外交的行政机关,在建制中的地位也至为崇高。用句现代话来说,那便是,不是首相兼外长,便是外长做首相(美国的国务卿,便是这样的)。那时搞外交的人,也是国家间的宠儿。苏秦就是一人兼六个国家的外交部长,‘佩六国相印’的,这在人类的外交史上,显然也是一桩‘金氏纪录’也。”(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一章第三节,岳麓书社1999版)折冲樽俎、远交近攻、晏子使楚、合纵连横、围魏救赵、完璧归赵、毛遂自荐、唇亡齿寒、假道伐虢、郑昭宋聋……,春秋战国时代以成语传承的外交佳话,在中国历史上千古流传。
苏秦
春秋战国时期,外交舞台上的诡诈现象不胜枚举,这是由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所决定的。庞大的周帝国解体了,诸侯以挑战的姿态出现在全新的政治舞台上。春秋300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战国250余年间,大小战争200多次。为了争霸,为了图存,列国都不得不结盟,也不得不绞尽脑汁,甚至出种种歪招、损招来拆散别国的结盟。
在结盟中搞诡诈,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郑国通过与胡国结盟的诡诈手段来吞并胡国。“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於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韩非子·说难》)【从前郑武公想要攻打胡国,反而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的君主以使他快意。就问大臣们说:“我要用兵,可以攻打谁?”关其思回答说:“可以攻打胡国。”郑武公大怒就把关其思杀了,说:“胡国,是我们兄弟之国,你说攻打它,什么居心?”胡国君主听到这件事,就认为郑国君主是自己的亲人而不防备他,郑国就趁机偷袭胡国,占领了它。】郑武公不惜以大臣的性命,吞并自己女婿的国家,奸诈狠毒可见一斑。
不过,当时国际间虽战争不断,但大体上是重和平守信义的。钱穆说:“当时国与国间交涉往来,仍多少遵守着周公所定封建制度下的一切礼文来维系。此种种礼,若用近代新名词说之,实即是一种国际公法。”(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修订第3版,第71页)中国古代国际法自春秋时期萌芽,在以后的五百余年间得到了初步的发展。讲信修睦,是周礼的基本要求,也是当时贵族文化的行为规范。齐桓公在结盟外交当中,践行诚信外交,在古代外交史上留下了佳话。试举两例:
齐桓公称霸
一是“曹沫之约”。公元前681年春,齐桓公在山东东阿(当时地名叫北杏),与宋、陈、蔡、邾等国国君会盟,齐桓公成为盟主。此前的盟会都是由天子主持,以诸侯身份主持盟会,担当盟主,齐桓公是第一个。春秋五霸辉煌篇章,由此翻开。会盟后,齐桓公首先率军灭掉了没来会盟的遂国,接着先后击败了鲁、郑两国,迫使他们求和,树立了齐桓公的权威。曹沫是鲁国大将,和齐国曾作战三次,都输掉了。鲁庄公害怕了,想要把遂邑这个地方送给齐国来求和。齐桓公与鲁庄公相约在柯这个地方盟誓。庄公与桓公盟誓时,曹沫手拿匕首劫持了齐桓公,桓公身边的人不敢有任何行动,只是问他:“你想要干什么?”曹沫说:“齐国强大而鲁国弱小,而强国侵占鲁国已经够多了,现在鲁国的京城已经在齐国的边界,你还想要侵占。”齐桓公于是允诺把侵占鲁国的地方都还给鲁国。曹沫见齐桓公这么说,就把手中的匕首扔了,走下天坛,泰然处之地面向北站在群臣应该站的地方。齐桓公大怒,想背弃“曹沫之约”。管仲却认为,齐国要认真归还侵占的鲁国领土,正好借此来树立诚信和平的道德形象。虽然短期失去了土地,却可以获得长期的外交收益。于是齐桓公把侵占鲁国的城池还给鲁国。曹沫三次大战所割出去的城池都还了回来。主动归还土地,在春秋战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此举让齐桓公在诸侯中赢得了很大的声誉。鲁国也按照盟约承认了齐国的盟友和霸主地位。
二是公元前664年,山戎进攻燕国。燕国向齐国求救,齐桓公亲率大军北征,击败山戎,维护了燕国的安全,阻止了山戎的南下。燕庄公非常感谢齐桓公,亲自送齐军回国。他一直送齐桓公进入齐国领土。齐桓公说:诸侯相送不出境,我不可以对燕无礼。齐桓公将从齐燕边境到燕庄公所到地点的所有齐国领土都割让给了燕国。
汉代以降:诡诈外交逐渐增多
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外交的定型时期,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外交活动,是从汉代开始的。对匈奴外交是汉朝外交的重中之重。天山南路在汉初共有36国,公元前176年以后,乌孙、楼兰等北道26国都在匈奴控制之下。西汉前期匈奴统治和控制区总面积约540万平方公里,是汉朝的两倍多,匈奴的日益强大对汉代构成严重的威胁,汉匈长期争夺对东亚体系的主导权。后来,汉朝打败匈奴,确立了对东亚体系的霸权,朝贡体系由此建立并延续了2000年。
朝贡体制是蕴含着强烈的等级和尊卑意识的大一统理念在外交制度上的折射和反映。朝贡前提是,其他国家接受中国皇帝的承认与册封,在君王交替或庆慰谢恩典礼之际,必须派遣使节前往中国觐见皇帝,呈献贡品,并且接受皇帝的回赐。这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呈放射状、用朝贡—回赐方式维系的国际关系。朝贡体制作用至少有三:一是通过对朝贡国的封赏使皇威远播;二是四夷外国通过朝贡表达对中国皇帝天下共主地位的认同;三是获得强大中国的承认是东方不少国家君主合法化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通过册封、赏赐和援助,维持了东方稳定。在朝贡体制下,中国对朝贡国家有义务提供安全保证,从广义上来讲,中国与朝贡国家也是一种结盟关系。然而汉代以降,相对于诚信外交,结盟中的诡诈外交现象逐渐增多。
赤壁之战
以三国时期外交为例,吴蜀联盟在中国结盟外交史上最为典型。曹魏的巨大威胁,迫使吴蜀联手应对。相对于曹魏来说,吴蜀地少人寡,却有独步天下之志,这就决定了吴蜀两国在外交上必然是一种既相互联合,又相互斗争的关系。建安十三年,曹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取了荆州,鲁肃和诸葛亮,为图结盟而穿梭往来,终于挽大厦于即倒,一举将曹操逐回中原。没有鲁肃、诸葛亮的结盟外交,就没有赤壁之战的胜利和三国的鼎立。赤壁之战的胜利是吴蜀军事合作和外交联合的共同结果。除了诸葛亮和鲁肃始终不渝地促进吴蜀联盟以外,东吴的孙权、周瑜、陆逊、吕蒙,蜀汉的刘备、关羽等,都没有少做损害吴蜀联盟的事,特别是围绕荆州的归属,诡诈之事没有少做。
作为“五常”之一的信,三国时期仍然得到了主流社会和舆论的提倡和褒扬。三国著名的相士管辂说:“忠孝信义,人之根本,不可不厚。”(《三国志》卷二十九《管辂传》注引《辂别传》)这一提法,可以说代表了当时的正统观点。三国时期对诚信外交的重视,表现在以信设立官职或爵位。《三国志》所载以信为名的官职(爵位)有:董恢,宣信中郎;申仪,建信将军;丁咸,行左户军笃信中郎将;罗宪,宣信校尉;费伟,昭信校尉;冯熙,立信都尉,上述6位是蜀汉派往东吴的使节。郑宵,宜信校尉;步鹭,广信侯;吕叫,昭信中郎将,上述3位是东吴派往蜀汉的使节。吴、蜀两国,以信立官,上述官职多是在外交出使时而宣拜的。其原因,就在于当时总的态势是吴、蜀联盟以抗魏。故所设官职,多以“宣信”“建信”“笃信”“昭信”“立信”“广信”为名,这是一种宣言,一种承诺。其目的无非是宣示自己结盟之坚,昭如日月,决不背信弃义。
《三国志》
这是外交之信在官制上的反映。这一现象的意义实际上是双重的:它既反映出人们对信的笃信与尊重,也反映出信的衰落及人们对信的怀疑。三国中,曹魏没有设以“信”为名的官职,出使的外交使节亦不以此为名号。这与魏的自恃强大,外交上的简出有关,魏国力的强盛不需要在外交上强调所谓的“信”来增加筹码。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曹魏的用人思想,曹操曾在发布的求贤令中指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曹操集·救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曹操对不守信、不择手段的外交人物苏秦公开赞扬。
为什么汉代以降诡诈外交逐渐增多呢?汉代开始,中国通过朝贡体制主导东亚秩序,这种主导是建立在中国霸权基础之上的,虽然朝贡体制涉及到东亚体系中的数十个国家,但这个体系并非是一个多边的实体,体系中的每一个朝贡国家,仍然是以处理双边关系的方式与中国打交道。中国也习惯于以居高临下的方式来处理结盟问题。朝贡体系不是一个平等的体系,中国在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中国有实力有机会摆布对象国了。此外,汉代以降,中国多数时候不是朝廷分裂就是政权分立,在分裂或分立的时期,诚信外交被一些人弃之如敝履,这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瞬息万变的乱世,生存、利益决定了诚信的实践程度。
晚清时期:中国呼唤诚信外交
晚清时期,中国从传统外交向近代外交、从夷务外交向洋务外交(接着向国务外交)、从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从以磕头为礼的外交向以鞠躬为礼的外交(接着向以握手为礼的外交)开始转型。转型时期的中国一直呼唤诚信外交。
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说:当时中国的一些人总是以道义原则去看待西方对外扩张行为,而一些西方人则是以贱买贵卖的商战原则一再哄弄着坚持这种道义原则的中国人。曾国藩就是这种道义外交的代表人物,道义外交就是诚信外交。
清廷总理衙门的第一进院
诚信外交以儒家外交哲学为前提,以传统的羁縻外交思想为基础。中国传统的羁縻外交的表现形式,就是以儒家外交哲学为前提的诚信外交。曾的诚信外交方针有四个字:“诚”,推诚相见;“信”,信守和约;“争”,据理力争;“和”,外敦和睦。当李鸿章向曾国藩请教外交方略时,曾送他一个“诚字锦囊”。李鸿章说这个诚字锦囊“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诚”的含义就是“忠信笃敬”。曾给李的信中说:“夷务本难处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曾国藩的“信”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信守已经签订的条约,把列强限制在条约许可的范围内,抑制其贪而无厌的要求;二是讲“恩信”或“威信”,从自身的道德完善中获取自信、自立和自强的力量。今天看来,这正是对外交往所需的基本品格。1861年总理衙门一建立李鸿章就把“外笃信睦”作为主要基调。
晚清时,中国为什么呼唤诚信外交呢? 一是晚清时朝贡体系一步步走向崩溃,中国已失去对东亚体系的主导权,就是说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已缺乏在外交中搞诡诈的实力和难以承受搞诡诈外交的成本;二是中国自身一步步进入西方主导的条约体系,条约体系中的各行为体,在法理上是平等的,诚信外交是条约体系的内在要求;三是朝贡体系时代,中国不愿意平等地对待人家,到了条约体系时代,人家不愿意平等地对待我,呼唤中国诚信外交,是因为不愿意被人家欺负。
几点思考
一是中国外交史上诡诈外交的出现同中国权术文化流行分不开。谋略不等于权术,外交艺术不等于谋术权术,更不等于诈术骗术,外交辞令也不等于空话假话。但外交史上尔虞我诈、欺东骗西的事确层出不穷,无疑是权术文化影响的产物。宋代叶适所作的《宝谟阁待制知隆兴府徐公墓志铭》写道:“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把权术视为“至诚”的对立项,十分准确。权术的主要特点是没有诚信,只有机变手段。《三国演义》展示的是一个外交上折冲樽俎的时代,也是一个“仁义”叫得最响但阴谋发展到最成熟的时代。这个时代,从表面看是沙场上力量的较量,实际上是骗术、权术、诡术、心术的较量。谁的心地最黑、脸皮最厚,谁就是胜利者。换句话说,人心愈险恶、面具愈精致、伪装愈精巧,成功率就愈高。
影视剧中的曹操与刘备
1917年李宗吾的奇书《厚黑学》出版,他说他读遍二十四史,终于读出“厚黑”二字。所谓厚,就是脸皮像刘备那么厚;所谓黑,就是心如曹操那么黑。如果没有厚颜与黑心,就不能成为称霸一方的“大英雄”。“诡”字进入兵事不奇怪,进入外交更不奇怪。例如,张仪为了达到拆散齐楚合纵的目的,出使楚国,对楚怀王说:如果楚国能帮助秦国封锁齐楚边境,并于齐国断交,秦国事成后可把商于的600里土地献给楚国。这样楚国可以削弱齐国,增加土地,还可以和秦国这样的强国结交,说这对楚国是“一计而三利俱至”的好事。当楚国在张仪的利诱下与齐国真的断交后,张仪却耍赖说根本不是600里地,而是6里地。然后,秦国和齐国联手打败楚军,楚国从此走上下坡路。即使是唐太宗这样的明君,外交上也有使阴招的时候。例如,唐太宗以答应新兴公主嫁给薛延陀汗国首领夷男为诱饵,换回唐功臣大将契苾何力,换回后却不将公主送往汗国,而是设计通过断绝和亲关系促使汗国内部分裂。对此,当时就有大臣坚决反对这一外交决策,认为既已答应,不可失信。夷男发觉被骗后,气恼而死,接着,“国中乱,如其策云。”(《新唐书》卷110,《契苾何力传》,第4119页)
二是中国外交史上诡诈外交的出现同契约文化的缺失有内在联系。《礼记·学记》有“大信不约”的话,说的是真正伟大的诚信不一定靠契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大信”不等于现代意义上的契约文化。“大信不约”的“信”能否实现,靠的是人们的良心,重视的是人际关系;契约文化的“信”,靠的是运行机制,重视的是条约关系。中国古代为何缺失契约文化?这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期,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政治上表现为集权专制,在文化上等级观念浓重,契约文化不可能在小农经济和专制政治的土壤中产生。儒家的“信”是局限于亲缘、准亲缘即“熟人”之间的“信”,是单方许诺、立誓。像刘备那样把江山托孤给诸葛亮,只是一种熟人之间的信任,而不是一种契约;诸葛亮鞠躬尽瘁辅佐刘备和阿斗直到生命终结,虽然其中包含有契约的因素,但体现的不是一种契约文化,而是一种忠义精神。
契约文化中的信用建立在双方约定的基础上,是对双方相互合作的约束,是合意、是互信,因而相对稳定。这种信用将全社会的所有“陌生人”都囊括进来,因而具有极大的普遍性。李鸿章缺少契约文化精神,他在外交中对自己屡打“痞子腔”,老用“痞子手段”洋洋自得,引为得意之谈。当乃师曾国藩对“天津教案”颇感棘手时,他几次去信建议说与洋人打交道要“参用痞子手段”。1863年8月,戈登建议诱降守卫苏州的太平军将领——纳王郜永宽等“四王”“四大天将”,他的建议为李鸿章采纳。经过一番秘密联络,郜永宽在苏州城外亲自与戈登、程学启商议降约。双方约定郜谋杀谭绍光献苏州城以降清,程学启与郜永宽指天为誓,“即往不咎”,戈登作担保人,程学启承诺保证郜及部下性命。12月4日,郜永宽等八人刺杀谭绍光,第二天大开城门迎接清军入城后,李鸿章违背诺言,诱杀了这8个降王、降将,数万太平军在毫无戒备中被诛杀。杀降激起了戈登和洋人的强烈不满,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更因为戈登是太平军投降的保人,这下搭上了自己的信誉,怒不可遏。上海的外国领事馆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也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相反,对李鸿章杀降,请廷下旨明确支持,连主张“诚信”的曾国藩也称赞这种行径说:“最快人意”。(引自雷颐《杀降的“国情”与“公例”》,载《历史:何以致此》,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这说明,儒家的“信”与契约文化不是一码事。
影视剧中所体现的“苏州杀降案”
三是军事压力和道德感召相结合,是结盟外交成功的关键之一。地缘格局同结盟外交中的诡诈与诚信有内在的联系。春秋时,晋楚争霸,郑国夹在晋楚两个大国之间,在南北霸主的争夺中,政治立场反复多变,晋国找上门来,就宣布与晋国结盟,晋国走了,楚国找上门来,又宣布与楚国结盟,毫无诚信可言。晋楚双方都苦于难于同郑国结成巩固的同盟关系。后来,晋国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将晋国及其从属国的军队搭配分为三部分,驻于虎牢,轮流出征与楚国争夺晋国,采用“楚进则晋退,楚退则晋进”的以逸待劳的战术。郑国终于经不起晋国的轮番进攻了。郑简公向晋悼公表达了永结盟好的诚意,请求立盟歃血。晋悼公说:“交盟已在前矣,君若有信,鬼神鉴之,何必再歃?”如果有诚意结盟,就没有必要再次歃血为盟,只要严格遵守之前的盟约就可以了;如果无心友好,再多几次歃血也是白搭。晋悼公传令释放所有郑国俘虏,撤掉虎牢全部驻军,严禁军队侵犯郑国百姓。随后语重心长地对郑简公说:“寡人知尔苦兵,欲相与休息。今后从晋从楚,出于尔心,寡人不强。”【我知道你苦于兵灾,早就想停战休息了。今后你是要从晋,还是从楚,都由你自己内心决定,我不强求你。】郑简公听了这句话,感动得泪流满面,发誓再也不背叛晋国。此后较长一段时间里,郑国果然全力维护与晋国的结盟关系。晋悼公军事压力与当地感召相结合,靠诚信外交成功地拉住了郑国。(参见张程《春秋大外交》,群言出版社2015年版,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