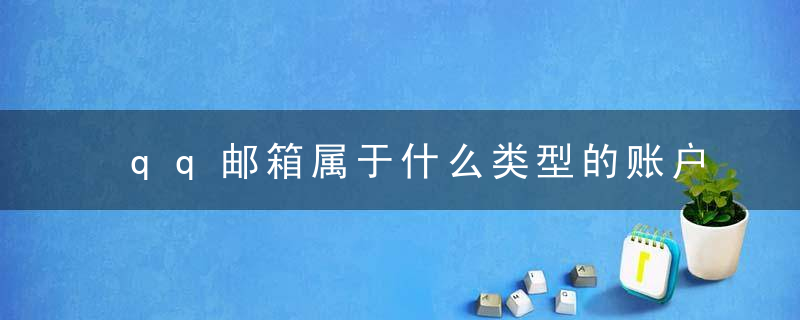拒收周末和假期的工作邮件

人们彼此的连接越来越紧密,也越来越想让人逃离。
编者按:从什么时候起,逃离成为了一种流行趋势,逃离北上广、逃离创业、逃离“凌晨四点”。互联网的发展让人们可以“一直在线”,但是身体的“在场”却并不代表着精神的“在场”。“连线”之后,人们的“下线”之心愈加强烈。
几个星期前,我向一位教授发了一封邀请他接受我的采访的电子邮件。几秒之后,我收到了一封“不在工作时间”的回复。
“现在不是我的工作时间,希望尽可能不受打扰。”这封邮件这样写道。非常典型的回复。它的意思是,当他回来时,会给我回复。
谢谢你的留言。从现在开始8小时内,××时间段的电子邮件将被删除。请在此日期之后再次发送你的信息。
什么鬼?
我的困惑很快就变成一种莽撞的冒犯。这封“不在工作时间”的回复简直是在藐视这个基于互联网的社会强加给所有人的电子邮件规则,而且他毫不掩饰地这么做!我们当然可以在度假的时候不去查看电子邮件。这很有道理。但是,不在回归工作后检查未读邮件?不在回来时一封封查看邮件情况?如此粗暴地直接删掉它?想在其他人都被控制的时候,将自己从大机器的齿轮中解救出来?这也太胆大妄为了吧?
又过了一分钟,我恍然大悟地发现,自己的反映看起来似乎不那么正常。
当然,这与邮件本身没多大关系。正如阿德里·安娜拉弗朗在其2015年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人们不像之前那样喜欢电子邮件了。“从文化角度分析,它从让人感到愉快变成了人们的累赘,这一态度转变反映在收件箱通知中。”她写道,“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线会兴奋地通知你‘你有邮件!’”而现在,Gmail的表达则恰好相反:“没有新邮件!”对于员工,尤其是那些工作信息需要查看大量电子邮件的人来说,他们大清早就害怕发现收件箱里有许多未读邮件。经过一周旅游过后的心情也是如此。
研究表明,人们在短暂休息之后需要处理大量等待回复的邮件这件事会给人带来压力。在2012年的一项研究中,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教授格洛丽亚·马克研究了信息技术的使用如何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她要求一些办公室工作人员在为期一周的工作时间里禁止使用电子邮件,而让其他人继续使用,并在所有实验者身上佩戴心率监测器。马克从实验者的静息心率数据中发现,被禁止使用电子邮件的实验者的压力水平明显下降。她说,当人们再次回到电子邮件的世界中时,压力也会随之出现。
在这项研究中,最精彩或者说是最糟糕的情况是,马克和她的同事在招募那些愿意在5天内不接触邮件的人时遇到了阻碍。邮件嵌入人类的生活程度之深以致于我们即便是想要获得短暂地喘息也显得极为不现实。在我遭遇“不在工作时间”的邮件回复时,我的反映如此糟糕,我对电子邮件的态度太过固执,以致于当我发现有人试图逃离时,第一时间竟然觉得这是错的,这种做法简直不公平。
而这封邮件的回复者,康奈尔大学工程师、曾经的美国宇航局首席技术专家,梅森·佩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佩克说道,当他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应付那些让人分心的电子邮件时,就决定采取激烈行动。
“虽然这样说有点愤世嫉俗,但是我通常认为电子邮件是一种不平衡的交易。”佩克说道,“总体而言,我回复的每一封邮件都是为了帮助别人,而不是帮助我自己。”
马克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管理电子邮件是一种控制行为。对于某些人来说,其邮箱的未读邮件越接近于零,越能感觉自己已经成功进行了大量交流。佩克也在试图控制自己的收件箱,只不过采用了另一种方法。
“我不会操心发件人的信息,除非他认为这些信息重要到需要不断强调重复它。”他坦言,这种将负担加之于发件人身上而非收件人的做法似乎是不公平的。但是佩克认为这种做法替他分担了许多压力,毕竟不这样做就需要他自己来处理这些事情。
“我觉得好多了。”他说,“当我结束度假的时候,说真的,我觉得自己心情愉悦仿佛面对一个全新开始。”
而马克则表示自己不喜欢这种做法,尤其因为这种做法扰乱了这个脆弱的生态系统的平衡。在这个生态系统中,负担应由参与者平均分摊。“这个社会交流信息系统之所以能够良好运转就是因为人们都默认为其他人也在这么做。我回复邮件是因为我想让其他人也回复我的邮件。我帮一个忙是因为我希望他们也能帮我一个忙。”她说道,“如果一个人试图从这个系统中逃离,就会打破这种微妙的平衡进而让人感到不安,而且责任的分配也会变得不再均匀。”
两年前的我也有着相似的看法。当时我的同事吉姆·汉布林提出了一套全新的使用电子邮件社会礼仪方法,目的是减少我们在这上面所花费的时间。他的建议是:追求简单,跳过客套话(“非常棒”“干杯”)、避免问候(“除非必要,不要再写上收件人的名字。因为绝大部分人已经知道他们的名字。”),而且尽可能用三句话或更短的话说清楚要表达的内容。简而言之,就是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发邮件。汉布林的这一举动和梅森一样,都试图打破了这个体系的平衡。同样,与梅森一样,汉布林这么做是为了让自己头脑清晰。
提倡功利主义的电子邮件往来方法,按规定要求写邮件并期待每个人都应该回复邮件的做法相当有戏剧性。马克说,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系统,但是我们此刻却都在使用。“我们只是被保持彼此互动的社交网络所吸引。”她说道,“有些时候,我认为我们都是被困其中的囚徒。”
马克认为,公司应该明令禁止在下班后发送消息,以减少电子邮件在非工作时间的往来频度,并让员工得以喘息。她引用一项纽约正在拟议的法律,该法律规定,当公司员工按规定下班之后,公司通过电子邮件或者是即时通讯服务联系员工是违法行为。这在法国已经成为现实。去年,法国颁布了一项“断开连接权”的法律,其允许员工在非工作时间可以选择忽视工作邮件。
或者,我们可以重新设计电子邮件服务,使其不仅可以通过扫描电子邮件来确定内容的优先程度,而且还可以代为处理某些人发给你的会议邮件安排。
“我们可以将处理琐碎工作的任务交给智能系统去处理。但是在这个愿望成为现实之前,我们依旧处在被围困的状态中。”马克说道。
我问佩克,他是否担心自己会错过一封非常重要的邮件,而且出于某些原因并没有在工作时间再次发送。“我想象不出自己能够收到一封重要到足以改变我一生的邮件。”他回复道。
的确如此。相关调查显示,我们收到的大多数电子邮件都没什么价值。正如我的同事Joe Pinsker去年一篇报道所言,杜克大学的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里进行了一项分析,分析发现“约有三分之一的邮件没有说清楚其重要性,而只有十分之一的邮件是重要的,其需要在5分钟之内得到查看。”
那么,批量删除邮件是否会让人错过一些重要的或者是有价值的信息呢?
“社交控们需要放弃对‘总觉得有事情找我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的焦虑情绪,” 一所致力于效率培训的媒体公司Forte Labs创始人Tiago Forte说道:“这就是稀缺思维的基本特征:如果有价值的信息呈稀缺状态,那么我们当然需要保持警惕以不放过它们。但是当我们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都沉浸在这些有价值的知识中时,社交控们已经无法得到任何有意义的东西了。”
的确如此。
在某种程度上,佩克的做法也可以被纳入为“不在工作时间”行动的一部分。早在10年前,人们的邮件回复很简单——你现在不在,不久之后会回来。现如今,人们的线下生活与网络生活日益相嵌合,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现实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也从未曾真正“离开”过,尤其是当我们从事的工作要求我们总是“在线”时这种情况更为突出。在如此高度互联的环境中,一个人的缺席就会变得非常突出,甚至让人觉得不那么合理。也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人们“不在场”的细节,关注那些吸引着他们耗费时间的与工作无关的事情,进而希望从那些等待着自己回复的发件人那里得到一些理解。
读读作家梅林曼于2007年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这篇“不在工作时间”的信息。“如果你的东西不急着得到回复,那么就不要现在发送。”梅林曼写道,“你自可以将电子邮件作为自己的记事簿,但是请理解我实在是无法在清理婴儿屁屁的时候给你回复。”
再读读《达拉斯晨报》编辑迈克尔·麦歇尔的文章,其被艾米丽·古尔德发表在《纽约时报》上:“如果你对我现在不在办公室这件事感到生气,那么你试想一位中年男人大约在18年前爱上了一个漂亮小姑娘,现在他需要把她送到一座遥远城市里的一所大学,在这里人们做些应该做的事情……他必须把她留在那里。独自驱车回家。伴着夜色。驾驶着厢式旅行车。孤独一人。”
或者这则来自作家丹尼尔·马洛里·奥茨伯格的信息,古尔德也报道过,其与佩克的回复类似:“我现在在休假,不接收任何邮件。我也并不打算在回来的时候查看这些老邮件,因为这极度破坏我度假的心情。”它想说什么?一个字,不。
相比较而言,派克给出的“不在工作时间”的回复可能是最最真诚的。他根本无心于做这件事,而且我们每天收到的大部分电子邮件都不怎么重要。
“那种每封邮件中都含有一个人的信息,因此也应该得到某种认可的认知令人抓狂。”福特表示。
我收到的第一封邮件,大概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当时我简直视若珍宝。这封邮件来自于我的父亲,也是他帮助我申请了第一个电子邮件账户,那年我10岁。“现在,我们可以随时给对方发消息,”他写道。每个人都能这么做。这么多年过去了,电子邮件从涓涓细流汇集成汪洋大海,服务商设计了文件夹、过滤器和标签等功能,通过算法进行邮件内容搜索,我们需要不断查看邮件,直到通知小红点消失不见。我们邮箱里的邮件堆积如山,有一些有用,而更多则是无用,它们都等着我们每天早上去跨越。但是当我们即将被掩埋时,努力让自己的头露出地面,从而使我们能够在这个将我们永远连在一起的世界中得到一些慰藉。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