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叛亲离养大的孩子,终没有成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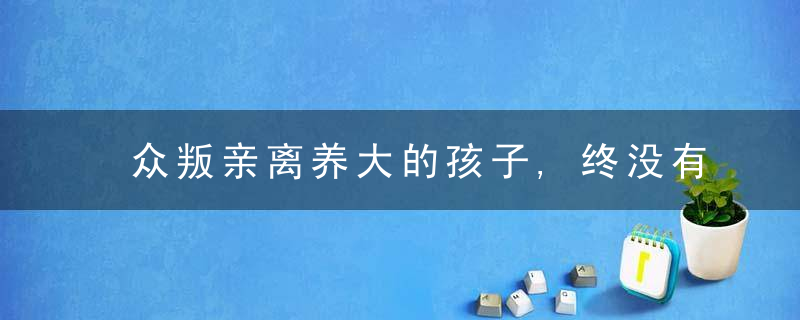
今年,我忽然想起20年前曾经帮助过的一个弃婴,便决定去看看他。
钻进县城老街那条狭窄的死胡同,两厢新建的高楼拔地而起,原本不过一米宽的胡同更显窄狭。湿热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腥味,从尽头扑面而来。
一个精瘦的汉子听说我要找那个弃婴,“陶央央早就死啦”,说着指了指胡同南边新建的三层楼房,“这不,宅子都卖给别人了。”
“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咋会死啦?”
“那小子命苦啊,得了白血病,冇人管他,死在郑州啦。”
1
1997年夏天,我在县民政局工作,跟局长和一名主管副局长、报社记者一起做贫困户调研,头一次钻进这条满地水洼、杂树丛生的死胡同。
尽管有心理准备,可眼前破败的景象仍让我吃惊。
院内有两间老屋,南边一间已经露天,倒塌的椽木砸在门头上,摇摇欲倾,进不去人。剩下不足10平方米的北边小屋,没有窗户,墙已被烟熏火燎得一片漆黑。屋内靠墙摆放一张小床,占去三分之一的空间。门口用烂砖支起一口铁锅,散落一地的烂纸箱和废弃塑料瓶都被雨水浸湿了,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老屋的主人是孤寡老人陶淑琴,已经73岁了。
那天,她一见我们就哭诉起来:“夜儿黑大雨下个不停,外边的水直朝屋里流,俺跟孩子用洗脸盆往外舀水,舀了整整50盆啊。天明,孩子直喊腰痛,去医院检查,急性肾炎,4个+号……老天爷,这可该咋弄啊!”
陶淑琴哭着把那个孩子拉进怀里。陶央央当年13岁,长得白白净净,只是左眼球像长了棠梨花一般,蒙了一层白光。
那天,我们代表给他们送去了200斤面粉和100元救济款。随后,雇工人拆除了旧房,建了两间新瓦屋。
建房期间,我曾几次采访陶淑琴,这才知道她和陶央央的故事。
2
陶淑琴早年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父母为避战乱水灾,将她嫁给乡下一个富户的独生子。婚后两人生育一男一女,不过都夭折了,等她再生下一胎女儿时,却因病失去了生育能力。
陶淑琴的丈夫看香火要在他这辈断茬,便将怨气全撒在了媳妇身上。陶淑琴忍受不了,就想回娘家躲几天。可她爹娘只觉得,嫁出去的闺女泼出门的水,硬是半夜把她赶出家门。
就这样,陶淑琴在丈夫的打骂中熬了几十年。
1984年农历10月10日,丈夫因琐事再次对陶淑琴大打出手。陶淑琴顶着寒风回了娘家,这时爹娘早已过世,家里只有患病在床的二哥。
陶淑琴行至半道,在路边的砖窑歇脚时,忽然听见里面传出一阵啼哭声。寻声摸去,只见地上有一个花铺盖卷,里边裹着一个婴儿。
解开铺盖卷,里面是个先天病残的男婴。孩子的两眼散光蒙一层雾气,双侧疝气憋胀得下身青紫,肚脐红肿。
陶淑琴不忍心让他自生自灭,便将孩子抱回家里。丈夫见了,破口大骂:“赶紧把这个废物给老子扔了,不扔给你摔死!”
说着扑上去要抢夺孩子,陶淑琴赶紧逃出家门,抱着孩子又回了娘家。
3
陶淑琴的二哥陶珍青年时代曾被错划为“右派”,婚姻破裂,膝下无儿女,晚年孤寂。
陶珍见妹妹抱进门一个男婴,十分高兴,当即以“龙旗阳阳,和铃央央”之意,给孩子起名“央央”,期待着长大成人后,为人处事居正。还将小央央认作孙子,立下遗嘱,让孩子继承家业。
为了抚育小央央,陶淑琴经常往县城跑。最终,夫妻俩离婚,陶淑琴净身出户,回娘家的老屋居住。
小央央的出现,也让昔日沉寂的老屋充满了生机。
兄妹俩辗转好久,终于给孩子落了户。为了给小央央治病,更是跑遍开封和郑州,最终奇迹般地让孩子的右眼视力恢复到1.5,左眼恢复到0.6。陶淑琴还找老中医寻了一个偏方,用公猪卵治疗婴儿的先天性疝气。县城养猪的少,陶淑琴就跑到乡下,一边拾破烂,一边寻找阉猪匠人。几年下来,孩子的疝气竟然逐渐消散了,连红肿的大肚脐也塌陷了下去。
小央央开始像正常的孩子一样,咿呀学步满院乱跑。陶珍也常常将孩子抱在腿上,手把手地教《三字经》。
4
1990年冬天,小央央6岁时,陶珍病倒了。
弥留之际,陶珍拉着他的手,“爷爷一辈子教书育人,除了一箱子书,没给你留下什么。今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了,多读书,做个好人。”
陶珍又把陶淑琴叫到床前,“把这孩子就交给你了,把他养大成人。”
陶淑琴大哥大嫂去世早,撇下一个女儿。侄女跟陶淑琴兄妹俩处得很好,经常登门探望,陶珍去世,就是侄女挑头办理的丧事。
可侄女一听说叔叔立下遗嘱,要将老宅过继给一个捡来的孩子,心里就横竖觉得不通情理,她找陶淑琴理论,认为这都是她一手造成的。
那时候,随着县城地价的飙升,位于老城中心的近半亩宅基地已成了一块“肥肉”。侄女家孩子多,住房紧张,就想在陶家老宅西边的空地上建新房。
陶淑琴遵寸土不让。为此,侄女将陶淑琴告上法庭。县法院经过审理,将宅基地一分为二,东边的老屋归陶央央,西边的空地给陶淑琴的侄女。
自此,陶淑琴和侄女也形同陌路。
不仅是侄女,陶淑琴的女儿也曾极力撺掇,让陶淑琴将剩下那块宅基地过户到自己名下。陶淑琴恼了,数落女儿竟有此非分之想。娘俩不欢而散,从此很少来往。
5
陶珍去世后,陶淑琴和小央央失去了生活来源,全靠捡破烂为生。
每天夜晚,陶淑琴都带着小央央,从城东到城西,奔波于各个垃圾点。废纸、橘子皮、饮料瓶,扔掉的破衣服、旧鞋,但凡穿身上能够遮风挡雨,她都要。一晚上奔波,最多也不过挣上几块钱。
那时候,小央央的学校距离陶家仅有一路之隔,但陶淑琴还是坚持每天到校门口接送。有时,小央央遇到好心人送他些零食,舍不得吃,总是跑回家,先让陶淑琴吃一口。
陶淑琴身患老年性肺心病,喉咙眼里嘶拉嘶拉直喘蜂鸣音。她害怕自己哪天死了,剩下小央央一人无人照料。于是,她只能常常到捡小央央的地方转悠,又去周围的村子里打听,希望能找到孩子的亲生父母。
听说我是做宣传工作的,陶淑琴拜托我把小央央的身世写出来,“能给孩子找到家,俺这辈子死也瞑目了。”那年,我根据采访笔录,写了一篇《一位孤寡老人和一个弃婴13载的风风雨雨》的报道,发表在两家报纸上。
然而,虽有热心人提供线索,但最终未能找到生身父母。
不过,开封市希望工程此后决定,每年资助小央央85元助学金,学校也减免了部分学杂费。县民政局每月提供68元救助金,还承担了小央央剩余的学费。
虽然这些钱缓解她们的部分生活压力,但祖孙俩的医药费和生活费,仍有很大的缺口。
1999年初冬,我到县城东商场摆摊卖服装,瞅见陶淑琴佝偻着腰,步履迟缓地在服装摊前徘徊。她手里握着一把分分毛毛积攒的6块钱,要给长高了的孙子买一条毛裤。
我从柜台上拿了一条毛裤送给她,她坚持要把那些零钱塞给我,但被我阻止了。陶淑琴吃力地喘着,上气不接下气,“俺认识你,会让孩子记住好人的。”
不久后,陶淑琴就去世了。
6
2003年非典结束后,防疫科长向我讲了一个事:闷热的夏夜,他钻进老城死胡同,去堵一个孤儿的门。陶央央从开封带回家几个身份不明的人,需要重点防疫筛查。我很震惊。
不久之后,县城召开公捕公判大会,几辆大卡车载着受审对象,游街示众。游街的卡车经过我的店铺,我打眼就看见,车上站着一个瘦高个子的男孩,面朝南,正对我,脖子上挂着一块黄板纸箱,上边用墨笔书写着一行醒目大字——陶央央。
卡车上站着的一行嫌犯,别人都低着头,唯独陶央央昂着头,扫视着围观的人群,毫无惧色。他那张稚气未脱的脸依旧苍白清瘦,未被完全治愈的左眼蒙着一层白光。
至此,再无音讯,直到今年我再度回到那条老胡同。
7
“当初陶淑琴就不该要这个孩子,叫他自生自灭去。”老城胡同里的邻居听说我要找陶央央,纷纷走出家门,七嘴八舌地议论。
“就是,自个十八张牌都顾不住,还去管人家扔的孩子,自讨苦吃。”
“陶淑琴死后,这孩子就整天跟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块,咋会不学坏啊。”
街坊们对陶央央颇有微词,抱怨他三天两头招来社会闲散人士来到家里,让左右邻居像防贼一样地提心吊胆。
陶淑琴死后,陶央央先是被劳动教养,继而“二进宫”,被判刑入狱。出狱后,生活无着落,当年,陶淑琴众叛亲离,拼命保住的半套陶家老宅,也被他两万块卖了。
2004年以后,他跑到郑州卖报纸,查出了白血病,没钱医治,很快就死了。至今,邻居们都不知道他身葬何处。
没想到,我曾满怀希望要为陶央央寻亲,却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本文系网易独家约稿,享有独家版权授权,任何第三方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