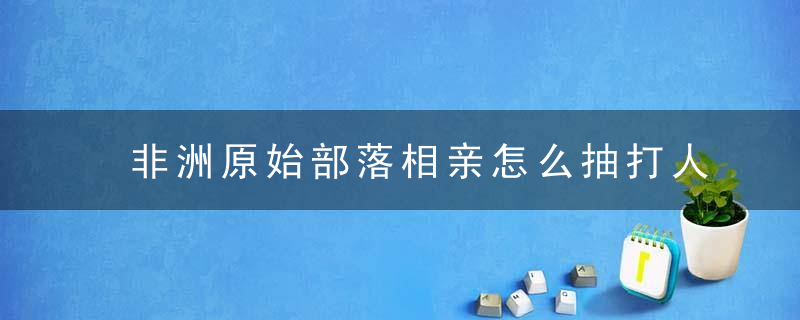一壶往事胸中浮

按:今年上半年,蔡猜告诉我她要出本散文集《安静地行走》,嘱我写篇文章。蔡猜和我是诗友,1999年我还在武汉读大二的时候,我们就在一个诗歌论坛里认识了,没想到我们后来能在同一个城市相遇。近日,蔡猜的新书正式出版,发布此文,以示祝贺老朋友。
二十多年前,读余光中、董桥等人的诗文,年轻的心虽亦时时为海峡彼岸的乡愁波纹所搅动,而暗地里总不时生起做作之讥。而人到中年,近读蔡猜的散文,听她回忆童年往事,追忆浮世前生,竟每每随之自失,对她明说暗指氤氲缠绕的乡愁,惘惘然有了感同身受之感。可见,乡愁的生根发芽不仅需要一再拉长的空间的悬置,亦喜回忆夕光的返照,在时空母体双手的一再揉搓之下,那一颗徜徉又敏感多思的心,才变得熨帖、自安,和融一色。
蔡猜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她也从未长期寄居外地,所谓的乡愁似乎没有来由。但是她写过去的苏州,写童年的街巷、山林,写往日种种的人情物理,笔笔皆是回忆,皆是情思。我想,如果可能,她宁愿生活在明代的苏州,在唐祝文徐墨迹未干之前就可以一览胸中丘壑。最不济,也要生活在沈三白的清代,古风犹存,可以细细品咂布衣素食的至理纯味。所以她的病,说到底,这是一种文化乡愁,是从一日三餐抽身而出之后,内心不知如何安放的惶惑感,是细碎的日子在时光之水里沉淀又沉淀之后,酿出的浓浓的醇香。文章是旧时的好,回忆是梦里的真。在这个时代,没有点怀旧精神,好像就写不好文章了。所以,蔡猜喜欢回忆快乐的童年时光,想念过去的点点滴滴。她时时想起儿时走过天平山上的古御道时的情景,而“如今,在这片土地上行走着时,我总是带着一种无法抑制的满足感。”(《古御道上的童年时光》)那些人与事隔着久远的时光在水里一漾一漾的,泛起的圈圈波纹,就走过了十年二十年的光阴。她甚至迷恋起了过去的耕作岁月:“我不晓得为什么,自己一踏上这片宽敞的土地,就要想起耕种,想起那些艰苦的岁月。我是那么迷恋过去,甚至很多时间都把当下给忘记了。”(《那些没有雾霾的情境》)说起耕种,她的印象是:“那时,我们还要种水稻,种油菜花,种小麦。我结婚怀孕后,因为妊娠反应,便在家中待产。每天,等丈夫回家,便陪我去田间散步。从村口走到典桥,一路上全是水稻,夕阳下的水稻田,非常美好。有风的日子,可以恍惚看见海浪一样的波纹。从青绿走到金黄,我把那一季的稻田,全部收录进我的记忆。”(《看夕阳》)从她的记忆深海里泛起的农耕画面简直是如诗如画,仿佛是最后的人间净土。但是我们可不能被她骗了。打小就跟着父母埋头弯腰躬耕于田间地头的我深深记得,农家的劳作绝不是这样诗意,相反它意味着烈日当空时遍身不断涌出与稻粒一样饱满、金黄而又擦都来不及擦的滚烫汗水,意味着腹中空空两股战战时肩上越来越重的千钧重担,意味着夏夜繁重的劳作间息只能倒在濡湿的田埂杂草上伴着虫子和蛙声睡去……。然而,蔡猜给它的命名是美好,她打捞上来呈现给我们的全是闪亮的珍珠。这真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功夫。说到底,回忆往往是一厢情愿的,在这恋恋不忘中,有种自甘沉沦、不依不饶的意思。对此,略萨说得很对:“文学是对生活的一种虚假的再现,却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活。”所以,无论过去如何艰苦经历多少磨难,当它在回忆里、在文字中现身时它只能是美好的,温馨的。她需要的不是一面反映过去的镜子,而是一面会变形的凸透镜。她要用尽所有心力,把所有的光聚焦到一点上,让它发热、并且燃烧,在那升腾的烟气中,她的心获得了一种难得的满足。
略萨还说:“文学在这座我们出生、穿越、死亡的迷宫之中引领我们。当我们在真实的生活中遭受不幸和挫折时,文学是我们的抚慰。”在漫长而晦暗不明的一生中,是文学带着人性之光照亮我们前行之路。巧合的是蔡猜也提到了迷宫:“年少时,我无数次走过这样的弄堂。骑着单车,在石板路上穿行。远远就能听到远处的人声,泼水声,小人的哭闹和打斗声。进入这样的弄堂因为不熟悉的缘故,我总会产生一种进入迷宫的错觉。因为这样的错觉,直到今天,我还是喜欢一个人在小巷子里闲逛,希望能在行走中,找回往日那种生动的情趣。”(《北寺塔上看姑苏》)在回忆的“迷宫”里,她找到的、认得的总是那些沿着她的情感脉络伸展的路径,顺着这些路径,一直走回记忆深处,走向自己。所以无论回忆、乡愁还是写作,都源自她的内心需要,源自一颗心不惧岁月风霜的需要——它以此为生。还是恩斯特·卡西尔看得透彻:“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即使在实践领域,人也并不生活在一个铁板事实的世界之中,并不是根据他的直接需要和意愿而生活,而是生活在想象的激情之中,生活在希望与恐惧、幻觉与醒悟、空想与梦境之中。”说到底,这是作家给自己编织的一个梦,一个独自怀想、安憩心灵的空间,她需要的是对那最高的自我有所交待。至于这个梦它是搁在过去还是现在,或者未来,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梦仍未醒,仍像春天枝头的露水一样美丽。
有一段时间,蔡猜连走路都困难,脚底的刺痛持续从地下冒出,有如行走在荆棘之上。这是一个绝好的象征。每一个内心修行者都必须走过这段荆棘之路,去寻找只属于自己的心灵家园,那些身体和心灵上留下的疤痕如同赐予他们的勋章。在这艰难的行走中,音乐给了她很多的慰藉和力量。深情的竹笛总是让她想起小时候“在乡间的小径上担水回家,每次都在竹林边驻足,似乎林子里会有欢声笑语传出来”,梦里田园,无比欢畅。歌者Russell Watson的嗓音具有无限的魔力,他只“用一句话,便把全世界孤独的心,都温暖了”,仿佛几个音符就可以托起一个世界。而奥立佛.香提用生命的鼓点让她“不知不觉地,已经放下了一切心理上的负累。那些阻碍我前进的理由,都被风一样吹远”。这些音乐仿佛一片片祥云,铺垫在她的脚底,让她忘记了疼痛,一种内在生命的欢喜伴着她安静地行走。在这行走的过程中,浮现了一些或高兴、或悲伤,或坚守或沉默的面孔,这里有她一生相伴的艺术家朋友,有诗歌写作上的知音,有认识和不认识、每天认真扮演好自己角色的芸芸众生。当她把笔触转向这些平凡而又可敬、可爱的人身上,她的语调是那么柔和,拣尽美好、温润的词语来无怨无悔地爱着他们。她写自己去养老院看寄娘,感叹于“我的寄娘老了,她不再记得所有的幸福和痛苦”(《去养老院看寄娘》),那是人事全消磨之后的空白与虚无,是面对生命徒然消逝的无奈与无助。有一段时间她被一个在枫桥路边卖香烛的老人吸引住了,每天早晨,她都要路过那里:“不管下雨,还是大热天,她依旧早早地坐在马路边,跟寒山寺保持着一段距离,守着她一个人的路口。不知道老人是因为家庭原因,还是因为寂寞,那么一把年纪,还要在马路边餐风露宿地做小生意。平时,倒也没有人去管她,我只见过一次,某个中年的城管,开车到她身边,跟她婉转地说,转去吧。苏州人把回家去说成转去。她竟然跟城管露出了一个调皮的笑容,还说等一歇我就转去了。”(《那些擦肩而过的灵魂》)这“一个调皮的笑容”实在惊艳,她用了长长的铺垫、用了很大的耐性按捺住自己,不要将它过早向我们和盘托出,它仿佛大雪封山之后绽放的一株红梅,一下就调动了所有的善意与感动。她还记得那些东山、西山的果农,“每到枇杷和杨梅桃子上市,总要挑上几篓沉重的水果,一路上挤几趟公交换几路不同的车次,到达那些她们从前常去的街巷。他们就是这样宠爱着苏州的城里人,即使那些人口袋里的钱没她们的多,她们每到这个季节,都要千里万里,把新鲜的水果送到城里。她们总是弱弱地不敢与别人对视,谦卑地缩着身子,怕自己的扁担,招惹来不客气的眼神。”(《挑一担杨梅的老妇人》)这些果农代表的是一种老老实实的生活,不管风里雨里总在路上,匍匐着、行走着,把一条路走到细入乡思愁肠,把一个生命走到烟尘之中。那种生命的谦卑,时时提前准备好的善良,在人世的风雨中放着光。
在这样兀自沉醉其中的回忆与怀想中,蔡猜经常表现出一种执著与天真,仿佛不谙世事,不知人间愁烦。她在《炎热夏季里的一个夜晚》里写道:“那天,我穿了一件旧衣服出门,去见朋友。我是有意穿着这样一件衣服出门的。首先是我喜欢,第二我还是喜欢。”它让我想起鲁迅的《秋夜》著名的“两颗枣树”,但是和鲁迅的冷峻不同,她是这样任性,这样专注于自我的内心,就像她对童年的回忆一样,哪怕世界已经地老天荒,她仍守着春暖花开的旧影。“艺术家的内心是顽固的”(《火车开往景德镇》),她早已经为自己写好了注脚。
有一年也许是儿时记忆的盅惑,蔡猜摘了很多桑葚来泡酒,邀友品尝。我常常想,那些又酸又甜的果实,在心形容器中浮浮沉沉浸泡久了,隐隐散发出的时间香味,在绵长的回忆中流散飘拨,真可谓是“一壶往事胸中浮”了。
思不群,原名周国红,男,79年生,安徽望江人,现居苏州。主要从事诗歌和评论写作,作品散见《诗歌月刊》《星星》《绿风》《扬子江》《天津诗人》《敦煌》《浙江作家》《南腔北调》《苏州文艺评论》《文学报》《中国书画报》等,编著有《苏州作家研究·车前子卷》(合作)。
秋水居为思不群个人公众号
人生少欢趣,何不逍遥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