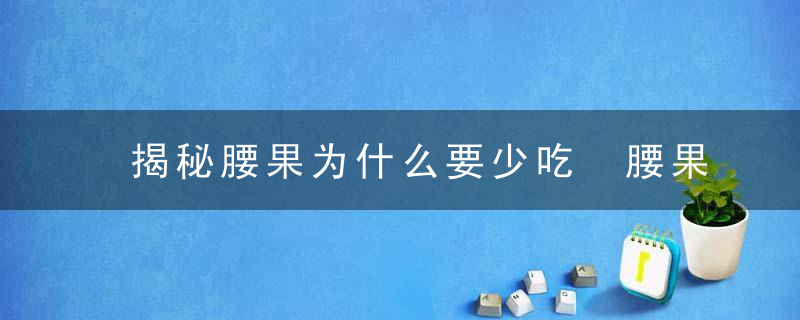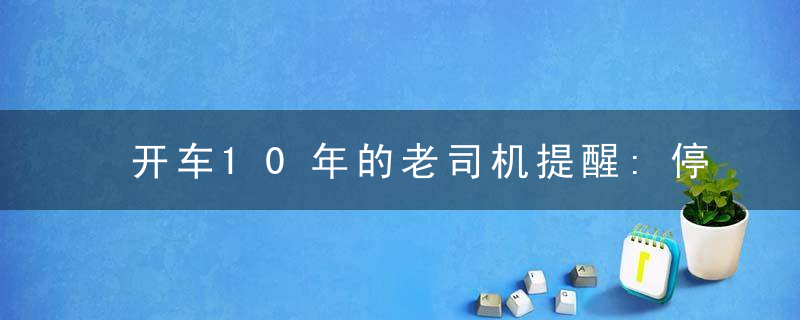何为诗意地栖居?

“人生此在即是被抛”,这句马丁·海德格尔的名言相信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1889年9月26日,被后世称为“存在主义大师”的海德格尔“被抛”于德国巴登州的梅斯基尔希镇,这个小镇位于阿雷曼地区与施瓦本地区之间,约翰·彼得·黑贝尔和荷尔德林分别出生于这两个地区,而他们均对海德格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海德格尔是当地天主教堂·马丁教堂的司事,从事较为低层次的神职工作。而就在海德格尔出生前不久,这座看似安静的小镇就发生了一场动荡的教派争端:旧天主教与罗马天主教之间的争端,旧天主教的人时常把罗马天主教派家庭出生的孩子称为“黑病鬼”,而海德格尔一家就属于罗马天主教派的一份子。当时的德国官方支持旧天主教派,因此老海德格尔携着家眷退出了当地的教堂。此后,斗争气氛渐渐减弱,在海德格尔6岁的时候,罗马天主教派又迁回了当地的教堂。而重归故地之后,海德格尔出人意料地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旧天主教派的司事觉得若将教堂钥匙交还给老海德格尔会十分尴尬,而此时6岁的海德格尔正在教堂前玩耍,于是司事就把钥匙塞到了他的小手里。这就是小马丁的童年世界,他由此扮演了一个“钥匙”般的关键角色,为大家开启希望与信仰的大门。
海德格尔中学阶段学业十分优异,而在进入大学之后,他本想着自己能成为一名牧师,由此就进入了弗莱堡大学神学系进行研习。此后却由于身体的缘故而不得不休学回家,被迫中断了神学的学习。大约半年过后,海德格尔身体康复了,便重回弗莱堡大学,但他意识到他之前专注于神学,是由于倾慕于神学中的哲学成分,这时他进入了数学和自然科学学院。在此期间,海德格尔阅读了大量的哲学、逻辑学著作,尤其是他后来的老师胡塞尔的著作。他在图书馆借了一本《逻辑研究》,这本书在他的书桌上一放就是两年。尽管晦涩,但这段时间的学习还是给海德格尔的独特的现象学方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胡塞尔转到弗莱堡大学任教,海德格尔顺利成为了他的研究助手,他们之间形成了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胡塞尔把海德格尔当做其最得意的门生,并且几乎是把其当做现象学界与自己平起平坐的研究者。
后来,经过胡塞尔的引荐,海德格尔顺利成为了马堡大学的正式教师。此时他的思想脉络已经初步运思而成,直到在1927年完成哲学巨作《存在与时间》。这一时期,海德格尔的思考重心无疑是要“抢救生活”,要把“生活”从形而上学那一错误的彼岸拉回来。他洞察到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的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导致了生活与世界的分离,从柏拉图以降的形而上学历史不过是“遗忘存在的历史”。为了破除主客体分离的哲学困境,海德格尔提出了“此在”(Dasein),“此在”的人不是主体,而是一种境域化的、完全投入实际生活经验的一个“人”。这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发生现象学上的“人”。由此“存在”才能通过这个“存在者”得以打开。传统形而上学的认识论一般认为,主体生活于这个世界就是面对着一个客体世界,它独立于人自身,人看起来不过是聚合的“众存在者”中的一个存在者而已。而海德格尔通过强调人的“在世存在”(In-der-Welt-sein),主客之间不再分离,在存在论上确立“此在的世界”,“在世存在”的内含是:没有人就没有世界,没有世界就没有人,人和世界从根本上已经黏合在一块了。人的“在世存在”其实就是人和世界的“相互维持”,人以一种完全投入的方式纵情于这个世界之中,被这个世界打动得无以复加。海德格尔立足于“此在”来清算过去的形而上学传统,这充满了“六经注我”的味道,他在课堂上讲授《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之时,如果你期待他给你讲授一门“中规中矩”的亚里士多德导论,那你可就错了,他对亚氏的提及无非是要指出:西方哲学史向来所从事的工作从根本上与哲学无关,因为与“存在”无关。
在这一时期,海德格尔可以称得上是十分荣耀,他没有与胡塞尔发生争执,也没有与纳粹产生任何联系。直到1933年纳粹上台,此时海德格尔似乎坚信自己可以通过纳粹来改造西方意识形态,于是他加入了纳粹党,出任了弗莱堡大学的校长。而“好景不长”,这段经历持续了不到一年,海德格尔便与纳粹产生了不小了争执,辞退了职务重新返回教席。然而这段“不光彩”的经历从此伴随了他的一生,哲学家的“政治幼稚病”被后世许多人提及,海德格尔的这一人生污点再也抹不去了。
出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时的海德格尔 由此我们进入了“海德格尔的后期”。在他的后期,他着重讨论语言问题、技术问题,艺术与诗开始成为他的探究中的重要论题。可以说,后期的海德格尔从“哲学”转向了“思”,从“此在”转向了“存在之真理”。他看到形而上学对“存在”之真正开端(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思想)的打断,而到了现代,他认为形而上学趋于终结,而以荷尔德林为主的诗人已然开启了“另外一个开端”,一个非形而上学的诗性开端。这一时期,开始通过“诗与艺术的沉思”来思“存在之真理”,进而又落实到对技术之本质的沉思。艺术是一种具有原始性意义的“除蔽”,技术则是对艺术原始解蔽的“扩建”(Ausbau)。他重视诗人的作用,作诗就是“度量”(Messen),这使得人在天地之间获得了稳靠的根基。语言具有根植性,语言与大地(Physis)归为一体。作诗并不飞跃和超出大地,作诗首先把人带向大地,使人归属于大地,从而使人进入栖居之中。这就是所谓的“诗意地栖居”。
1976年5月26日,海德格尔与世长辞,在他故乡的教堂举行了安葬仪式。他要求在墓碑上刻上一颗星星,星星象征着光明,从黑暗中除蔽而出,这显然代表了海氏的真理观。海德格尔的一生追索真理,却也陷入过各种困境,真理的追索之路漫长而险要。
(责编 海逾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