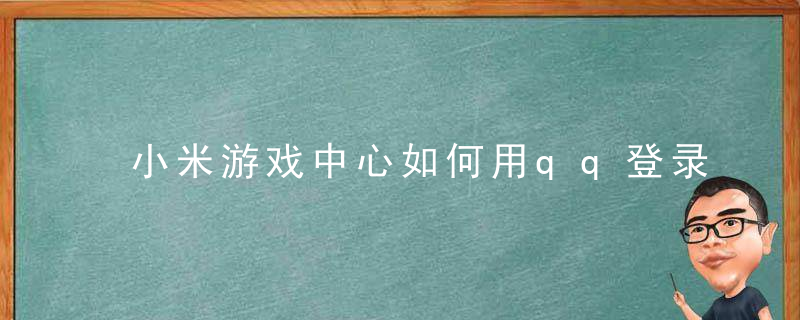没有东北话,还能做成有趣的春晚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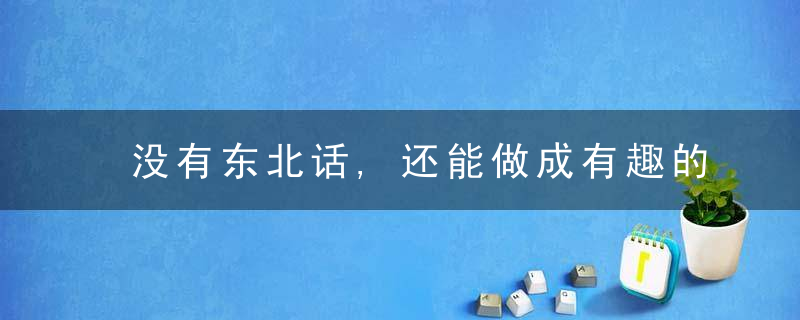
一
2011年春节,我是在广州过的。
除夕夜十一点多,岳父颇有倦意。劝他休息,不肯。他说要等赵本山。这才知道,每年春晚,赵本山的小品他都必看,因为“就这么一个好笑的节目”。
岳父祖居潮汕,年轻时在青岛当兵,本可以在当地提干,他毫不犹豫跑回广州,因为被青岛的“酷寒”吓到了。他并不喜欢北方。
我第一次意识到,在最南的南方,还是有人喜欢看春晚。倒不奇怪,今年春节去台湾,听说台湾也有春晚的拥趸。难得的是,居然喜欢看赵本山。
说起来,可能是东北人在文化上的不自信——或者正面点说,是“自知之明”,虽然近三十年东北出的写字人并不少,但很多年里,我还是自认东北的文化不大上得台面。而且朋友圈里认识的南方人士,多来自媒体圈、文化圈,尤其喜欢公开宣示自己不看春晚或不看东北小品的正确性。这种针对北方文化的焦虑或南方文化主体性的自觉,说人话,就是矫情,当然也矫情得很有道理。
不过那天,我严肃地想了想,这部分文化自觉,是不是就能代表整个南方的态度?或者说,怎么解释那些愿意在东北口音的小品中收获快乐的南方土著呢?
那一年,是赵本山最后一次登上春晚舞台。完全出于巧合,那年后,我也没再看过春晚。
2011年春晚,小品《同桌的你》
没有赵本山的春晚仍旧是春晚,尽管偶尔能在身边和网络上,碰见对他的“怀念”。没有赵本山的春晚,不是没有东北话的春晚,比如潘长江,仍然很活跃。只不过,东北方言的小品,不再那么强势扎眼而已。
看起来,像是一个时代的谢幕,如果以赵本山在春晚的艺术生命史来断代。不过,东北方言为什么能在春晚有这样一段历史?东北方言与春晚,会不会就此渐行渐远?
我的老家在吉林,与赵本山的老家辽宁开原,在东北官话分区上,同属吉沈片的通溪小片,所以对以赵本山为代表的东北方言小品,熟悉是熟悉的。不过说来惭愧,本人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并不算真会说东北话。
此话从何说起呢?
我自小是个“书呆子”,与同龄的孩子玩耍极少。我的词语,很多是书面的,或者是普通话的。所以虽然我每个字的发音都是东北话的发音,日常东北话的很多词语,我却不会熟练使用。身在东北时尚且如此,离开东北后,就更不必说了。
这关系到东北话的一个重要特点:东北话是活的语言。
这话说的,中国还有死的语言吗?
倒不至于。中国大部分方言,多多少少都在“活”着。只不过,相比之下,东北方言由于历史短,还在不断成长、更新,它的“活气”,要足得多。
“活”到什么程度呢?我记得,只要有三五年没回东北,就会对交流产生某种障碍。比如说,有一些你从来没听说过的词汇,就加进来了。这些词汇,可能来自外语,可能来自普通话的某个新词,可能来自某个电视剧,可能来自某个娱乐节目,也可能来自谁都说不清楚的某处。
总之,它来了,作为东北话,藐视着你,考察着你。在那一刻,作为一个东北人,注定是有些羞愧,有些忐忑的,当然更不可能开口问这个词什么意思,只好佯装了然于胸,调动十万条神经评测新词到底何解,一边在对话中旁敲侧击验证,一旦整准,方能豁然开朗,刚刚龟缩的近乡之情倏地雄起了。
一些不那么活的方言,对于新概念新表达的引入,就没那么急迫那么肆无忌惮,和现实生活的结合度,就会差那么点意思。
我觉得,“活”,是东北话的最重要特点。尤其是因为这个特点,东北话得以占据很多本来应该被普通话占据的市场。与东北话一比,普通话虽然字词发音相去无几,却显得干瘪无味、面目可憎。
二
然而东北话能长期占据春晚语言类节目高地,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特点或优点。
比如东北话用词,喜欢押韵,也喜欢用叠词:唧唧歪歪、大大咧咧、疯疯傻傻……
网络图片:东北话“音译”版
对此贡献最大的,是二人转。
小时候,大约1986年上初中前,寒暑假期都在姥爷(外公)家。家里有个唱机,不少唱片,部分是流行歌曲,更多的,是二人转。假期家里人都出去干活,我有时一个人搭上唱针,一个个听过去:《马前泼水》、《猪八戒拱地》、《西厢记》……
走笔至此,有些唱段还是可以从记忆中毫无滞碍流淌出来:
“一代圣贤孔夫子,二郎担山赶太阳,三气周瑜诸葛亮,四姐临凡配夫郎,伍子胥打马沙江过,六国不敌秦始皇,七夕牛郎会织女,是八仙过海笑脸扬,九里山前数韩信,十面埋伏楚霸王……”
这是《西厢记》里的“观画”。画还有好多,记不过来。
又或者,“哧溜溜他拱开了四垄地呀,栽点地瓜再种点花生啊,哧溜溜他拱开了五垄地呀,拱得八戒鼻子疼啊,哧溜溜他拱开了六垄地呀,八戒的耳朵直卜愣啊,哧溜溜他拱开了七垄地呀,八戒的脑袋直嗡嗡啊,哧溜溜他拱开了八垄地,猪八戒我趴在地上把腿蹬……”
这是《猪八戒拱地》,猪八戒被收拾的段子。
资料图:二人转的经典曲目
唱词不能表现的,是二人转著名的“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嗨嗨”,弹指之间,余音在耳。
二人转在东北的影响,在相当多年里,是远远超出外人所知的。在曾经漫长寒冷的冬季,二人转就是电,就是光,就是惟一的神话……
而且,二人转也不是只有一种。十多年前,姥姥已经近八十岁,我听说她还是喜欢听二人转,回乡时专门买了一整套传统二人转光盘给她送去。过段时间去探视,却发现已经被打入冷宫。说:“太正经,不好听。”
不正经的剧目,我也听了,并不是真的不正经,但是表现形式,是与观众有更多互动的,演员动不动就间离出去扯点闲嗑——有点像今天的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区别。
顺着这个话说,就容易理解了。与今天的新媒体一样,民间二人转,更讲究接地气,“不隔语、不隔音,最要紧的是不隔心”,是标准的“民间写——写民间,民间演——演民间,民间唱——唱民间”。甭管什么素材,都能烹制成东北味儿。二人转戏文里,皇帝在宴请大臣时会说:“饼是娘娘亲手烙,待寡人与你卷上大葱”。苏州闺阁小姐王二姐思夫,表现是“拆炕砸锅”。
二人转和东北人,真是天造地设的般配。
毫不意外,东北话大量的叠词和押韵,主要受二人转影响。东北话的特点,也自然地成了东北小品的特点。东北人的日常表达,与小品的距离,本来就相当小——可以参见《乡村爱情》系列。那里演员“演”的成分,在东北人看来,真是可以忽略不计。
资料图:《乡村爱情》剧照
三
但是二人转影响东北话,并不止词语的表面,影响东北话的,也不止二人转一种曲艺形式。
今天的相声界,当然只认郭德纲的天津。但很少有人知道,东北相声的渊源也算久长。沈阳和北京、天津并称为相声的三个发源地。
再如评书。东北的评书艺人,怎么说呢,四大评书魁首,袁阔成、田连元、单田方、刘兰芳,那可全是东北的。
更早,还有哨歌。这是1980年代以前,东北人的一种交流、交际形式。早前,东北民间家家有哨本,记录“俏皮嗑”。哨歌场景多样,“大车老板住店、买卖开张、赶集上店、姐夫小舅相遇、亲家聚首、恭迎客套”。
估计哨歌知道的人少,举个例子吧。有个《哨车老板儿》,是这么说的:
“我和你说一说,当年就发科。发科就买马,买马就栓车。拴车上营口,营口挣钱多。一去拉白面,回来拉海蘑。刚下虎头岭,辕马跑了坡。大车翻进沟,马腿被砸折。又遇土匪抢,赔进了货和车……”
哨歌现下不再流行,但东北小品、二人转中,都有哨歌的身影。东北人日常说话喜欢“一套儿一套儿的”,讲求合辙压韵,与哨歌也有直接关系。
这些曲艺形式的另一方面影响,是语言的幽默、形象、简洁。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彼时的曲艺,都是真正靠市场吃饭的,不能把人逗乐,咋活?
语言简洁,就容易听懂。形象,就必须用大量比喻。像“没有弯弯肚子,你别吃镰刀头!又没让你去,你逞的哪份能?”这种。
幽默,更是根本。东北二人转及小品对于幽默元素和技巧的应用,是全方位的。当然,我也没有真正研究过。论文不少,其中一篇《东北方言幽默研究》,居然是温州大学的硕士毕业论文。
除了制造错位、落差、曲解等常见技巧,还有一些幽默风格,是东北小品相对特有的。比方自贬式幽默。通过贬低自己来抬高他人,把幽默的矛头直指自己,使自己成为笑柄。赵本山那句“瞎么杵子上南极根本找不着北,脑血栓练下叉根本劈不开腿,大马猴穿旗袍根本就看不出美,你让潘长江去吻郑海霞,根本就够不着嘴。”使的就是这一手。
弗洛伊德说:“矛头指向自己的幽默是一种成熟的幽默,因为它显示了说话人自我疏远的能力……也同时体现了说话人的另一项美德,即笑谈困难和克服困难的能力。”这句话,大概指明了这种自贬式幽默,从何而来。
由于流民特质,民间东北文化较少受意识形态影响,甚至自觉地消解语言中的意识形态内容,解构主流的“高雅”。在《乡村爱情2》中,有这么一段:“这话谢广坤不乐意听了,他说:谢永强,你别小看了刘一水,刘一水什么人,用句书面语言说是你的竞争对手,用句庄户话说是你的情敌,你怎么这么沉得住气呢?”庄户话与书面语的对比,就是有意识的解构。
因为日常影响至深,幽默地唠嗑,对大部分东北人来说,都是童子功,是本能。幽默的价值已经不止是为了引发哄堂大笑,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东北日常交际中的“礼”,承担的是“理”与“法”的缺失。
四
除了曲艺文化影响,还有一些因素,也是塑造东北话面貌的原动力。
尽管古早以前,就有“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的说法,但当代东北人的形成史,特别是在柳条边以北,其实还是很晚近的事。
历史原因,这里的很大一块,曾经近乎空地,在很短时间里,有多个族群,汉族、满族、蒙古族、朝鲜族,以及俄罗斯人、日本人,碰撞聚会,语言互相影响,某种融合,就不可避免。重要的是,在当时,各方的文化是相对均衡的,不是谁简单融入谁、压倒谁的问题。这和在华南,小规模外来人口只能面临被粤语“同化”,境况就不一样。
东北话里,各少数民族的语言遗留很多,尤其是满语、蒙语和朝鲜语。哈尔滨就不说了。比如我老家,吉林省梅河口市,柳条边以北的一个城市,以河得名。我一直以为“梅河”是一个相当风雅的汉语词汇,很晚才知道,“梅河”其实是满语“梅黑河”的音译。
多方均衡下的族群交流,必定会呈现出一种倾向,就是寻找各族群的最大公约数,选择最简单的发音、语汇,最终形成都能接受的新的方言。
小品《不差钱》剧照
所以,可以看到,在内地类似的条件下,只要参与各方中有一方是北方语系,又不能随便把这方吸收同化掉,就会按照这种逻辑演进,发音更简单的北方语系就会占优,比如在四川发生过的。因为交流需要嘛,一定走最高效直接的例子。另一个例子,可能是台湾。一个东北人在台湾实际上是没有任何语言障碍的——可能比一些南方的大陆来客还感觉宾至如归。
一些南方同学曾对此表达了极大的不满,包括依据语言因素考证什么“崖山之后无中国”之类。其实呢,人还在,只是话变了,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多数情况下,这种走向有利于沟通。至于是不是有利于思考,有利于记述,是另外一回事了。
最简单的表达,意味着最短的词,最简单的声调,最形象的比喻,而且,最好,足够幽默。
后来,在西藏,与藏族、门巴族群众接触比较多,很快就发现了非常类似的情况。不同民族在互相沟通时,一定是选择最形象的比喻、最简短的词汇、最夸张的语调。比如说在某个村,一位藏民向导,拉肚子不能上山,他不会说“拉肚子”,就来说自己“屁股下雨了”。自然,这个词很快就在小范围流行起来。反过来,汉族同事,也会有意用藏语“打电话”与“啪啪啪之事”之间的谐音,和老百姓开玩笑——这是不需要任何人教的,而且效果奇好。
五
越是多个语种人群需要迅速沟通交流的地域,他们的方言,特别是早期方言,就越能体现这些特点:简单、直接、生动、幽默。
中原地带,比如山东和河南,按地理位置看,在春晚上占据主流的,肯定是河南话或山东话吧?然而不是。因为这里语言已经稳定,逐渐开始复杂化,对于伦理的要求也更强,势必影响到鲜活生猛的表达。
而与东北更为近似的区域,是四川与西北。所以西北人在春晚上,一直占据语言节目第二的地位。相比之下,四川话“活语言”的气质也非常强,同在长江沿线,川人的幽默感与湘鄂赣等地,相去何其远。正常来说,四川话应该在中国的语言类节目中,有更大的比重。
有些地域差别,就像少数民族喝了酒都能歌善舞,就像俄罗斯人非喝伏特加,既有文化基因,又有族群偏好,不论孰优孰劣,多样性是现实存在的。
那么,这种气质的东北话,对春晚意味着什么?
春晚从一出世,就有明确的使命。它是用于宣示统一,宣示完整,宣示最新的融合,是寻找最大公约数的。它不是用来表现传统久远(粤语)或语音优美(吴语)的。而东北话,有普通话的好处,而没有普通话的僵硬,它简单又形象,幽默又开放,它就是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的语言最大公约数。因此,要我看,只要春晚还想保持语言类节目的吸引力,不管有没有赵本山,恐怕都不能没有东北话。
东北人能把网络直播做成“最大轻工业”,不是偶然的——那也是需要最大公约数的舞台。
可这正是威胁所在。真正可以替代东北话“最大公约数”地位的,我觉得,会是网络语言,主要基于普通话的网络语言。
它们的很多特点几乎一样。某些自媒体十万加文,其实就是另一种东北小品的变体。甚至都不能再用雅俗来区分:“屌丝”“绿茶婊”“装B”等,与东北民间二人转的气质不相伯仲。它们应对的使命、承接的功能,都有很大相似之处,不同的是,网络语言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并且首先以文字形式传播。但是,它的生命力,已经非常强大,越来越接近一种新的、主要基于普通话的“活”的语言体系。东北话可能还会受到一些基于地域的抵制,而网络语言面对的则可能是断无胜算的基于年龄和阶层的抗拒。在此过程中,东北话一定还会贡献不少的话语基因,但它在春晚的功能,可能会没那么不可替代了。
资料图:2018年春晚开场歌舞
在东北,有句俏皮嗑,“没有你这臭鸡蛋,还做不成槽子糕了?”正确使用方式,必须问号收尾。“槽子糕”,是老式蛋糕。意思明摆着:别觉着离了你地球就不转了,其实啥事都不耽误。
那么,没有东北话这臭鸡蛋,还能不能做成一个有趣的春晚槽子糕?
我的回答是,这不重要,因为槽子糕还有没有人吃,谁也不知道。
参考资料:
徐杰舜主编 《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
高永龙 《东北话词典》
阿成 《哈尔滨人》
杨怀波 《东北方言幽默研究》
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