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街坊邻里赶走的“抗拆领袖”丨人间

吴国强悻悻离开的时候含混甩下一句话:“你老K还不是一样在等着碰开发商的瓷儿?”
配图 |《老兽》剧照
每个城市还存在的老街,不外乎两种情况:刻意想要保留的和想拆迁却谈不拢的。我老家县城的“六安街”在2018年之前属于后者。
这条不长的老街,因街上有座建于宋代的“六安庙”而得名。街上住着二三十户人家,从街尾往东过了“六安桥”,就是市中心了。
前些年,县城里的红木产业迅速崛起,嗅到商机,大兴土木,在离城区不到五公里的郊镇,仿造唐朝大明宫的样式,建了个“红木工艺博览城”,对外号称国家4A级景点,也算吸引了不少游客。经常有外地来的游客在城区闲逛,只要逛到六安街,一般就会边走边感叹:“哇!这儿保留得好完整,好有年代感!”
这话要是被正在门口泡茶聊天的老K听到,保管拿眼冷冷一瞥,把茶杯往桌上一礅,冲来人说:“保留个屁!年代感个屁!啥都不懂,瞎嚷嚷个啥?”
老K就属于拆迁“谈不拢”的一份子。当然,这条街还不只老K一个钉子户,在老K的组织号召下,这儿已经成了一排“钉子”。照老K的话说,这叫“众志成城”,照拆迁队的话说,那就是“这排房子的地基已扎进六安河底了,很难起掉”。
前些年,开发商派人来六安街找老K商谈过几次拆迁赔款的事,但每次都无功而返。无奈,开发商只得先把六安街周边的几条老街先“瓦解”了。这一来,六安街的“老”就显得格外突出。
敬酒不吃,开发商便请求配合,来硬的。2014年夏秋之交,一号台风刚过不久,乌云低沉,阴风怒号,无数警车、挖掘机、推土机轰鸣着聚集在了六安桥桥头。老K闻到风声,挨家挨户叫人,不顾自己一把年纪,赤膊扛了罐液化气,率队直冲到桥头,把手中的打火机气阀开到最大,不时点起灭掉,风吹得火舌飘摇不定,犹如眼下的六安街。
没想到还真管用,眼里、手上一起冒着火的老K,硬是吓退了一批钢盔警棍的拆迁队,对峙了一阵子,拆迁队为首的接了个电话,一辆辆车就都掉头回去了。
那次行动老K风头无俩,理所当然成了六安街“抗拆”的精神领袖。
我一直以为,老K是那种传说中喜欢沉浸在旧时光、有情怀的人,所以愿意誓死捍卫六安街。有次跟他喝茶,我刚盛赞完他,没想到他一脸不屑:“有个屁情怀,还不是因为价钱谈不来!开发商想抢钱?没门!”
老K看着我,不停地用食指叩击茶几:“猴子,我跟你说,我们这儿达成共识了,没到那预期,就算指甲盖这么大点儿地,我也拿炸药包守着!”
可自从老K勇退拆迁队后,开发商似乎就把六安街给忘了,不再找人谈判,也不用强,就如这条街不存在似的,一心只加紧周边的建设。
这反倒让老K有点坐不住了。眼瞧着周边一条条老街都变成了高楼,唯独六安街还夹在里头,青石板路窄得两辆车会车都费劲,房子是木柱子木门板,光线昏暗,电路凌乱。现在的六安街既不像三坊七巷,又不如徽派民居,古不古新不新,不伦不类。
“操!也不知道开发商使了什么手段,那些人乖乖就让拆了,就那点打发要饭的钱,至于吗?”老K每早站在门口刷牙时,总是满嘴泡沫地跟左邻右舍叨上两句,然后再狠狠地甩甩牙刷,望了望对面新盖的楼盘,心有不甘地踅进老屋。
可偏偏总有一些已经拆迁、住进新楼的老街坊回来酸老K:“还是你能守啊,现在的房价是越来越高了,守下来就是个大价钱,可惜当年我们那条街没你这样的头儿……”
刚开始老K没听出什么,点头嗤之:“你们这帮人,软骨头,一点好处就把房子拱手给了人家,等着后悔吧!”再后来,见开发商迟迟没有动作,老K答起来就没好气:“你他妈啰哩八嗦什么,损我呢?!我这房子给你,你的给我,咱换不?”
话到这份上,来人也知趣,叹了口气劝道:“K哥,差不多行了,开发商的钱也不是那么好拿的,早也拆晚也拆,你还真能带头守到老啊?你愿意,住这块儿的小年轻还不定愿意呢!”
这话说得极是,老K心知肚明。
前阵子,邻里已经开始有意见了。说老K价钱没谈好,反倒搞成一潭死水,万一开发商放弃了,总不能守着这条老街过一辈子吧?有几个等着买房结婚的年轻人更是一肚子不爽,人前虽还是尊他一声K叔,人后却都说他:“死老K,真以为自己还是老大啊?”
老K确实是做了一辈子的“老大”。
说起来,老K并非六安街的“土著”,在来这儿之前,他是我乡下老家的邻居。
老K50年代生人,属马,中等身材,结实精瘦,说起话来粗喉大嗓。70年代当过侦查兵,上过战场,也算是从堆满尸体的战壕里爬出来的人。他动不动就喜欢撩起衣服给我们看他后背上的两个圆圆的弹痕,说自己命大福大,只挨了两粒“花生米”。放下衣服,他总会很诗意地说,这两个弹痕一定是那些牺牲的战友的眼睛附着的,要他帮他们看看这“新世界”。
“现在社会变化真是快啊,快得我眼睛都跟不上了!”这是老K最喜欢感叹的一句话。那时候,老K刚学会用微信,经常跟远在新西兰的小外孙女视频。
80年代初,老K光荣退伍,回乡时不仅带了一身军功章,还带了一身本事。据村人说,老K不但拳脚功夫 “一人能打八个”,而且还会“轻功”,上个屋瓦如履平地。老K刚回来那阵,跟着村里的一个老师傅学泥水匠,上墙从不走棚架,而是像只猴子似的七手八脚就上去了。不过,老K后来没当成泥水匠,而是经人引荐,当了一阵子村干部。再后来又嫌没意思,便混社会去了。
那年月,出人头地的捷径还是靠拳脚说话。二十多岁的老K很快就从自己村子打到了镇上,再打到县城,一路打出了名声,使得村子也跟着声名大噪,老K自然也坐上村里老大的席位。
成名后,老K给村子定下规矩:“同村人不许欺负同村人,要是邻村来犯,一致对外。”那个年代,村人外出要是不小心惹上事,只要报上是老K同村的亲戚,一般对方都会给个面子。
老K名号如日中天那会儿,我还在上小学。每天放学,经常能看到一帮十七八岁的同村后生在后院里跟着老K习武,只是可苦了那棵老龙眼树,不但枝杈上挂着自制的吊环,树干上还被钉了个木靶子,用来练习飞镖,后院的土场子上,还有一堆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石锁和石碌碡。一练习起来,尘土飞扬,鸡飞狗跳。
老K的徒弟很多,除了村里那些四处惹事的年轻人,还有慕名来“交流”的外村人。这些人跟老K一样,也是各自村里的成名人物,一来二去,全混成了朋友。
在老K教过的一干徒弟中,三教九流都有:有在“严打”中吃了“花生米”的,也有考上大学后在异乡混上个一官半职的,有在开“摩的”的,也有在开KTV和足浴店的,据说还有几个,现在已经是或者了。
我当年因为常趴在墙头上观看,老K一时兴起就教了我套猴拳。猴拳是老K自认最得意的拳法,据说还在部队里拿过大奖。老K打得形神俱备,我学得十分刻苦,拳不离手,尽得老K衣钵——后来我还在学校的晚会上表演过,搞得那些校霸以为我很有功夫,从此不敢惹我。
正是因了这层关系,尽管我后来四处奔波,但跟老K间还是常有联系。现在,我已人到中年,油腻肥胖,可老K见到我,还是习惯地叫我“猴子”,我没有正式拜师,有时叫他“师父”,有时直接叫他“老K”。
90年代初的时候,老K的结发妻子三十五岁那年得了癌症离世,给他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老K为了孩子的教育,便把儿女转去县城的实验小学上学,在六安街买下了现在的老宅。
这老宅少说也有好几十年历史了,土木结构,样式老旧,前房主要举家迁去美国定居才出售。老K买下它,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便宜,临近学区;再者,老K有点迷信,知道前房主一家子都是学霸,就有点想让自家孩子也沾点才气的意思;最重要的一点,这条街上还住着几个他当年一起“打天下”的兄弟。
老K初来乍到的时候,当地有个混儿听到他的名气很是不服气,硬是要找老K单挑,老K再三推辞后还是答应了。比武约在六安桥边的榕树下,结果俩人打着打着就上了桥,那混儿后退的时候脚下一滑,眼看就要掉下六安桥,老K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他的脚踝,硬是扎稳马步悬空把个近二百斤的汉子提了上来。从此,老K一战成名,那混儿又羞又愧,心服口服,日后逢人就说“老K才是六安街真正的老大”。
老K来六安街后又娶了一个女人,姓张,我管她叫张姨。老K当时为带孩子一筹莫展,原打算请张姨过来当个保姆,没想到日久生情,后来结了夫妻。
或许是老K买的房子真的风水好,总之,两个孩子后来都考上了重点大学。大儿子现在在福州自己创业,据说忙得都没空要孩子;女儿更牛,留学新西兰后定居下来,几年才难得回来一次。
老K以前的那帮兄弟们一个个先后离开了六安街,不是搬去了别的地方,就是去外地帮儿女们看孩子,只有春节的时候,才会赶回来凑凑热闹。唯独老K没地方可去,去福州,孙子还没抱上,只能给儿子添堵,去女儿那儿?老K去过一次,说待不到三天就想回来:“那鬼地方,冷清得很,还不如咱乡下热闹呢!洋话我就会个‘哈啰’,找谁聊天去?”
几年前,风闻旧城改造的步伐已经踏到了六安街,每年春节,老K的那些兄弟便会找上老K,一致说:“咱六安街一定得齐心协力地守着,不能让开发商轻易收了去。一辈子就等来一回拆迁,怎么说也得争个三瓜俩枣,公家的钱,不拿白不拿。”
“有你K哥在,我们在外都放心,只要你觉得价钱合适,出得了手,我们也不二话。”
老K其实不差钱,90年代那会儿凭着“江湖名声”,他倒腾过假烟,垄断过客运,还承包过山头,贩卖过木材,近些年又参股了徒弟在县城的几家KTV,分红可观。总之,黑金白金都挣,儿子福州的房子,女儿的留学费用,全是老K一人搞定。老K还把老家的旧房子翻了,盖上大别墅,让不愿来城里的老母亲享福。
老K两口倒是住惯了六安街的房子,要说感情嘛,那也是真有,但这显然占不到老K抗拆的一成理由。老K跟我说:“猴子,实话实说,也不全是钱的事,我那房子不大,能多拿几个钱?”
老K拼了老命抗拆,或许更多是出于骨子里残存的“个人英雄主义”。
这些年老K闲来无事,看了很多关于拆迁的社会新闻,在他看来,强拆的个个都是坏蛋,而抗拆的,不论成败,个个都是悲情英雄。认定了这点,老K就想:怎么也得抗一抗嘛,说不定就真的比别的街多赔了呢?况且,兄弟们那么信任我,怎么着都要出头的嘛,我老K是从战壕里捡了条命回来的人,这些临时组成的乌合之众,我怕他们个鸟?
可老K怎么也没想到,两年前“击退”拆迁队后,一切就都风平浪静了。非但筹划的好多对抗方案都无用武之地,还让自己落下了好大的埋怨,这让他焦虑。
他终于忍不住,问了一个当县的徒弟关于六安街拆迁的事儿,得到的答复是,县里决定暂时不管这块了,“六安街的人个个漫天要价,抗拆的头儿又是个老兵,有点麻烦,万一失手影响不好,先放着”。
徒弟带回来的话让老K很意外,不知道是该开心还是该别扭。
儿女知道了老K的“抗拆事迹”后,也是一肚子埋怨:“老头子,一把年纪了,留着清福不享,当哪门子抗拆英雄啊?人家多少人都等着拆迁安置呢,你偏强出头,现在好了,不管不问了,自己惹来一身怨,再撑下去,早晚得被口水淹死。”
老K问我该怎么办好。我说真想拆还不简单,女追男隔层纱,自己去找拆迁队谈,就按政策来,保证一下子就搞定了。
我说这话其实也是开开玩笑,可老K听了却很认真地想了想,说:“不行不行,我拉不下这个脸,大家还以为我背后收了开发商多少好处了呢!”
2016年中秋,我提了盒月饼去看望老K。老K对我摆摆手说:“哎,猴子,学人送什么月饼,甜的东西我无福消受。”我这才想起他之前跟我说过,他年前体检的时候查出了糖尿病。
老K看上去瘦了许多,有点疲惫。他说打算回去乡下老家住上一年半载,陪陪老母亲,至于拆迁的事儿,他打算交给六安街的老傅全权去处理。老傅是个文化人,是省内一家大型钢铁厂退休下来的老会计。
“他能谈下来多少钱就多少钱,反正我是不打算再管这事儿了。”
2016年国庆前后,我接到朋友发来的微信,说老K被人砍了,现在正在县医院的急诊室里,还好伤势不是很严重。
其时,我正在外地出差,听到消息赶紧给老K发了个短信问安,说自己一回来就过去看他。
我到县医院的时候,老K正侧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脸正对着门。见我来了,一手接过张姨削好的苹果就转递给了我。我连忙摆手,老K却执意要我接过,说自己吃腻了,这几天大大小小老有人送果篮来。
“你也是,买什么水果花篮,全是些烂果子,尽花钱。”老K大着嗓门说。
老K的伤并无大碍,背后被人砍了一刀,缝了二十多针。老K叫张姨撩起竖纹住院服,示意我过来看伤口,厚厚的纱布从腰间缠过再绕过肩膀,隐隐约约透出的暗红色血迹就在他那两个弹痕附近,像个惊叹号。
老K苦笑了下:“想不到活到一把年纪了还会被人砍,打仗的时候天天闻血腥味,回来打打杀杀也没这样流过血,这下倒好,还没跟拆迁队的人干,倒差点被邻居的一刀要了老命。”
老K是被他邻居王二妹的独子吴国强用菜刀砍伤的。吴国强三十岁出头,是个六安街的小混混,没干过什么正经工作,不是在这家红木厂做两天甩膀子走人,就是在那家厂子因偷盗木料被开除出去。后来说想跟人合股倒腾红木买卖,逼王二妹把棺材本都搬了出来,没想到半年之内就被他赌博输个精光。老K看在邻居的份上,说过吴国强几句重话,吴国强表面虽没说什么,背地里早就烦得要死。
有一次,吴国强在六安街瞄上了辆外地车,便找了个机会碰瓷儿。这事让老K看到了,不但帮着外地人作证,还把吴国强狠批了一顿,说有本事的年轻人谁会干这营生。
“你这是在丢你爸的脸!”老K毫不客气。
吴国强悻悻离开的时候含混甩下一句话:“你老K还不是一样在等着碰开发商的瓷儿?”
这话让老K暗地伤心了好久。
后来吴国强谈了个女朋友,这女的本是冲着王二妹老宅要拆迁来的,初始小情侣还觉得有老K在,可能会赔个好价钱,不料这事儿一次次地没谈成,女孩失了耐心,甩了吴国强走了。
这一来,吴国强就更恨老K。国庆节期间的某个晚上,吴国强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回来时喝得醉醺醺的,一路上越想越气,觉得自己讨不到老婆全是拜老K所赐,最后竟从厨房摸了把菜刀杀了过去。
“那小子来真的,一刀朝我头上劈过来,幸好我练过,虽然我现在老了点,但动作还是没忘掉。倒霉被一个橱柜挡着,没闪利索,要不然,凭吴国强那小子,十把刀也砍不到我!”老K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一边说一边下意识做着动作,伤口撕扯得他“哦哦”叫出声来。
“好了,别逞能了,要不是老傅赶过来,你这会儿就被吴国强‘光荣’了。”张姨白了他一眼,“猴子,你劝劝你师父,拆迁这事儿他就别管了,免得我成天提心吊胆的。现在我不是怕拆迁队使坏,就是怕那些等着分房的小年轻扛不住了,找你师父麻烦。”
“师父不是说,要回乡下避避吗?”我问。
“这不刚想走吗?吴国强那小子就等不及了。”老K一脸苦笑,“他砍我的那晚上,我正收拾行李呢!”
老K很快痊愈出院,吴国强因故意伤害罪,被判两年。
这事儿过后,王二妹每天都噙着眼泪来老K家,请求老K给张“谅解书”,说大半辈子邻居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她丈夫当年跟老K也是过命的交情,可怜走得早,留下个孩子没人管教,才有他吴国强现在这个样子。
王二妹呜呜地哭:“我就这么一个独苗,进去后出来就更讨不到老婆了,我们吴家绝后了,他死鬼老爸就是在地底也不能瞑目啊……”
“要不是你不让人家拆迁,也不会发生这种事啊……K哥,我不是怪你,你也大人不记小人过,谅解谅解孩子吧……”
2017年元旦过后,老K出示了“谅解书”,之后他就把老宅租了出去,带着张姨回到乡下生活去了。
回乡后,老K很快又聚集起一帮老友,我看他的朋友圈,时常有些喝酒打牌的照片,熟面孔中多见当年村里的老炮儿。老K不忌口,他的糖尿病愈发严重了。我劝他还是少喝点,他每次都说“知道了知道了”,说完又照喝不误,回头总跟我说:“兄弟在一起,哪能不喝酒?没事的,打两根胰岛素就OK了!”
2017年夏天,我最后一次收到关于老K的消息:老K在自家张罗的一次牌局中,因心脏病突发离世,享年六十三岁。葬礼十分隆重,小城稍微有点头脸的人全来了,花圈多得放不下。灵堂上,张姨哭得死去活来。
六安街终于在2017年底动工拆迁了。按拆迁政策,张姨分得了两套房子和一间店面。老街是真老,推土机在两天之内就把它推成了一片废墟,只留下“六安庙”孤零零地立在一堆破垣残瓦中,正在讨论是要平移还是拆到别处重建。
成堆城堆的旧木料被旧货商们一卡车一卡车地运走,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我站在六安桥西边,向曾经熟悉的六安街望去,发现已然辨不清老K家原有的方位了。
四周的铁皮栅栏迅速立起,一切都快速且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再过不久,这儿就是新楼盘了。
2018年清明的时候,我回家扫墓,顺便看望一下张姨。其时,她正在客厅的镜子前扭来扭去,见我来,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自己最近正组织村里的一帮老太参加广场舞比赛,她是领舞。说着,随即从沙发上拿起两套广场舞的衣服问我:“猴子,你说哪套好看点?老K说你一向眼光好!”
我胡乱指了其中一套,突然有点感伤起来。
三十多年前,这个客厅还是老K的后院,尘土飞扬中,他示意我从墙头上跳下来,问我要学什么功夫。我脆生生问:“猴拳,可以吗?”
老K哈哈大笑,声震屋瓦,拍了拍我的肩说:“没问题,你小子眼光真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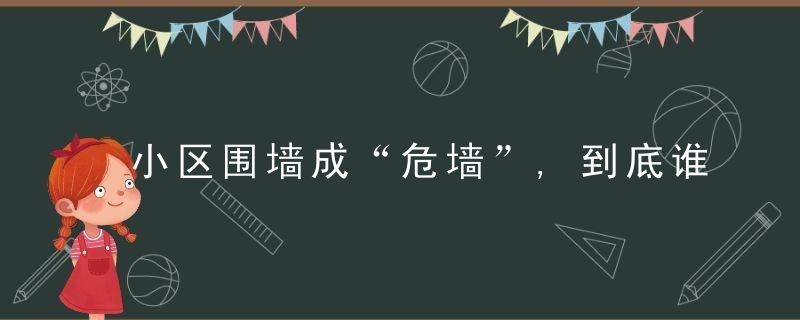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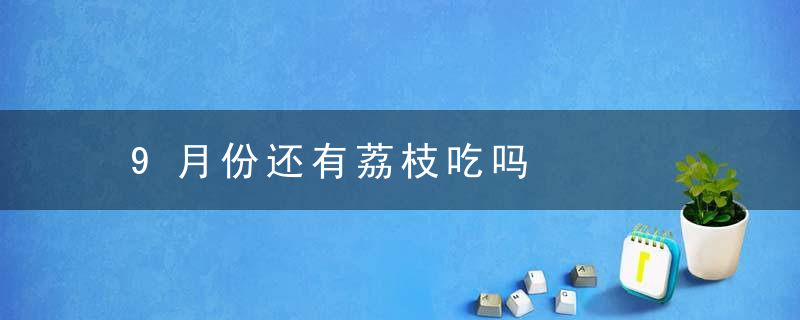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