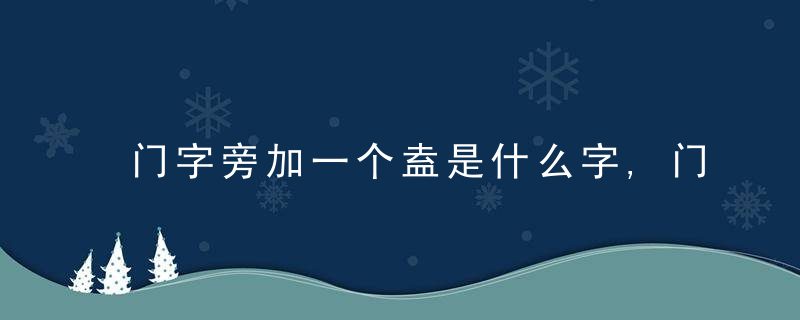把唐诗窄化成《唐诗三百首》,还有比这更大的灾难吗

你究竟是把古人供起来读,还是努力把自己当作古人的同代人来读?
”这是著名诗人西川在他的新书《唐诗的读法》中提出的一个问题。对于大多数当代读者来说,采取的读法显然更偏于“供起来读”,是“以面对永恒的态度来面对古人作品,希冀自己获得熏陶与滋养”。
但将其放入神龛,同时可能就意味着窄化。仅仅推崇唐诗伟大,很多问题都得不到解答:唐人怎样写诗?为什么好诗人集中在唐代?……对于诗歌创作者而言,还会关心:唐人怎样写诗?他们如何处理他们的时代?
所以西川换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去读唐诗,并提出了不少引人质疑的观点,比如“王维是一个二流诗人”、“唐代为其诗歌成就付出了没有思想者的代价”、“时常有人(例如季羡林、夏志清等)站在古诗的立场上批评新诗,那其实都是极片面之语”等。
近日,新京报书评周刊采访了西川,听他解读为何要以这样的方式去读唐诗,以及关于自己观点的争议。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张进
西川,诗人、散文和随笔作家、翻译家。1963年出生,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曾任教于美术学院人文学院,任副院长、图书馆馆长,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创作,出版诗集《西川的诗》《深浅》等。
西川是个争议颇多的诗人。关于他的写作、对文化的讨论,甚至性格,都引起过争论。近期,西川出了本小书,《唐诗的读法》,争议随之而来。
在诗词热的当下,《唐诗的读法》有意无意地回应了当下的文化热点。西川写作本书的原因,是有些人质疑现代诗人写不出像唐诗那样的经典诗歌,站在古诗的角度批评新诗。因此,西川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给出了“如何读唐诗”的看法。借由本书,西川回到唐代诗人写作的现场,以诗人的身份走向李白、杜甫们,并用文字让他们活转过来,再次成为有血有肉的人,进而与他们展开写作者之间的对话。
现今的读者接触的唐诗,大部分来自课本,有些读者读过《唐诗三百首》,而了解《全唐诗》的人少之又少。其次,一般读者评鉴唐诗时思维僵化,如李白是浪漫主义、杜甫是现实主义,而更深的缘由并不知悉,对这些诗人的日常也缺乏了解。
那么我们是怎样把唐诗封入神龛的呢?说来有趣,竟是通过大规模缩小对唐人的阅读!——显然太大体量的唐诗我们无力抬起。今天我们每个人(不包括大学、研究所里专门吃唐诗研究这碗饭的人)说起唐诗,差不多说的都是《唐诗三百首》(外加几个唐代诗人的个人诗集),不是《全唐诗》;而《全唐诗》,按照康熙皇帝《全唐诗》序所言,共“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
……
纵观《全唐诗》,其中百分之七十的诗都是应酬之作(中唐以后诗歌唱和成为文人中的一种风气)。读《全唐诗》可以读到整个唐代的社会状况、文化行进状况、唐人感受世界的角度和方法、唐人的人生兴趣点和他们所回避的东西。这其中有高峰有低谷,有平面有坑洼,而读《唐诗三百首》你只会领悟唐诗那没有阴影的伟大。
——引自西川《唐诗的读法》
”西川试图向读者展示,在“以诗赋取士”的唐代,诗是如何写出来的,唐人又是如何写出一首首杰作的;而且唐诗也不全好,唐人写诗时竟是有“小抄”的,如《古今诗人秀句》《泉山秀句集》等,这些在唐代被叫作“随身卷子”,诗人随身携带,以便不时查阅。这些“逸闻”和他认为唐诗是“类型写作”,把王维视为二流诗人,唐代没有思想家等争议观点一样,都是他针对当代唐诗阅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从写作者的角度给出的看法,以及提出新的批评框架。
对话西川
中国古代艺术全是类型化的
新京报:写这本书的起因,是有些人对新诗作者提出质疑,认为你们不能写出像古诗那样琅琅上口的经典诗作。接收到这种批评的诗人应该不少,但用写书方式给出回应的现今好像是只有你一个。
西川:不光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前头的人,比如艾青那一代,郭沫若、闻一多那一代,一定都受到过这种质疑。闻一多写过《唐诗杂论》,冯至写过《杜甫传》,郭沫若写过《李白与杜甫》。在我这一代诗人中,我勉强具有这个能力。
新京报:书中说,唐诗写作是“类型写作”,这个观点受到不少质疑,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西川:我也看到别人质疑这个观点。是这样:我手里有一部日本模仿中国、在明治十七年(1884)始印行的诗歌写作参考书,叫《增补诗学金粉》。如果你手边上有这种书,你就会非常吃惊,直观地了解我说的“类型写作”的意思。所以,别人不同意,说明他没碰过这类东西,也没接触过这个批评概念。
其实,中国古代不光诗歌是类型化的,咱们的艺术全是类型化的,比如佛造像、戏曲、山水画、剪纸、甚至青铜器的铸造。你看《芥子园画传》,艺术家徐冰说那就是本绘画词典。所以我这么说中国古代诗歌,好像在贬低它,实际上我说的是中国古代艺术的一个通则。但是,你知道了它的通则以后,就知道为什么中国艺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艺术。当然,我说的类型化是指基本形态,不能说由于这个门类的艺术是类型化的,就不允许天才存在了,一定是有天才的。这些天才一定对这些通则没兴趣。他们要打破这些东西,李白可能就不信这个。
新京报:唐诗的伟大毋庸置疑,在《唐诗的读法》中你也称赞了很多作家,那当代创作应该以唐诗为坐标吗?
西川:我们可以有多重坐标。唐诗是一个坐标,宋词也可以是坐标,六朝的那些作品也可以是坐标,《史记》也可以是坐标,更别说战国时代的作品,都可以成为坐标。而且不光文字可以成为坐标,绘画、雕塑、音乐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坐标。所以这是很宽阔的。另外,我们也读了那么多外国翻译过来的东西,那些东西也都是坐标。我读中国古代文学的背景是世界文学。
新京报:我们现在已不使用古汉语,如何以唐诗为坐标?
西川:以他们的高度为坐标。不光是古代诗人给出的高度,诸子文章、历史书写给出的高度、中国古人学问的高度,全在那儿。
李白像(南宋梁楷画)
关于杜甫、韩愈和“最伟大的诗人”
新京报:关于诗人排序的问题在书中也有提及。宋朝、明清和当代,对唐代诗人的排序不是特别一样,但李白、杜甫至少都在列。好诗人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呢?
西川:没有人明确地给出一个标准。这跟一个人的创造力、写作的开合度、语言能力、对文本本身的抱负、具体实践、信仰等等都有关系。我想把这话岔到另一个地方,就是关于谁是最伟大的诗人,在任何一个当代都充满了争议。比如韩愈写“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一定是当时那帮人在挤兑李白、杜甫,否则韩愈不会维护。
古人跟今人一样,也是叽叽喳喳,把杜甫都惹急了,所以才撂狠话:“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他接着又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杜甫要是活在今天,一定也被认为说大话。
新京报:你在书中写到杜甫时,说安史之乱推出了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给出了一个极高的评价。
西川:我对杜甫的伟大认可,对李白也认可。《唐诗的读法》是一本讨论问题的书,并不是要给文学立标准。为什么讨论杜甫?我实际上讨论的是杜甫之所以成为杜甫,他和他的历史逻辑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都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有“在天”的那一部分。安史之乱以后,历史就把杜甫送到这个位置上了。当然他也“谋事在人”,一直在写。
杜甫书《严公九日南山诗》拓片,据传为杜甫唯一存世墨迹。
新京报:你认为杜甫的伟大之处在哪里?
西川:让我一句话说他为什么伟大,我说不上来。稍微具体一点讲。杜甫的写作越来越自如,同时“晚节渐于诗律细”。他逮着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而且怎么写怎么是。那些差一点的诗人,他们就得合辙押韵,讲究章法,才觉得自己是个诗人。黄庭坚写字,说“老夫之书本无法”。一个道理。
在杜甫的诗里,有两首完全是象征的写法。一首叫《佳人》,是写他在山里碰到的一个女人,这女人是被抛弃的;另一首叫《瘦马行》。试着来比较一下,杜甫的《瘦马行》和俄国布罗茨基的《黑马》,都是象征写法,而杜甫的身世感特强,布罗茨基的哲学意味更浓,都很好。所以,你读杜甫的时候从来不觉得过时,你会觉得,他怎么在那个时代就抓住这种写法了?安史之乱之后,他有一行诗把我彻底惊着了,这行诗说他的女儿饿得不行,叫“痴女饥咬我”,饿得她都咬我!我们大多数人记住的是“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咬我”这种诗句让我震撼,别的人哪达到过这种力度!这行诗,你今天读今天震撼,下个月读你还震撼,他的诗句永远有效。这些在《唐诗的读法》里都没写到,因为这本书只是给出一个批评的框架。
新京报:谈到韩愈时,书中有一句话是这样的:“韩愈以文字处理当下生活的涉险勇气和杂食胃口深刻打击着我们这周作人、林语堂、张中行化了的、晚明小品化了的、徐志摩化了的、以泰戈尔为名义的冰心化了的、张爱玲化了的文学趣味。”你一句话批评了一众作家。
西川:我还漏了胡兰成!——这并不是“一众作家”,而是一个系列的作家。我多次去印度,了解一点印度的情况。泰戈尔本来是用孟加拉语写作,自己又把它翻译成英文,所以泰戈尔的英文和孟加拉语的写作又不一样。我听印度的两个作家跟我讲过,一个叫莎米斯塔.莫罕蒂,一个叫维维克.纳拉亚南,他们说孟加拉语的泰戈尔是比较硬的。但是泰戈尔通过英语进入中国,变成一个娘娘腔的人,被大大的窄化了,就跟我们今天读《唐诗三百首》,把唐诗给窄化了一样。你说还有比这更大的灾难吗?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与韩愈处理现实的勇气相对比,他们缺乏这个?
西川:处不处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想处理当下,也得有这个能力。有些人可能想处理,他处理不了,原因是语言是从别人那来的,自己对语言没有发明。比如您的语言都是从王维那里来的。有些人认为我说王维是二流诗人就疯了,其实王维也是很了不起的诗人,但是王维把一切都变成风景,用这套优美的处理风景的语言,是处理不了当代生活的。
王维像
王维经历了安史之乱,但是他已然固定下来的文学趣味和他被迫充任安禄山大燕朝廷伪职的道德麻烦,使之无能处理这一重大而突然,同时又过分真实的历史变局。这真是老天弄人。其经历、处境令人联想到才高掩古、俊雅造极,却丢了江山的宋徽宗。
王维的语言写山水、田园和边塞都可以,他可以将山水、田园和边塞统统作为风景来处理,以景寓情,借景抒情(借用中学语文老师们的话),但要处理安史之乱,他需要向他的写作引入时间维度,同时破除他的语言洁癖,朝向反趣味的书写。这对王维来说是不可能的工作。
所以安史之乱塑造的唯一一位大诗人是杜甫。杜甫在安史之乱中发展处一种王维身上没有的东西:当代性。……杜甫的当代性是与他复杂的时间观并生在一起的。他让三种时间交叠:历史时间、自然时间、个人时间。而如果说王维的风景也贯穿着时间之纬的话,那么那只是一种绝对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王维是一个二流诗人。
——引自西川《唐诗的读法》
”“诗词热”和“国学热”
新京报:近些年出现了“诗词热”的现象,你怎么看《中国诗词大会》这类节目?
西川:我家里没电视,所以也不看,不知道节目具体什么样,但我在网络上看到过一些报道。我跟背古诗词的人的不同是,我是个写作者。当我面对一首古诗的时候,它对我来说就不仅仅是一个修养的问题,而是一个创造力的问题。所以出发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别人背古诗词挺好,但问题是,那些并不真正写东西的人——偶尔照葫芦画瓢写点古体诗的不算真正的写作者——由于背了古诗词以后,便制造出一种舆论,开始对写东西的人形成压力。一个社会如果形成了对文学的某种认识,而它又妨碍到这个社会本身的文学创造,这就麻烦了。
新京报:在《唐诗的读法》中你也提到,很多人背古诗词,是让自己获得文化身份感。为什么现今社会会出现“诗词热”、“国学热”这种现象?
西川:一个是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就是老往回看。比较一下,二战以后,西方社会要重建,但没有人说咱们就回到十九世纪末。但中国有一种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心理模式,就是往回走、往回看,回到民国,回到《唐诗三百首》。第二,也许是老百姓觉得当代文化资源匮乏或者不足信。
《唐诗三百首》
新京报:即便诗词很热,但普通读者看待唐诗,还是有一些问题,比如以偏概全,比如思维僵化。如果这么认知唐代诗人和唐诗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西川:这样一来,诗人就被装在一个套子里了:李白是浪漫主义,杜甫是现实主义。但我们这么认识文学,就把文学搞得太简单了。它造成的后果就是,每个人都自以为了解唐诗,每个人都自以为了解历史,但是他了解的是诗歌最皮毛的那一点。如果他认识到自己了解的是皮毛也行,但问题是,这些认知最后变成了妨碍今天创造的一个武器了,开始对创作指手划脚,这就成问题了。
新京报:在这本书中,包括在一些采访里,你多次提到个一个词就是“智力阅读”。
西川:不光是阅读,因为智力这个东西,在阅读上有,就意味着你在别的方面也有。我觉得当代缺这个。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但好多人的智力没跟上。我觉得这是我们太需要提升的一块。在刚写的一首诗里我借忧天的杞人之口说:“与普遍的道德退化相比,我更关心普遍的智力退化”。
新京报:那如何提高智力呢?
西川:就是通过阅读。所谓的“智力生活”就是阅读讨论、思考问题。现在我们真不缺有滋有味的日子,可真正的智力生活水平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