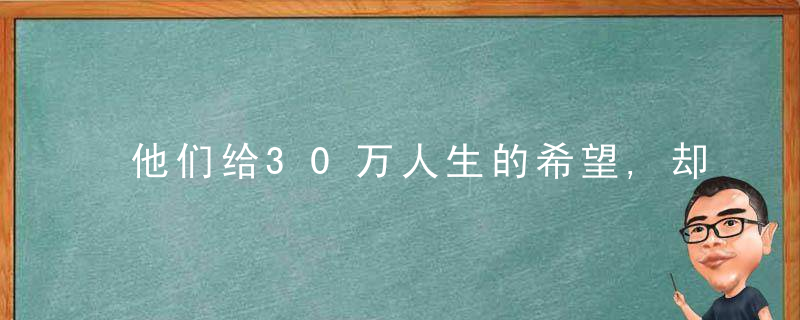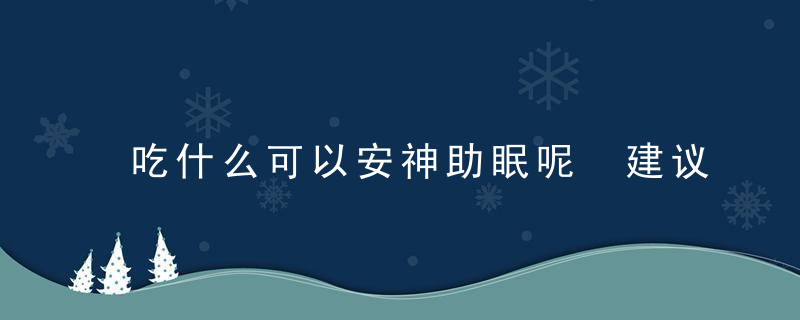器官移植简史

1906年Zirm医生实现了人类首例角膜移植手术,他把一个因眼外伤而摘除的眼球上的角膜,移植给了一个因碱性烧伤而失明的患者,病人的视力得以 恢复并终身保持,虽然角膜移植严格地说只能算组织移植,但这个成功的手术,推动了器官移植技术从实验室开始慢慢地介入到临床实践中,鼓舞了士气,因为在此 之前的人类首例肾脏移植以失败告终,让人灰心。
今天,经百年来先辈们不懈地奋斗,人类的所有主要脏器—心肝肺肾胰—都已可以进行移植,甚至包含大脑中的某些神经组织的尝试性移植也已经开始探索,以提供一种缓解如帕金森氏综合征这样的中枢性神经系统疾病的新方法。
18 世纪的欧洲,由笛卡尔所倡导的二元论哲学日益深入人心,二元论哲学虽然保留了灵魂的特殊性,但它毫无疑问地将人的身体和机器放到了等同的地位,这种新的生 命哲学观,极大的促进了对生命现象的研究,并直接催生了器官移植的惊人想法,就如同修理损坏的机器一样,也许我们也能同样修补人体,只要及时更换失效的器 官。从有文献记载的1824年赖辛格(Reisinger)首次设计出了角膜移植术,并成功地给鸡兔施行了异种角膜移植算起,从美好的理想到成为现实,人 类花费了100多年时间探索,克服了重重障碍,这其中主要的突破都发生在20世纪。
所有器官都依赖血液带来的氧气和营养才能生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身体才需要一个遍布全身的血液循环系统,要进行器官移植,首先需要完美的血管吻合术,这项技术被美籍法国外科博士阿历克西斯?卡雷尔完成,他因此常常被认为是器官移植领域的真正创始人。
卡雷尔不满于法国外科学界的保守风气,这种不满在法国总统遇刺因大失血而死时达到顶点,他出走加拿大并最后定居美国纽约,由于他无法在美国获得医师执照,被 迫告别了外科医生生涯进入新创建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中心,历史证明美国拒绝给他医师执照的决定十分英明,进入实验医学研究领域的卡雷尔对医学的发展作出了 让人无法忘记的巨大贡献。
他完善了血管吻合手术,由此开创了显微外科新领域,并且利用这项技术在1905年成功的把一只小狗的心脏移植到大 狗颈部的血管上,并首次在器官移植中缝合血管成功。小狗的心脏持续跳动了两个小时,直到血栓发生而停止。这项惊人的成就在当时无人关注,虽然他因血管吻合 技术荣获1912年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但那完全是因为他的一次非法行医。在他的助手兰伯特博士的强烈要求下,首次利用血管吻合技术通过输血拯救了兰伯 特博士的女儿,一个出生仅数天的婴儿,要知道那时候血型的秘密仅仅只有几个人知道,只能说兰伯特博士的女儿十分好运。而对器官移植必不可少的血管吻合术, 在临床上首先用于输血领域,直到更方便廉价的输血方法出现后才退出。但1912年的获奖以及在输血领域的应用,促进了血管吻合术的传播,同时正是由于输血 的大规模临床实践,促进了有关血型的研究和知识传播,让器官移植实验研究克服了外科技术上和血型的障碍。
虽然巴斯德早就开始利用免疫系统的 抗体生成能力,成功制作了狂犬病毒的疫苗,但人们长时间认为免疫系统的功能就是抵抗微生物的侵袭。直到器官移植的兴起,才促进了免疫学家认识到免疫应答是 既可防御传染和保护机体,又可造成免疫损害和引起疾病的一个生物学过程。1960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梅达沃(P.Medawar)发现了免疫防御系统在对移 植物排斥中的作用。几乎同时,多塞(J.Dausset)发现了人类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而获得1980年诺贝尔奖。免疫是生物体对一切非己分子进行识 别与排除的过程,不幸的是除了同卵双生以外,所有移植进患者体内的器官都是被排除的对象。
经过几十年在动物身上做的各种器官移植实验,许多 研究小组积累了大量器官移植手术的经验和文献,但由于难以克服免疫系统的限制,第一例人类器官移植手术似乎遥遥无期,甚至许多人怀疑器官移植在人身上根本 就行不通,即便己经有了动物实验的证据。1954年,美国波士顿的一个晚期肾炎患者,改变了历史,因为他幸运的拥有一个同卵双胞胎兄弟。
约瑟夫·默里(JosephMurry)医生牢牢的抓住了这个天赐的机会,在布里格姆医院给他移植了一个肾脏,一切都非常完美,成功完成了人类首例器官移 植,改变了患者和器官移植的命运,终结了投资者的顾虑,扫除了笼罩在这个研究领域上疑虑的乌云,开辟了器官移植的新纪元,也为其他器官的在人身上的移植性 研究铺平了道路。事实证明,器官移植技术完全可以在人身上应用,只要我们能够找到克服免疫系统对移植器官的排斥就行。按照今天的眼光看来,这次手术的象征 意义远大于其实际价值,首先拥有同卵双胞胎兄弟姊妹的人微乎其微,而且肾脏是人体唯一拥有两个,但只需一个就可以维持生命的器官。如果找不到克服免疫排斥 的方法,器官移植就只能停留在实验室中,无法真正进入临床实践。
在这种尴尬的局势下,有人想到了核辐射的巨大威力,这是因为广岛和长崎的许 多幸存者,发生了各种免疫损伤,他们据此提出一种在理论上十分具有吸引力的方案,首先利用辐射杀死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的骨髓造血细胞,同时用器官提供 者的骨髓重建受者的免疫系统。但采用这种处理的动物手术无一成功,以至于1960年的BMJ(BritishMedicalJournal,英国医学杂 志)哀叹到“由于免疫学原因,同种肾脏移植可能注定要失败。”
不过哀叹尚未结束,卡恩(Calne)就发现如果在狗的肾移植中使用抗肿瘤药 物6-硫基嘌呤,可以提高存活率,遗憾的是6-硫基嘌呤的副作用实在过于巨大,后来在临床中停止使用。不过这个发现掀起了一股采用药物抑制免疫系统的高 潮,很快在1962年,副作用更小的硫唑嘌呤代替6-硫基嘌呤在临床上开始广泛应用,同时,肝脏移植创始人Starzl发现,常用于抑制炎症的强地松如果 联合硫唑嘌呤使用,可以使肾移植的成功率大幅度提高,这项发现使得肾脏移植技术真正成熟。
但这两种药物的免疫抑制作用是非特异的,也就是说 为了抑制引起移植排斥的淋巴细胞,它们不加选择的杀死或抑制大量与移植排斥无关的淋巴细胞,而这些细胞对于防止感染、监视恶变细胞具有非常重要作用。因此 很多患者虽然得到了新器官,但最终却没能躲过由抗排斥治疗导致的感染和肿瘤。除了肾脏移植以外,其他器官移植的效果都十分糟糕,所有人都意识到,如果不能 找到一种特异性的只抑制和移植排斥相关的淋巴细胞的药物,器官移植这项美妙的技术无法普及。
生命医学领域中经常有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故事,谁 也想不到千呼万唤的特异免疫抑制药物,来自于一种抗真菌药物的副作用。1976年,瑞士山德士药厂的Broel意外发现一种用于抗真菌的治疗药物具有免疫 抑制作用,这种药物来自于霉菌酵解产物里提取的一个环状小肽(环孢素A)。这个报导吸引了英国剑桥的R.Calne的注意,他立刻意识到这种副作用,也许 有望成为一种新的专用于免疫抑制的药物,因此他将之用于他的动物器官移植实验,以检验这种药物的潜力。两年后,他将其成功的用于临床肾脏移植和骨髓移植, 所取得的效果,让器官移植学界为之疯狂。
今天伴随着环孢素A的广泛应用,除小肠移植外,其他器官的移植终于打破了肾脏移植一花独秀的局面, 将器官移植患者的一年存活率提高到70-85%,而肾移植存活率更是高达95%以上。不少女病人术后生了孩子,有的受者术后甚至能跑马拉松。为了鼓舞接受 器官移植的患者的意志,自70年代中期,每2年还有一次世界性的器官移植病人奥林匹克运动会,而1993年6月,在加拿大温哥华的第9届运动会上,男子百 米跑的成绩是11秒。同时,心、肝、肾器官移植的患者最长存活时间都已超过20年,肾脏移植患者中甚至长达36年。
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器官 移植道路上的重大的障碍逐一被人类征服,这个梦想终于成为现实,然而技术的巨大成功带来一个万分尴尬的问题,我们从哪里去得到那么多的器官。要知道除了肾 脏、骨髓和肝脏之外,其他的器官是不可能从活人身上获取的,比如说心脏。而在器官移植的狂潮中,第一个引发滔天大波的正是第一例人类心脏移植。
1967 年12月4日,南非医生巴纳德将年仅25岁死于车祸的安达维尔小姐的心脏移植给了一名55岁的患者,手术成功,但后续的免疫排斥使患者仅存活18天。围绕 人类第一例心脏移植引发的争论沸沸扬扬,相关各方心态复杂,比如面子问题。在许多西方人看来,这项荣誉本应当属于早就致力于心脏移植的西方人,巴纳德是一 个抢夺桃子的小人。时易事移,在器官移植遍地开花的今天,继续讨论荣誉问题只有老学究和道学家才有兴趣。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严峻的问题,巴纳德医生如何 判断安达维尔小姐的确已经死亡。而对于普通大众而言,这场争论的最大价值正是引发人们重新思考,在医学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下,如何界定生和死的界限。
在从前,呼吸心跳神经反射停止几乎同步,但现在可以利用技术在大脑已经死亡的情况下,维持一段时间的呼吸和心跳,这段时间对于器官移植来说却非常关键,如果 不能及时地取出器官,这些本来可以用来救活其他人的器官就可能会彻底或部分丧失生机。面对这场风暴,1968年美国医学会正式提出了大脑死亡就等于死亡的 新观念,并从医学角度确定了“脑死亡”的诊断标准。西方国家相继通过“脑死亡”,或以“脑死亡”为前提的器官移植法案,对器官移植的发展提供了保障。然而 遗憾的是,我国脑死亡立法,虽然2002年就号称进入实质阶段,并拟定了《脑死亡判断标准(成人)》和《脑死亡判定技术规范》,但一方面公众观念难以改 变,同时医生的社会形象欠佳等等因素的作用下,使得直到今天为止我国仍然没有一个相关法案,这对我国的器官移植尤其是心脏移植的发展和普及显然不利,而心 血管系统疾病排在人类疾病杀手榜第一名,何去何从,值得每个人深思。
(作者:三思逍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