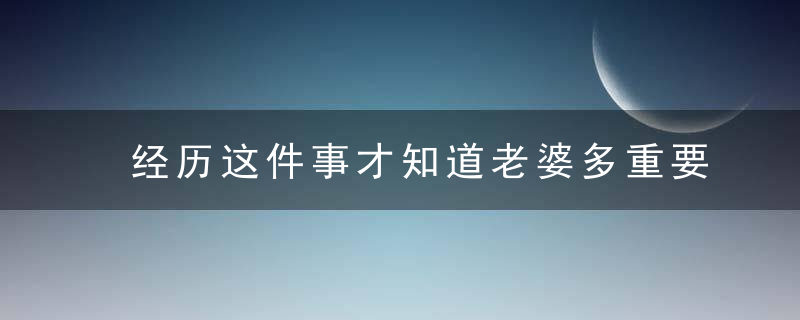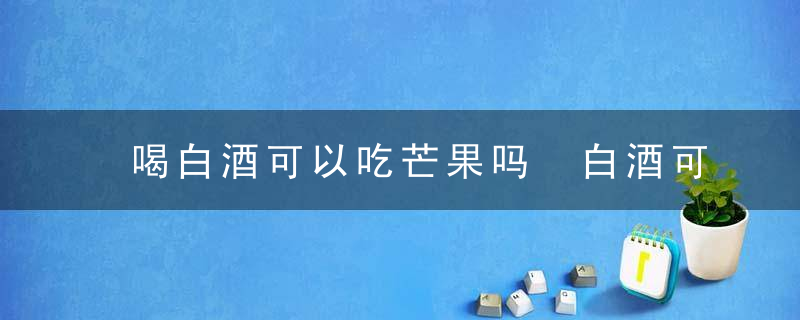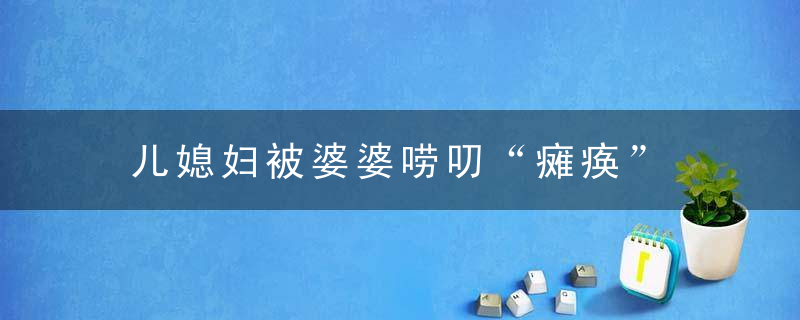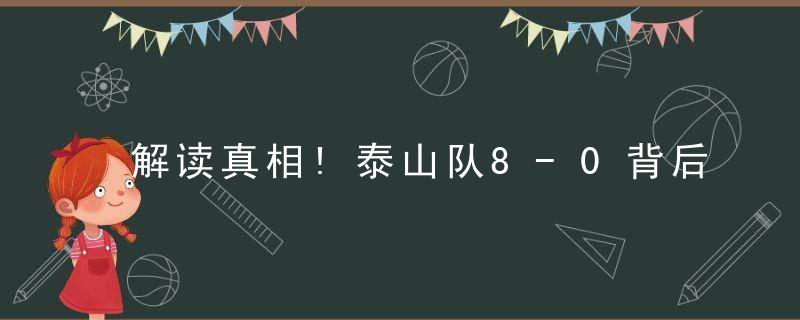快快乐乐过大年

亦农
1
吃过晚饭,我妈收拾完厨房,回到堂屋。到了收音机播放豫剧的时候,今天唱的是《柜中缘》。我妈慌忙找来笔和本儿,边听边记录唱词。
“你们跟着我唱,学会了爸爸回来唱给他听。”我妈兴致勃勃。
我和我弟举双手赞同,之所以这样充满兴趣,因为我爸这次回来与平常不同,他会和我们一起过大年。我爸依照国家休息安排,在大年二十六回来。他一定会带很多乡下买不到的年货,比如一大块肉,一堆紫色洋葱,好几张崭新的故事年画,漂亮的挂历等等。
再没有比过新年更快乐的事情了。可以穿新衣,放开肚皮吃平日很难吃到的美食,即使犯了错也不必担心挨巴掌。孩子们像快乐的音符蹦蹦跳跳,笑声在家家户户的上空飘荡,浓浓的年味在村庄檐下弥漫氤氲。
二十三烤火烧。由小年开始人们就要为过年做准备了。火烧大概是中原称谓,做法与味道异乡都极少见。我爸我妈灶房里忙一下午,一簸箕一筐热腾腾焦黄的火烧端出来。咬一口,葱油的香,面的酥香,美得人齿颊清爽。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三十捏鼻儿(集中包饺子),初一拱揖。这些日子忙碌的是大人,孩子的任务就是放肆地玩儿。
二十九或三十贴年画对联。门眉上贴一条长长的小联:“抬头见喜,大吉大利”。我在下面来回跑,伸手碰触那小联,就有甜滋滋的欣喜溢上心头。院墙或小院树身上,贴着“满院春色”、“粮谷满仓”“瑞雪兆丰年”等。看到它们仿佛春天真的来了,家里仓廪实满。我喜欢挨家挨户看对联,多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富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之类,年年如此,年年都感到新鲜、喜庆和快乐。
我爸每年都买年画,年复一年,堂屋左右侧墙上贴满旧的、新的年画。单张巨画有“九大元帅”、《刘海砍樵》、《打渔杀家》,方格故事画有《沙家浜》、《红灯记》、《梁山伯与祝英台》、《卧薪尝胆》等等。我爱站在板凳上仔细看,那些文字我还认不全,但大概意思能看懂。那些画儿,眉眼线条,神态举止,都活灵活现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仿佛古人也来和我们一起过年哩。
三十下午上坟。我爸带着我和我弟,装着一框新蒸馒头、两瓶烧酒,走出我家小院,翻过房后的土沟,往北偏东方向走约千把米,就到了我爷我奶的坟。上供、烧纸、烧香,磕头。我爸说:“过年了,给你爷奶送些吃的喝的,保佑后代儿孙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此时,平原乡下的冬日,万物萧条,田野萧瑟辽阔。近村鸡犬相闻,炊烟袅袅,远山苍茫,天空若洗。时间与空间,就在这一瞬间永恒成我脑海的一幅画,伴我成长,直到永远。
三十晚上熬夜,我妈再三叮嘱:“明早儿莫让大人唤起床啊,吃到煮烂的饺子也不许说‘破了’‘烂了’这类不吉利的话。”总之,多吃饺子少说话。尤其是嘴上没毛的小孩儿,口没遮拦。
新年鞭炮从凌晨零时乍然响起,邻居大伯家比我大五六岁的田富,每年都争抢全村第一。在他家放完鞭炮之后,村里的鞭炮声便此起彼伏,时断时续。与四周三五里外的村落遥想呼应,过年的大幕正式拉开。
在我们兄弟俩实在熬夜熬不住,钻进背窝睡觉之后,我爸我妈常常还要忙到很晚。蒸馒头,炸果子,做菜,收拾屋子等等。大人们做的还有许多事情,小孩并不全知道。他们要把未来四五天的饭食准备好,乡下有“不过破五不能摸剪刀”之说,至少从初一到初五,大人不许干任何活,每天除了吃喝,就是串门聊大天。
那年,我爸买了两个深蓝色大沿帽,我和我弟每人一顶,戴在头上像警察。那时我们的理想之一,就是将来当警察,可以带着盒子枪到处抓坏人。我和我弟在堂屋方桌旁做游戏,一不小心,我的帽沿儿被蜡烛薰出指甲盖儿大小的焦点,嗅到焦糊味儿,才突然发现。因为过年,我妈没有责怪我,我自个儿却心疼不已,好再没有烧破。如果不凑近仔细看,发现不了。
初一早上,一觉醒来,我爸我妈早已经起床。案头焚着香,屋子里弥漫着特殊的香味儿,香头星星点点,明明灭灭,桌上还摆了馒头果盘,平添几分肃穆。我妈总能在这时候变魔法似地拿出一件件新衣,让我和我弟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
有一年,我妈给我和我弟每人做一件棉半大衣。只有生产队长,或者有些资历权威的成年人,才会披着一件半大衣在村里来回走,显得很威武。我们兄弟俩竟然有了半大衣,简直太让人兴奋了。我带着我弟在村里走动,遇到多位大娘大婶夸赞,我妈也很骄傲自己的手艺。我和我弟都感到很提气儿,走路脚丫子抬得高高的,挺着胸,仿佛自己像生产队长老铁那样多出几分威严。
在这个早上,我总能够看到收拾得干净利落、焕然一新的家。因此,我一直暗暗佩服我妈做家务的能力。我能想象到,在我和我弟熬完大年夜酣睡之后,她和我爸仍在整理房间的忙碌形象。
我妈煮好了荷包蛋,每人碗里五六个,这是新年第一道早饭,之后是每人一大碗饺子。饺子里会包一枚五分硬币,谁吃到就预示着一年的好运。我和我弟因为激动兴奋,很快就感觉饱了。
接下来的程序,该出去给长辈们拜年了。
2
天蒙蒙亮,已有黑魆魆的人影在村里走动。邻居一对刚结婚的夫妻,六娃的大哥和大嫂,早早来给我爸我妈拜年。我妈嘱托我和我弟先去谁家再去谁家,依血缘关系远近亲疏而定,后来每年大约都依这样的顺序。
我和我弟拜年的第一站,当然是我伯家。穿过村中小道,绕过我伯家那没有院墙的小院,进入他家堂屋,我和我弟同声说:“伯、娘,给你们拜年了。”
“不磕了,来了啥都有了。”我伯笑眯眯地取出两张还算干净的贰角钞票。那是乡下最普遍的压岁钱标准。老实巴交的我伯,农闲时靠在家里劈芦苇编凉席到集市卖赚些钱。我娘在一边缩着手,也是一脸的笑。只有在过年时,我伯和我娘才会穿上干净整齐的衣服,屋里也才收拾得有些模样。
我堂哥勋还没有起床。我到西屋喊他。勋光着上半身,癔癔症症从地铺上坐起来。只有这一天,勋才不会穿带布丁的衣裤。平日里,每个村人都会穿戴布丁的衣服。我也穿过,衣服划破了,烂个洞,我妈用针线缝了继续穿,大家都不觉得丢人。勋穿的裤子上面,经常是补丁摞着补丁了。
我姐早就穿戴齐整。等他们吃过饭,一起返回我家,我爸或者我妈同样会取出两张贰角,给我姐和勋做压岁钱。我爸递给他们的压岁钱总是崭新的,那是他刻意去银行换的新钱。
在村里,我能挣到的压岁钱,也就这贰角了。
当然,我妈会给我和我弟压岁钱。我爸我妈比较开明,我妈偶尔会开玩笑般让我和我弟磕头,然后再给压岁钱:贰角,伍角,或者贰元。有时我弟尚没起床,我妈把装了压岁钱的红包放在他枕边。我弟睁眼看到红包,立即兴奋起来。但这些压岁钱常常还没在我们口袋捂温乎,就被我妈以“代为保管”的名义,收缴而去。
我和我弟还要去旗哥家、大奶家拜年。
当然,邻居六爷家也要去的。到他们家拜年很有意思。六爷六奶坐在堂屋方桌两边太师椅上。方桌上摆着几盘凉菜,豆腐皮拌红萝卜丝、莲菜红辣椒丝,炸丸子等,一瓶白酒,几个小酒杯。来拜年的先要磕头。然后,成年男人要喝主人端起的酒,夹一口凉菜。女人吃瓜子、果子。
人们拜年大多见面拱手、作揖、寒暄,在家里坐一坐、烤烤火、吃颗糖果。
我爸我妈一般等到我们兄弟俩拜年回来,村里晚辈该来拜年的也来得差不多了,他们才一起出门,给村里他们的长辈拜年。
在村里,我爸我妈的辈份算高的,因此,他们需要去拜年的并没有几家。他们每年都要去秀成家。会计秀成的妈年纪很大,个子不高,皮肤黝黑,长乎脸,眼珠子溜园,滴溜溜乱转,看上去很精明。后来瘫痪了,长年卧床不起。秀成的爹是一个小老头,大圆脑袋,皮肤也很黑,总是弯着腰,悄无声息地在村里走,或者坐在某个地方,长时间一动不动。后来听说,秀成他爹得了肝癌。我从他的脸上看不到痛苦,但似乎看到了许多无奈。
那时,我以为我爸我妈去给秀成爹妈拜年是因为他们辈份高。几十年后,一次和我爸聊天,才知道还有另一个原因:秀成妈是我爸我妈的红媒。当年我爸我妈能走到一起,还要感谢秀成妈从中牵线搭桥。
我爸我妈还会去村东的贤玉大爷家。那是一处老宅,正屋坐西朝东,进院有影背墙。贤玉大爷有三个儿子。小儿子很小送了人,后来长到六七岁又回来了。一年春节,我爸我妈去贤玉大爷家串门,我独自在家里,不知为何大哭。我明知道我爸我妈去了贤玉大爷家,自己也一路走到贤玉大爷家的院子外面。隔着贤墙,我甚至听到贤玉大爷两口和我爸我妈在大声聊天。我并没有进院,而是又悄然返回家,站在厨房后面的路上,面向贤玉大爷家的方向,大哭。
我明知道,大过年的掉眼泪不吉祥。但孩子的心理就这么古怪,甚至连我自己都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
3
大年初一,村里人相互拜年,初二各家各户就开始串亲戚了。
我们最先要去的是外婆家。我爸那辆永久牌自行车是我们家唯一的交通工具。开始时,我坐前面横梁,我妈抱着我弟坐后座。后来,我弟一年比一年长大,体重大幅增加。我妈个矮,车梁又高,抱了他很难再坐上去。于是,我爸改变策略,先带我和我弟走一段,回头再接我妈。
春节往往已进入数九寒天,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有一年大雪,我弟在前梁上冻得直流青鼻涕,呜呜哭。
“别哭了,瞧你哥都没哭。”我妈鼓励我弟。
我也很冷,但要证明自己是男子汉,一直咬牙坚持。
“莫哭,马上就到外婆家了。”我爸安慰。
过年走亲戚是一道景致。乡间小道上三三两两,都是你来我往走亲戚的,骑自行车算是先进交通工具。有人套着马车,一家老小坐在马车上。还有拉架子车的,也是欢欢乐乐一大家。更多则是步行,小孩在前面蹦蹦跳跳,大人提着礼物在后面走得四平八稳。
村头路口,尤其是通往侯集镇的姜营丁字路口,路旁有两间小屋商店,出售过年礼物,比如糖果、果盒等。村人一般都自带礼品,走亲戚没啥带的,自家蒸的大白馒头、红枣馒头,两包红糖,两包挂面、鸡蛋等,塞满一筐,沉甸甸的。
我们家的过年礼品,大都是我爸从工厂服务公司商店买回来的,品质很好。不像那些村口小店,虽然便宜,质量没有保证。甚至有些礼品,还是上一年春节剩下的,换了包装再卖。送礼讲究成双成对,亲戚家一般留一半,回一半。一个要全留下,一个要多回些,总要拉拉扯扯一番。
去外婆家,中途经过大王庄。姨婆家就住在村马路的南边。我爸我妈会顺道拐个弯儿,去看望姨爷和姨婆。姨婆是外婆的亲妹,我妈的亲姨,也是很近的亲戚。因路途较远,我妈图省事儿,每年都是经过这里,稍座片刻,喝杯茶,歇歇脚,把礼物留下,就动身继续赶路。
一家人这样走走停停,20多里的路要走好几个小时。一大早出门,到外婆家已是大中午。外婆知道我们要来,早早做好准备,中午肯定有一顿丰盛大餐。外婆家五六口人,我们一家四口,十几个人凑一块很热闹。若碰巧姨也回娘家,带着表妹表弟四五口,加起来十六七口,一张方桌坐不下,只好大人坐方桌,孩子坐小饭桌。没地方坐的大舅、妗子等,只好在厨房凑和着扒拉两口。
外婆家并不富裕,但在外婆的操持下,日子还算不错。满满一大桌香喷喷的饭菜,尤其是皮厚肉嫩、香而不腻的红烧肉,吃得我和我弟满嘴流油。亲戚团聚,热闹与快乐是最主要的,也是小孩最高兴的时候。
我除了到外婆家,还要去姨家和姑家。
我们家并不算亲戚多的。亲戚多的人家,七大姑八大姨,今天去这家,明天去那家,今天你来我家,明天我去你家。喜欢喝酒的人,见了面总要喝上几杯。把控不住的就喝多了。因此,总能在乡间小道上,看到某个成年人里拉歪斜、双脚打绊地走路。就有人指着他的背影,嘿嘿笑:“瞧,走亲戚的,喝多了。”
这样热热闹闹,一直要走十天半个月。人们嘴上说忙死了,心里还是快乐的。毕竟亲情总让人温暖、舒服。
过年不仅仅走亲戚,如果谁家村上唱戏,也会请亲戚朋友来看。那就更热闹了。
摘自亦农著长篇自传体小说《梦回旧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