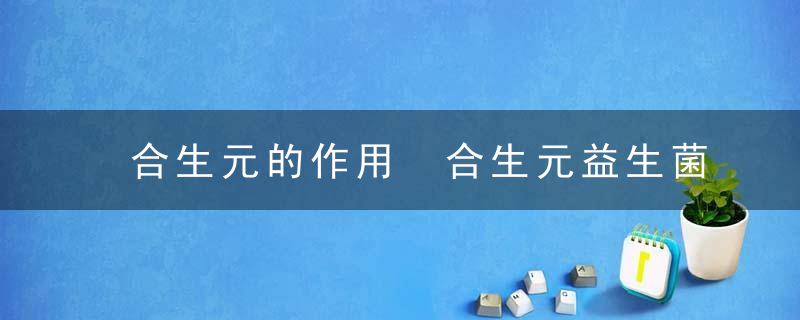非洲加速度

如果经济学家的预测准确,这可能是这块土地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了。
飞机从北京起飞,差不多11个小时后,会降落在“另一个中国”。
这个叫埃塞俄比亚的国家处在非洲大陆的高处。两个国家间的巨大差异,渗透进历史的几乎所有细节里,地表的植物也都在为此提供证据。但是,在计划前往非洲之前,不止一个人告诉我,那里就像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
他们说,那块遥远大陆上的中国影子,包括城市中随处可见的工地,也包括门外有货车排队的工厂。一个又一个工业园区成了这里的特区。有人把埃塞俄比亚的努力称为改革开放,那么这里摸着过河的石头,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中国。
闻名世界的中国制造正在影响这里。埃塞俄比亚想要成为“非洲制造”的典范,这样的目标写在了该国为2025年制定的发展规划中。
对于埃塞俄比亚来说,这是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而且这条道路还在通过这个位于“非洲之角”的国家向非洲更深远的地方延伸。
中国人开在卢旺达的服装厂里,容纳了四五百公里外偏远山村里的打工者。北京一位不久前去过乌干达的教授说,她每天早上5点被外面的喧闹吵醒,窗外是成群结队的年轻打工者。他们大多凌晨三四点就起床,骑摩托车或挤公交车去工厂上班。那总能让她想起上个世纪末北京太阳宫附近公交车开着半个门拽人上车的热闹场面。
卢旺达一家中国人开的制衣厂
在这些碎片拼起来的模糊图像前,非洲对于我来说仍然只是存在于纪录片里的神秘之地和出现在新闻里的“老朋友”。从1955年万隆会议算起,这已经是中国和非洲“相好”的第63个年头。但我还是只知道中国人在那里修了房子,建了铁路,知道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除此之外,中国在非洲还留下了什么?那里真的会出现“下一个中国”吗?
我想答案就在飞机之外。
中国的细胞融进了非洲的血管
机舱门打开,外面是一个我熟悉的陌生地方。
目力所及的远处,群山代替了高楼出现在地平线上,展示出非洲的辽阔。空旷的飞机场上,凉风裹着阵雨,冲散身上从北京带来的暑气。距离容纳了足够的自然伟力,在北半球的夏天,营造出一个和中国完全不同的季节。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年平均气温只有15摄氏度,空调都没有存在的必要。
亚的斯亚贝巴的街头,公路旁边是中国修建的轻轨。
埃塞俄比亚历的一年有13个月。在招揽旅游的宣传页上,这里被形容为“13个月阳光普照的国家”。
从天空到土地,这儿处处透着和中国的不同。但是走出机场,这些不同被各式各样的建筑和拥挤的人群压缩得越来越小。
这里的中国人太多了。在这个主要使用英语和阿姆哈拉语的国家,机场指示牌上唯一出现的另外一种文字是中文,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专门设立了一个中文的服务柜台。有人说,中国人是当地数量最多的外国人。数量庞大的中国人抬高了中餐馆的物价,中餐的价格至少是西餐的两到三倍。在当地高档的中餐厅,一盘鱼香肉丝都要几百元人民币。
春节的时候,从这里回国的机票像春运一样紧张。候机大厅的门口会贴上春联,摆上拜年娃娃的人形立牌,甚至在大厅里煮饺子,让人们上飞机前吃一盘。
埃塞俄比亚是没有唐人街的,卢旺达大使馆附近住了太多中国人,成了当地约定俗成的唐人街。当然,它的名字听起来更接地气一些,叫“卢旺达菜市场”。
街边的馆子里聚齐了从东北菜到川菜的各种口味,不过最火爆的还得是大排档。菜市场也在努力适应中国人的味蕾,“国内有的这里基本都有”。
其中一家蔬菜超市是中国人开的。店主本来在深圳开了一家发光二极管灯具工厂,后来,“国内产能过剩对工厂冲击不小”,他关了工厂,来到这里。那时,菜市场还只有白菜、萝卜和土豆,这个山东人受不了这种贫乏,开始种菜卖菜。如今,他正打算把种植面积从原来的300亩扩展到5000亩。
这些曾经带动中国经济循环的活跃细胞,正渗入非洲经济的毛细血管里。在国内开婚纱制造厂的中国人,看到埃塞俄比亚根本没有婚纱礼服厂,只有租赁礼服的商店,而租一次的价格就相当于在中国买两件新的,于是找到了发财的希望。原本在这里倒卖和维修手机的80后,看到当地医院缺乏核磁共振的仪器,很多医生只能靠经验判断病情,很快就从国内进口了仪器,开起了诊所,还把生意做到了吉布提、坦桑尼亚,下一步打算把足迹踏上津巴布韦、加纳、尼日利亚的土地。
中国商人在非洲大陆的村镇开设了上千家“中国商品杂货店”。他们教原本不种蘑菇的赞比亚人种蘑菇以出口,也教还没有熟练运用电脑的非洲人如何成为电商。“中国人就是善于在夹缝中生存。”一位常年往返于中非之间的人说。
吴文俊是1996年随父母从中国浙江省来到卢旺达的。那时这里的大屠杀刚结束不久,道路坑坑洼洼,城市里甚至都没有5层以上的楼房,“路边还有很多残疾人乞讨”。但是,看到当时的种种治理举措,这家人决定留下来。如今,他们经营的酒店就像地标一样立在首都基加利整洁的市中心,旁边还有一个由他们经营的超市,“是当地最大的”。
就在他们酒店的后面,是基加利最热闹的所在,卖Tecno手机的店铺密集地安插在临街店面中。这个来自深圳华强北的手机制造商,研发了针对非洲人的自拍美颜功能,还考虑到非洲人对音乐的热爱,让“开机的音乐铃声似乎永远不结束,来电时的铃声大得似乎全世界都能听到”。到非洲10年后,它成为非洲销量最高的手机品牌,每10个非洲人就有4个在用它。有人发现,从内罗毕的机场道路到坎帕拉的贫民窟,从肯尼亚的边境小城到卢旺达的旅游城市,只要有墙的地方,就少不了来自这个中国厂商的涂墙广告。
还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通往或准备通往非洲的路上。
11个小时内,飞机在天空上划过的弧线超过8000公里,这是从北京到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之间的距离。这个数字正在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飞机通航只是两个大洲不同肤色的人们缩短距离的诸多努力之一。
这个非洲重要的中转机场是中国人承建的,机场外扩建项目的工地上也挂着中国公司的标志。从机场出发,路边最显眼的一个广告牌上,中文的标语写着“携手埃塞人民,共建繁荣之路”。
整个非洲,有50%的国际承包项目由中国人完成
繁荣的影子,首先出现在塔吊和砖块旁。
在亚的斯亚贝巴,差不多每隔两三个楼房,就有一个正在施工的建筑,歪歪斜斜的脚手架不是用钢管搭起来的,而是桉木。当地一位中国人告诉我,因为建筑工地太多,钢管不够用了。
这些建筑里,60%由中国人完成。有人说在首都,几乎能找到所有中国搞建筑的大型公司。一位在当地做工程承包的中国人说,他曾经见过一个不算大的工程招标中,有59家中国企业竞标,“主要为了抢占市场”。
在这里,中国的企业并不是没有竞争者,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公司同样存在于这片土地上。但是中国人这些年越来越适应这种竞争。咨询公司麦肯锡曾去年发布一则报告称,在非洲的基础建设方面,50%的国际总承包项目由中国人主导。
埃塞俄比亚最高的建筑,中国人建的。第一条高速路,中国人建的。中国在亚的斯亚贝巴建的轻轨和从这里到港口国家吉布提的全电气化亚吉铁路,对于整个非洲来说都是新鲜事物。出租车司机载着我到当地被称为金融区的地方,一边指着那些即将封顶的,一个比一个高的建筑,一边用不太流利的英语说,“你们中国人太快了,太快了。”
麦肯锡在非洲调研的时候,在肯尼亚的乡村发现了一座由中国人建的瓷砖厂,从动土到竣工一共用了8个月。调研团队的人感叹“我家重铺屋顶和厕所都用了不止8个月”。
在埃塞俄比亚,这样的速度也不罕见。由中国人建设的阿瓦萨工业园,9个月内完成了23万平方米的总建筑面积,美国PVH公司迅速入驻,在这里生产的产品可能会被贴上Calvin Klein或Tommy Hilfiger的标签,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商场里。
高楼和光鲜的道路在这座城市里并不少见,同时还有许多地方是由未经硬化的坑洼道路连结的。玻璃幕墙装点的楼房旁,很有可能就是连成一排的,由几块铁皮搭成的棚屋。对这些高低不平的房子来说,唯一公平的事情恐怕就是不知道何时会突然造访的停电了——能够在两分钟之内逛完的商店门前摆着黄色的柴油发电机,以备不时之需。晚上有人在大厅演奏钢琴的高档酒店里,停电也会让正在运转的电梯突然变得一片漆黑。
这其中随便哪一项对于当地人来说都是巨大的障碍,中国人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中国电建集团水电一局承担了亚的斯亚贝巴城网改造项目。在他们2016年6月开始改造前,首都街头树的电线杆子大多还是木头的,很多都腐烂了,“街头的电线都是裸导线,刮风下雨都有可能短路。”
这个改造项目在亚的斯亚贝巴市内,总共立了一万多根水泥电线杆。就在不久前,城市不远处一个变电站里的变压器突然坏掉了,造成城市一大片地方突然停电,项目的甲方。当地电力公司的项目经理家都漆黑一片,团队紧急调度,用了5天,就换上一台全新的变压器。
辽阔的非洲从来都不缺海外的参与者,即使被认为是“非洲下一个中国”的埃塞俄比亚,第一和第二大援助国也是英国和美国。
但无论如何,中国人在当地的身影遮掩不住。
美国的一位学者在接受中国《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过,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存量占外国对非洲投资总量比重很小。但外国的投资总量是在数十上百年的基础上形成的,如果从逐年的投资流量来看,中国的投资份额正在逐年增加。美国的《外交学家》网站在不久前曾刊发一篇文章称,“中国和西方可以共同努力提供发展援助,而不是相互指责。大多数中国基金投向硬件基础设施,但传统的西方捐赠者更喜欢社会‘软’部门。”“如果没有中国在基础建设上的帮助,西方用于培训和其他‘软’行业的资金就会陷入黑洞。”
那份麦肯锡发布的报告称,中国如今在非洲的参与程度之深,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匹敌。根据这份报告估算,目前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已超过1万家,是此前预测数据的4倍,约90%是民营和私营企业。这份报告在发布时,名字定为《龙狮共舞》。
绝望的大陆和希望的大陆
参与这场“舞蹈”的中国人数量众多,但平日在首都街头,碰到他们的几率并不高。大部分时候,中国人待在工地上或者是宿舍里。工作是他们到这里最重要的事情。
老高是我在埃塞俄比亚见到的第一个中国人。他在这里已经差不多是第4个年头了。遇到他时,距离他工作的那个工地交工,只有几十天的时间了。工地上贴着加班的通告,大部分人都在工地赶工。
他向我抱怨工作紧张,也抱怨竞争激励。但他还是慢慢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来到埃塞俄比亚之前,他去过许多其他非洲国家。第一次到非洲是在上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前,国内生意不太好做,老家在山西的他寻思出来做些事情。
在非洲做得很辛苦,单是疟疾就让他受不了。到非洲的第一个月,他打了4次“摆子”,为此打了20多次针。还有一次是回国后打“摆子”,当地的医生因为没有治过这种病都不敢给他用药,只是当成普通的感冒医治。后来,是他签了字,逼着医生用药的。
他在非洲做的第一个工程是在中非共和国建一个酒店,那里的贫困至今让他印象深刻。他记得他所在的工程队一次吃饭就能吃光一个菜市场。他们把首都方圆120公里的猪吃光了,后来的18个月,他们只能吃牛肉,以至于许多年后,老高看见牛肉就反胃。
在非洲待得久了,他有些跟不上国内的节奏。他记得第一次回国的时候,站在突然变得繁华的城市街头,自己都不敢过马路。
但是他目前还没有回国的计划。在埃塞俄比亚待了4年,在非洲待了十来年,他见过越来越多的建筑公司来到这里。没办法,相比于国内趋于饱和的市场,这块土地里藏着更多的机会。
2000年,《经济学人》杂志曾在一篇封面报道中把非洲称为“绝望的大陆”,战争、饥荒和专制的让那篇文章的作者看到对非援助的黯淡未来。今年,同一本杂志上新的文章标题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大陆》。
“许多曾经稀缺的商品和服务,现在已经被广泛使用。非洲每4个人就有3部手机,与印度一样。到2017年,有近30%的家庭拥有电视机,10年间这个数字增长了近五倍。尼日利亚的电影产量比美国多。电影制作人、小说家、设计师、音乐家和艺术家在新的希望气氛中茁壮成长。民意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二的非洲人认为今年会比去年好,这个比例是欧洲的两倍。”
藏在这块土地里的希望让远隔千山万水的中国人兴奋不已。工地上的中国人只是受益者之一。不断破土的建筑为中国产能已经过剩的钢铁和水泥找到了一个可贵的出口——因为对建筑质量要求较高,老高说,当地生产的这些材料大多不合标准,他连脚手架等基本的工具都是从中国进口的。去产能压力巨大的河北,还鼓励一部分企业把钢厂搬过去。
开工两个月赚了上千万元
如果科学家的假说成立,非洲恐怕是地球上年龄最老的一块土地了。早在恐龙出现之前很多年,南半球那个叫做岗瓦纳的大陆裂开后,这里的骨架就形成了。埃塞俄比亚所在的土地上,还曾站立过我们最早的祖先,那个叫露西的女人。
而如果经济学家的预测准确,这可能是这块土地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了。
这里的许多国家,每个女人平均能生育5至6个孩子。有人预计,到205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可能翻一番,达到20亿。相比之下,欧洲和美洲已经停止增长,亚洲人口正在稳定下来。
埃塞俄比亚的街头,即使在工作日的早上,也有许多年轻人闲逛。他们几乎包揽了街头所有擦鞋的工作,有些还在胸前挂上卖电话卡的牌子。
能开出租车对于当地人来说已经是份不错的工作,到工地或者中国工厂上班也是。老高告诉我,在他工作的工地上,一个小工日工资只折合10元人民币。每次招百十名工人,都有五六百人前来报名。
同时,庞大的人口也蕴藏着巨大的市场。一家中国服装出口企业将满满一集装箱的衣服运到埃塞俄比亚,结果在两周内就销售一空。还有一家中国人开的钢铁厂,因为原料不够,一年只开工了两个月,但就是这俩月的盈利已经超过千万元。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从2000年至2016年,在全球所有人口超过千万的国家中,埃塞俄比亚是世界发展第三快的国家。它甚至在10年时间里,保持了约为10%的平均增长率 。
即使在2018年,有关经济不景气的讨论比比皆是时,世界银行还预测这个国家GDP增速达到9.6%,而世界平均增速只有3.1%。
对于经历过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来说,热闹的街头和枯燥的数字,都让他们看到了商机。他们在各个领域尝试拓展业务,有的还入股当地的家族企业。不管怎么,能够拿到某个领域的经营许可总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亲善大使海宇说,随着中国人在非洲工业化领域的投资增加,中非的合作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非关系是以援助为主的,那时中国也很穷,除了帮助修修铁路以外也做不了什么。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一些中国企业开始到非洲探索贸易和资源合作领域的机会。90年代,中非主要是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如今,我们要开始帮助非洲实现经济转型。”海宇说。
成功带来成功
除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亲善大使外,海宇还曾经担任过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的工业发展顾问。她见证了许多非洲国家的工业化过程。
这位在英国受过教育的精算师,六年前就参与了中国一家大型民营制鞋企业华坚集团在埃塞俄比亚的投资。
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让华坚的总裁张华荣从起家时的4000元钱、3台缝纫机和8名工人,到如今已经拥有40条生产线,年产女鞋超过2000万双。找他代工的国外品牌,包括GUESS、COACH,还有特朗普女儿伊凡卡·特朗普旗下女鞋。但是人工成本攀升和招工难成了挡在前方的障碍之一。
海宇说,当时,华坚一双出厂价10美元的鞋子,人工成本占比大约22%。而在埃塞俄比亚,工人的月薪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
故事的开始并不容易。时任埃塞俄比亚总理来中国招商引资,希望能够在中国援建的非盟大厦落成之时,有至少一家中国制造企业完成投资。而那时已经是11月,距离第二年1月非盟大厦完工只有3个月的时间。后来,就是用这3个月,华坚在非洲的第一家工厂落地完成。
埃塞俄比亚对华坚的许诺是,制造鞋子的设备以及原材料进口都享受免税优惠。但第一个集装箱就被扣了下来,当地的海关人员把做鞋用的刷子当成了牙刷,把给鞋子穿孔的机器当成了手枪。为了解决类似问题,海宇找到当地海关的6个副关长以及所有的主任、处长,开会讨论,还请海关的20多个工作人员到鞋厂考察,了解制鞋流程。
华坚刚到埃塞俄比亚时,招来的员工没有流水线工作的经验,很多工人领完薪水第二天就没了人影,钱花完了才回来上班。直到有人因累计迟到5次被开除,上班迟到的问题才得到解决。张华荣不得不自己上阵抓员工培训,还把当地人送到中国的工厂学习。
卢旺达一家中国人开的制衣厂里,当地工人正在做早操。
很多员工进厂时营养不良,工厂就免费为他们解决一日三餐。不少员工住在附近的山坡上,洗澡成问题,公司就挖深水井接通水管,修建多个洗澡房。
华坚在埃塞俄比亚的工厂,让当地皮革产品出口增长57%。第一年创造了2000人的就业,第二年这个数字到了4000。
“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实际是帮助了人口金字塔最底端最贫穷的人,创造了大量就业后,他们会拿收入进行消费,底端的经济转型带动整个社会转型。”海宇说,“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都是在全球工业化转移的过程中抓住了产业转型的机遇,中国改革开放也是走了工业化的路。”
如今华坚在当地已经建成9条现代化制鞋生产线和配套的鞋材厂,截至2016年年底,已累计出口超过8000万美元。而且,这个鞋厂的成功,还带来了更多的中国制造企业关注和投资非洲。
东方工业园外的农村
第一次来埃塞俄比亚的时候,华坚集团把厂址选在了东方工业园。这个由江苏一家民营企业投资的工业园筹建时,商务部正在进行境外经贸合作区招标。但没有多少中国企业愿意去非洲投资。东方工业园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焦永顺记得,“园区里草都长起一茬又一茬”。
后来华坚来租了第一栋厂房,第二年就租了第二栋厂房,第三年再想租的时候,厂房已经租满了。焦永顺说,2015年以后,来园区考察的人开始变得很多,而且有许多是带着项目来的,考察完当场就签协议。
“成功带来成功。”海宇说。
她在此后成为埃塞俄比亚的工业发展顾问,接手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帮当地另一个已经建成的工业园区招商引资。
在此之前,这个园区已经五六年没有成功招商了。但是她和埃塞俄比亚工业部的官员一起,不到3个月,把园区22栋厂房全部租了出去。“我当时做法很简单,就是把中国的、印度的还有土耳其的投资者都找来,带她去看华坚的工厂。”
从2008年到去年,东方工业园在当地租地的价格已经涨了68倍。
中国人带来的不只是就业。2015年,埃塞俄比亚颁布《工业园法》,焦永顺说,这里也有他们的功劳。“我们是当地的第一家工业园,很多经验都是从我们这儿摸索出来的”。在这个内陆国家,进出口货物的清关需要从临海港口拉到5个内陆港清关,耗时且费用高昂。东方工业园就推动当地海关现场检验,后来,还协商海关入驻工业园区,形成一站式服务。如今,海关的一站式服务被写进了法律。
在这里生活多年的“老非洲”们,现在大多有了更宏伟的目标。焦永顺所在的公司,就有两个项目。一个是要在埃塞俄比亚造一个全球的牛仔裤生产基地,“一年至少生产1亿条,全部出口”。在公司的构想里,这是一个从种棉花开始的全产业链生产基地,“棉花的种植面积就40万亩”。第二就是成立一个电力装备公司,“这边不是输变电不行吗?哪怕电线电缆电表箱都要进口,我们这个公司就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还有更大的计划,这个参照江苏工业园的模式建设运营工业园的公司,准备在埃塞俄比亚建一座工业新城,“就像北京的亦庄”。这个预计占地72.5平方公里的工业新城,至少已经在规划图纸上展露出最初的模样。除了工业区域外,还有金融、房地产和市政配套,“能够解决五六十万人的就业问题。”
当然,把这些目标从图纸上挪到土地上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大家对这点都心知肚明。在那个遥远大陆上工作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和国内不相同的制度,不相容的效率,贫乏的外汇储备,对生活在这里的中国人都是挑战。
这依然是个贫穷的国家,人均GDP至今还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但不少人对这里保持信心。经济学家林毅夫把这儿与上个世纪的中国进行了比较。他说,1978年中国开始转型的时候,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当时中国人均GDP156美元,和埃塞俄比亚人均155美元GDP相比几乎相同。但是改革开放带来的转型,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海宇就出生于1978年的中国,她了解那种贫穷。
她2011年到埃塞俄比亚的时候,住在首都的喜来登酒店。有一天,她发现酒店的后面有一个高档的酒吧,酒吧里都是欧美人在唱歌跳舞,没有一个非洲面孔出现在那里。
这让她想起7岁生日的时候,爸爸带她从老家东北到北京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爸爸那时本来想给她一个惊喜,但是知道酒店一晚的价格差不多要100美元后,只好离开了那里。她走之前看了一眼那个漂亮的大堂,也是看到了很多白人,感觉那是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美丽世界。
如今,对于这个已经成为众多非洲国家工业化顾问的人来说,高档酒店外的那个“墙”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她说,看到与喜来登酒吧一墙之隔的那些衣衫褴褛的妇女在埃塞俄比亚街头抱着孩子乞讨,她想,如果这个国家找到一条适合的发展道路,这里的人们也可以享受高档酒店这样的美好。
原文刊载于《中国青年报》2018年8月15日12版
作者 / 陈卓
编辑 / 从玉华
微信见习编辑:魏其濛
审核:郑萍
转载请扫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