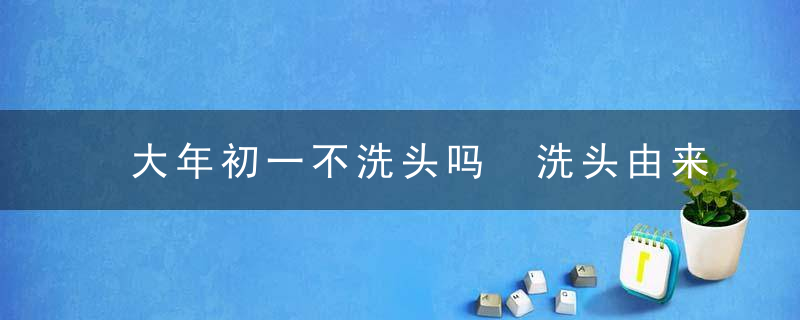那些不得不祭出“佯狂”大法的时刻

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有一个唐伯虎佯病不去给宁王当参谋,手持鸡翅引吭高歌“红烧翅膀我喜欢吃”的桥段,这并非全是影视杜撰。历史上唐寅为了躲开宁王的招揽,更加没有下限的事情也曾做过。古者,天下皆帝王所有,而帝王们都爱说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是无论他们撂下多少狠话,都无法阻止有人看不惯他们。那这些看不惯帝王们的人在一人独大的专制时代要怎么办呢?
王夫之琢磨完《资治通鉴》里头1362年的经验教训后,给出了这么几条路子:
说这个君子要是不幸陷于逆乱之廷呢,能跑路就赶紧跑路(“亟去之”);
要是一时跑不了路,就“佯狂痼疾以避之”;
装病佯狂要是还不能脱身,那就干脆豁出去,试试看能不能发动嘴炮将对方洗脑(“直词以折之”);
洗脑要还失败,就只好老老实实待家里吃鸡翅膀听天命了。
能不死当然最好,要是死,那也已经尽了本分,没什么可不安的(“身可全则可无死;如其死也,亦义命之无可避者,安之而已”)。
因为古代争取上位的人都很重视名声,喜欢招揽名士当吉祥物,所以历史上那些陷于乱世的才子能人很少会被轻易放走。比如王维在安禄山攻陷长安后就想方设法逃跑,结果都跑到洛阳了还被安禄山抓住硬塞了个给事中给他。至于“直词以折之”的成功率太低,一个不好就会激怒对方,最后像王子比干那样被刳心而死,所以这三条路子里,要数在“佯狂”这条道路上前仆后继、推陈出新、争奇斗艳的仁人志士最多,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欣欣向荣的景象。
佯狂“辞招揽”
佯狂的第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形,是“辞招揽”。
箕子应该是史上最早打开“佯狂”这扇大门的人。这位看到纣王使象牙筷子就觉得苗头不对,知“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的王叔向纣王进谏而不被听纳后,就有人劝他别干了。箕子觉得自己要是这么甩手了,虽然可以全身而退并得到大家的赞美,但到底对侄子影响不好,就没忍心直接跑路,只是披头散发假装癫狂以便“远引自外而不与闻”——也就是说,他虽然选择不走,但是留下又会有助纣为虐的嫌疑,所以佯狂以避嫌。此后他被纣王一直囚禁到武王伐纣之际才趁乱逃脱,因不愿仕周,最后带着族人东渡朝鲜建立侯国(《史记》)。相较于比干被刳视其心,箕子的结局可以说是圆满。
到了曹魏末年,佯狂史上最坚忍的人物形象诞生——太宰中郎范粲。当时的背景是司马师废曹芳。范粲身着丧服拜送废帝后,就托病拒绝朝廷的一切召见。此后他佯狂不言,连儿子们向他私下里请教事情也不曾开口,只用身体的动作回应,并终日睡在自己的车乘中,以示自己再不与司马氏共踏一片土地的决心。范老先生就这样坚持了36年之久,最后“卒于车中”。
至东汉初年,蜀地又出了一位“漆身为厉,佯狂避世”的费贻(《华阳国志》)。什么叫“漆身为厉”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豫让刺赵襄子的故事。豫让第一次行刺时被赵襄子看到了容貌,所以第二次为了防止被认出来,就“漆身为厉,灭须去眉,自刑以变其容”。(《战国策》)“厉”通“疠”,是恶疮的意思。“漆身”就是用漆树的汁液涂满全身。由于漆树汁含有强烈的漆酸,会让皮肤因过敏而形成许多恶疮,看上去丑秽不堪,令人厌恶,从而可以有效避免别人接近。漆身为厉,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需要极大的勇气与意志力。东汉初年光武帝虽已建元,但蜀地仍为公孙述所据。公孙述为壮声威,大肆招揽名士。轮到费贻的时候,前面被聘请的李业、谯玄、王皓、王嘉等人几乎都因“连聘不诣”被公孙述祸害死了——这里顺便提一句,这里面只有谯玄被机智的儿子以奉上“家钱千万”赎命才得以隐居终老。费贻既想忠于汉室,又不愿意赴死,他的家人可能也凑不齐可以赎命的“家钱千万”,于是在公孙述遣使招揽时,便漆身为厉以讨人嫌恶、假装疯癫以示无才可供驱驰,这么一直装到汉武帝平定蜀地、遣使召贤,才高高兴兴地跑去受任合浦太守。
到了明朝末年,吴中四大才子唐寅也承续先贤遗意,在宁王面前佯狂。不过相比范老先生36年佯狂不言、足不履地的高行以及费贻的漆身为厉,他的佯狂就显得要没品一些。《明史》记载,唐寅被宁王朱宸濠重金聘请入幕后不久,便察觉宁王有造反之意。自诩“不愿鞠躬车马前,但愿老死花酒间”的唐寅发现自己掉坑里了之后,赶紧“佯狂使酒”,装出一副疯癫的模样企图脱身。“佯狂”还非得加个“使酒”,是因为堂堂吴中四大才子之首,说疯就疯太假了,所以要借酒来当引子,好让宁王觉得真像那么一回事。这里需要特别注意,这位吴中才子的“佯狂使酒”和我们这些凡人撒酒疯可不是一个级别,因为《明史》在“佯狂使酒”后面还特意加了四个字:“露其丑秽”。丑秽就是丑陋肮脏的意思,怎么个“丑秽”法,史书里并没有介绍,但好在我们还可以通过观察朱宸濠的反应来体会一下——《明史》后文紧接着用五个字形容了宁王的反应:“宸濠不能堪,放还。”“不能堪”就是受不了,整段话连起来讲,就是说唐寅佯狂露丑的尺度已经远远超出宁王的忍受底线,宁王被恶心到不行,这才打发唐寅走的。故事的最后,唐寅成功跑路,筑室桃花坞,折花沽酒,与朋友过着日夜饮宴放浪形骸没羞没臊的日子,一直活到了54岁。
明清鼎革之际,有很多不愿仕清的遗老,其中也不乏佯狂的人。比如那位会画翻白眼鱼鸟的朱耷,出身宗室,是明代宁献王朱权的九世孙。他在清朝定鼎之后遁入空门,隐居深山,因身系旧朝王裔,政治敏感,连作画也无法直抒胸臆,往往只以极度隐晦的手法表达对故国的眷念。譬如由“三月十九日”京师陷落的日子变形而来的龟形画押,像“哭之”又像“笑之”的“八大山人”落款,以及为朱耷向这世道翻白眼的鱼鸟。结果他在山里安安静静地研习佛法也出了名,还和师兄弟一起被临川令胡亦堂延请到官舍,真是让他苦闷到不行(“忽忽不自得”)。他这么忽忽不自得了一年多后,终于有一天忍不下去,就跑到闹市“被葛布袍而歌”,一会儿大笑不止一会儿痛哭流涕,做足一派我已经疯了的姿态后,独自跑回南昌继续安安静静地当和尚去了。
除了上面讲的“辞招揽”,还有一拨求“辞招揽”不成,就佯狂“避世”、求在醒醉之间忘却今夕何夕的人。比如几次辞官又几次被迫卷入政治斗争的阮籍,求步兵校尉只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秩二千石却“不治官事”,整日披头散发、袒胸露乳,吊儿郎当地M字腿坐着(“云头散发,裸袒箕踞”)和刘伶他们饮酒歌呼,“佯狂以避”。
盖人逢乱世,不愿进而同流,又不要做轻生重道、赴死无悔的烈士,便唯有退而守志,披发佯狂,以求全身远害。当然,这些人的佯狂未必是真的骗过了对方,有时候更多的是一种表态。掌权者见你连这么下流龌龊痛苦的事情都做了,心领神会之下,心软一点的就都放手了。
佯狂求生存
第二种比较常见的情形是“佯狂求生”,也就是被张溥在《五人墓碑记》里痛诋为“辱人贱行”的“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那一类型。
楚汉争霸时期,范阳辩士蒯通谏韩信而不见听,便佯狂求“去”。当时的背景是韩信在楚汉相持不下之际击败了龙且并平定齐国,此时刘项两家生死都取决于韩信个人的抉择,天下大势便系于韩信一人(“天下权在信”)——连项羽都一度派武涉来说服韩信三分天下。刚以乱齐之策助韩信攻克齐都,顺便害得郦食其被田广烹杀的蒯通觉得眼下确是立不世功业的大好时机,向韩信分析时局利弊,警之以功高震主、兔死狗烹,诫之以“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希望他能背叛刘邦。结果劝谏至再,韩信始终犹豫不决。蒯通知其大势已去,自己跟着他也会遭殃,于是“佯狂为巫”,跑路给别人相面算命去了。这之后就有了长乐宫钟室中“为儿女子所诈”的淮阴侯临死前“吾悔不用蒯通之计”的叹息。
如果要评选历史上最成功的佯狂者,恐怕非唐朝末年的杨凝式莫属——这位杨同学靠佯狂安全地从唐朝末年一直活到后周,平安地度过了五个朝代,可以说是佯狂里收益率最高的一位。起初,杨凝式同学为自己当宰相的父亲接下了向篡位者朱温“送传国玺”这样遗臭万年的差事而义愤填膺,劝父亲推掉这个任务,但由于当时朱温为防止唐朝旧臣反叛自己安插了很多奸细,所以杨同学的爸爸杨涉听了这话之后被吓坏了,表示熊孩子你这是要害我死一户口本啊(“汝灭吾族”)。为了弥缝此事,杨凝式祭出了佯狂这个大招。虽然不知道他都做了些什么疯事,但从此人们都管他叫“杨疯子”。注意,这事到这儿只开了个头。因为他的疯病已经天下闻名,所以后来不管他说什么出格的话,别人都会心领神会地点点头表示理解——哦,您的疯病又发作了啊。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翻一翻《旧五代史》列传里头杨凝式的那一节,你将会看到自从他得到“杨疯子”这个头衔之后,文本里就到处都是“寻以心疾罢去”“复以心疾不朝而罢”“以旧恙免”“以心恙喧哗遣归”这种字眼。杨凝式最后的职位是后周太子太保。连续供事于梁唐晋汉周的杨凝式,就这样闲散地混过了被人们视为乱世的五代的绝大部分。
佯狂求生里头,最敬业的应该要算明初为了逃避朱元璋迫害的袁凯。他遭朱元璋迫害的原因很理不直气不壮。据《明史》记载,朱元璋为了锻炼懿文太子,“每有大狱,辄付论之”,但往往朱元璋主张酷刑,而懿文太子却要减刑,所以老朱就让监察御史袁凯来评断。这一个是皇帝一个是未来的皇帝,哪个都得罪不起,于是袁凯就说了一句讨好两边的话:“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这句话听上去没啥,却让老朱很不满意。袁凯见朱元璋已经起了恶意,就赶紧佯狂。正史虽然只使用了简单的“佯狂”两个字,但与袁凯同时的陆深却在《金台纪闻》里记录了更加丰富的细节:朱元璋听了袁凯的话之后就把他抓了起来。但老朱大概是觉得自己这样未免也显得太神经质了点,就又放了他并官复原职,只在每天临朝的时候对袁凯施加精神暴力,骂他是“持两端者”。这么骂着骂着,到有一天袁凯终于受不了了,就在过金水桥时假装中风,“仆地不起”。老朱知道了,冷笑表示中风好像应该不怕疼的,就让人用木钻钻袁凯。谁知袁凯“忍死不为动”,老朱只好将信将疑地放人回家。袁凯一回到华亭,朱元璋就后悔了,若有所思地吟了一句“东海走却大鳗鲡”后,又派人去试探监视袁凯。袁凯为了让老朱彻底断了迫害自己的念头,先下手为强开始了种种自残行为,不但拿铁索锁在自己脖子上“自毁形骸”,还苦心孤诣研制了一套炮制“猪犬下”的法子,吃“猪犬下”给监视他的人看。顺便说一句,“猪犬下”就是猪和狗的排泄物。《金台纪闻》里说:袁凯“使家人以炒面搅砂糖,从竹筒出之,状类猪犬下,潜布于篱根水涯”,然后“匍匐往取食之”。这里的炒面是指炒熟的面粉,因为颜色发黄,和红褐色的红糖搅拌在一起,颜色和动物粪便颜色十分接近,再用竹筒塑出类似于动物粪便的形状后,二者几乎别无二致。“篱根”是指篱笆脚,“水涯”则是指水边,这些都是猪狗喜欢排便的地方。由此可见袁凯为了演吃“猪犬下”也是殚精竭虑。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袁凯敬业的表演,朱元璋终于相信他是真的疯了,而他也如愿得到了“寿终”的结局。
佯狂求关注
另外,可能因为“佯狂”这个手段实在太好使了,所以除去上述这种常规的“佯狂求隐”外,古代的人们还出于各种目的展开花式佯狂。在此只举佯狂求“取关”与佯狂求关注这两种情形。
明建文帝登基后,周、代、岷、湘、齐诸王先后被削夺,燕王朱棣“硕果仅存”。朱棣为了表忠把儿子送去南京当人质,结果儿子才被放归,正喜不自胜呢,转个身家里就出了倪亮上变的事。虽然倪亮举报的主要对象是于谅、周铎,但燕王本人也被皇帝下诏责备。见形势急转直下,朱棣立刻开启影帝模式求力挽狂澜。他不但跑到闹市佯狂,大喊大叫、抢人酒食、随地睡觉,还“佯为风疾”,即使在自己的府邸中也不忘扮演中风,走哪儿都拄根手杖。精诚所至,朱棣的表演终于感动,齐泰等人派张昺、谢贵来探虚实。朱棣觉得这下可要搞个汇报演出了,于是大热天的叫人弄来一个围炉,自己缩到炉子边扮出冻得瑟瑟发抖的样子,一边哆嗦一边对张谢二人说:“这天也太冷了。”就这样,朱棣,这位堪称“佯狂”史上真正意义的影帝,终于使“朝廷稍信之”,为此后起兵创造了条件。
有这种佯狂求“取关”以便扮猪吃老虎的,也有佯狂求关注的。春秋时期,遍地都是牛人,所以大家都会做些特立独行的事情以相互区别。譬如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而逃吴后,必须要找一个大靠山来施展自己的复仇者计划。为了引起潜在“风投”的注意,伍子胥在闹市上披头散发、光脚涂面,疯疯癫癫地行乞。后来果然得到公子光(后为吴王阖闾)赏识,顺利鞭尸复仇。与伍子胥同时的范蠡也是如此。范蠡很早就因为披发佯狂出名,所以文种当宛令时才慕名去见他。后来范蠡埋伏在文种来的路上,表演蹲在狗洞学狗叫这种羞耻play,看得边上的小吏尴尬症都犯了,却因此俘获文种的心。两个人一下子就看对了眼,此后手拉手投越,成为勾践的左膀右臂。
在大多数人眼中,“狂”都是一个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字眼。但实际上,真正历史上的“狂”是十分沉重的。比如箕子佯狂之际,纣王焚炙忠良、刳剔孕妇、醢九族、脯鄂侯,比干直言谏纣却被刳视其心;阮籍刘伶的穷途而哭与“死便埋我”则出现在司马氏以顺者昌逆者亡的态度对待士人、士人鹰犬不如的背景下——要知道阮籍写完《劝进表》没两个月就死了。孔子到楚后,楚狂陆通在他面前唱了一首歌,说:圣人遇天下有道,可以成就事业;若遇天下无道,就只能求苟活而已。“佯狂”中固然不乏逃避危险以求生存的人,但它也曾是人们对抗政治黑暗的一种手段。在有些时候,佯狂未必比激昂大义的蹈死轻松,因为一个人不愿意去死,就看轻这个人为了自己的志向所做出的牺牲,未免太草率。佯狂的人里面,贞烈者如范粲的佯狂36年,卒于车中;费贻的漆身佯狂,拒不仕述,为了坚持自己的志向,坚忍地活在乱世之中,对其他人的鼓舞,并不亚于蹈死不顾的五义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