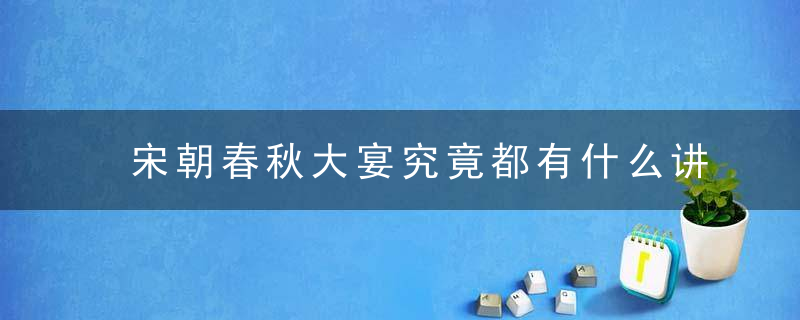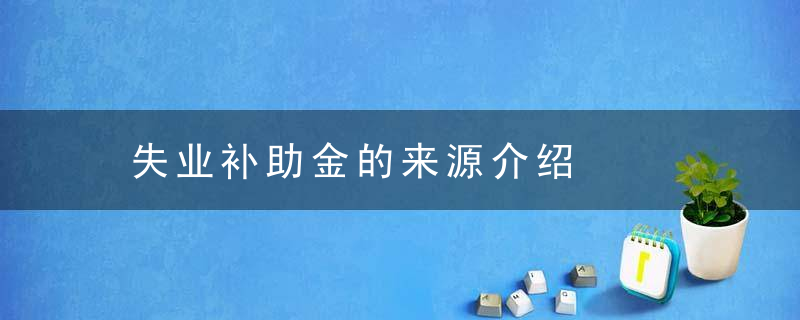那个拖累全家的杀人犯回来了

1998年夏天,我的“三爷爷”突然冒出来了。
在此之前,小时候有一年回老家过年,饭桌上的座次按孝感老家的规矩,爷爷坐在上首,四爷爷在他旁边,而爷爷另一边则是空着。我好奇地问了母亲:“这里怎么总空着?”妈妈赶紧捂住我的嘴巴,偷偷望了一眼爷爷,爷爷皱一下眉头,嘴巴一抿,将刚端起的杯子“咚”地一声按到桌上。
我吓得缩着不敢出声,四爷爷讪笑一下,打着圆场:“噶事噶事(没事),小屁伢知道么斯(什么),不讲这些。”全家这才又端起杯子,喜气洋洋地碰杯。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位置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三爷爷”的,而从爷爷脸上的怒气看,他似乎是不受欢迎的,所以家里再也没人提起过他——直到那天下午我蹦蹦跳跳回到家。
我推开门,发现堂屋里坐满了人,一些平时不多见的亲戚也来了。见我进来,他们忽然停了说话,全都看着我。
我以为是冒充父亲签字的事败露了,全家集合起来要教育我,吓得正想躲进角落里,忽然才发现角落里还坐着一个人,黑黑瘦瘦,也是怯怯的样子。那人紧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突然抬起两手紧紧搓住我的脸,笑出一口黄牙,眼睛睁得大大地说:“这是溪溪吧?”
他盯着我父亲,又伸手搓我头发,搓得我龇牙咧嘴。父亲朝那人笑了笑,看了眼爷爷,又迅速恢复一脸严肃,对那人点了点头。那人似乎想起了什么,赶紧尴尬地放下手,又恢复了怯怯的样子,讪讪地笑着说:“是赵家的种,是赵家的种!”
母亲走到我身边蹲下来,摸着我头指着那人说:“这是你三爷爷,快叫。”
我的脸早被搓得通红,只低着头怯懦地叫了一声:“三爷爷……”
“叫大点声!”母亲提高了声音。
我连忙大声叫:“三爷爷!”
“哎!”那人又笑出一口黄牙,“好了好了,莫吓到溪溪。”他不停地搓手,脸上显得很兴奋,想再摸摸我的脸,但看了看远处默不做声的爷爷,手又缩了回去。
大家又笑谈起来,聊到最后没话了,都默契地闭口不言,奶奶甚至抿住了嘴巴。爷爷这才问:“你回来住哪哈,莫样打算?”
三爷爷收起了笑容,支起身子,又稍微地躬着:“前街找好了地方,不回湾里,找个事搞到着。”
父母和姑妈们都低下了头,奶奶的嘴巴抿地更紧了,但四爷爷听到这些,突然松了口气,便立刻起身,一边说“再不回去就赶不上车了”,一边拉着几个叔叔匆忙出门,也不顾母亲的挽留,不一会儿,几个人就消失在了巷口。
三爷爷低了低头,起身说:“我回去打扫一下,屋子里太拉呱了(太脏了)。”而后也是匆匆忙忙地出了门。
堂屋顿时安静下来,屋顶的吊扇不休地旋转着,吱呀作响。
那天,三爷爷完成20年的刑期,出狱回家。对这个大家庭来说,一个“杀人犯”的回归似乎不是件欢喜的事情。
2
1998年的孝感比20年前早已大变样,再也不是人人喊着下广州、上北京的时代。人们想去中心城区、想回老家,再不用赶早搭乘班车,路边有随叫随停的“面的”、三轮车,宽裕的人家都买了摩托车。“大哥大”也不稀罕了,我父亲将BB机换成了爱立信手机,用皮套子兜着,别在腰上。
爷爷家里兄弟6人,饥荒时饿死2个,大爷爷1986年去世,排行老二的爷爷在我懂事时已成了家里的“大哥”。 三爷爷出生于1948年,十几岁时也差点饿死,后来参军,复员回到孝感种地。过了几年,镇上供销社改制,三爷爷出面牵头,拉拢4个本村叔伯,将供销社的货物供给承包下来,做起倒卖供销社物资的灰色生意。挣钱后三爷爷也成为乡里有头脸的人物,他给家里添过不少东西,资助侄儿侄女们读书,希望家里有一个“正正经经读书读出去的人”。
跟三爷爷合伙做生意的人里有当时大队村支书的儿子刘建,后来因为分利不均,三爷爷跟他闹翻结仇。刘建不断找我家的茬儿,打过那时还在读书的大伯,又把三爷爷的腿打骨折,指着四爷爷的鼻子骂:“你家老三是个什么东西,废物!迟早把你们全家害死!”四爷爷生性怯弱,也不敢顶回去,回家向三爷爷撒气,怪他拖累全家。
积怨越来越多,有天三爷爷在路上碰上刘建,他举起锄头想用锄头背面砸刘建肩膀,不想刘建一躲,锄头直接砸到脑袋。三爷爷毕竟行伍出身,锄头势大力沉,刘建竟被当场砸死了。
后来村里传言,录口供时四爷爷添油加醋地说三爷爷打死刘建后还将人推到河里。三爷爷听了信以为真,以为自己极力维护的弟弟,却对自己落井下石。
三爷爷进去后,乡邻们与我家划清界限,渐渐不来往了。后来爷爷搬到城里,四爷爷一家留守祖屋,我们每年回老家吃顿团圆饭。
出狱后的三爷爷没有坐过出租车,没有用过手机,连人民币都不再是他以前认识的模样。
他说过不回老家,但其实偷偷回去想给过世的老人烧烧香。回乡下的土路已变成二级公路,他不识字,看不懂路牌,只能边走边问。结果到村口有人认出了他,刘建的家人赶来将他堵在村口,叫他滚出去。有人知道事情原委,但没人帮他说话。
等到天黑,人都睡了,三爷爷才敢进村,硬着头皮敲四爷爷的门,想问老人们的坟埋在哪里,四爷爷将门开了条缝,露出半张脸,一边摆手一边说:“你回去吧,你回去吧,别搞得我里外不是人。”
而后三爷爷就再也没回过老家,与我家也来往不多。
1998年底临近春节,按照习俗是要在堂屋烧纸钱,插长香祭拜先祖。父亲跟爷爷提了一句:“三爷刚回来,接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个年吧,也好拜下祖宗。”爷爷不耐烦地一摆手:“叫他来干什么?祖宗还认他这个人?”说完转身进屋,边走边摆手:“你们谁都不准叫他!”
那年春节,三爷爷独自在前街的小屋子里过的。之后逢年过节,他有时会提着东西来我家,但爷爷从未主动去看过他。
3
三爷爷出狱后的第一份工作找得很不容易。因是重罪,派出所会时不时上门问话,很快街坊就知道他以前坐过牢,所以没人敢雇他,也没人敢做担保。
那时孝感城里的人家都开始使用煤气炉灶,煤气厂离我家和三爷爷蜗居的小房子都不远。
孝感不大,打车从城西到城东来回也不过30块钱。我家在国营4404厂(后更名汉光电工厂)附近,厂里划了安置区,自家出钱出力,建起一栋二层的小楼房,安置区的房子大都一样,成排地连在一起,墙挨着墙,这边争吵、揍孩子,隔壁听得一清二楚。每天早上,骑自行车去厂里的人群呼呼啦啦地穿过房子间的小巷子,人们大都熟络,见面都要问候,“走了啊!”、“上班去啰!”此起彼伏。
三爷爷的小房子隔壁就是安置区的“送气点”,人们总以为煤气罐容易爆炸,没有多少人愿意干这个,只有老板一个人做活,所以煤气经常供不应求。看老板实在找不到帮手,于是三爷爷毛遂自荐,天天去他店里帮忙,老板见他还算勤恳,最终答应让他来店里做事。
第一个月,三爷爷为了表明决心,执意不要工钱,只要吃住,不论天晴下雨,只要有人打电话,他都会马上装上煤气罐,踏上三轮车,呼哧呼哧地从“送气点”出发,帮人把煤气罐扛上楼,安装好再走。
住在安置区的几户老人知道三爷爷坐过牢,执意不要三爷爷送煤气,说是怕晦气,但有时店里人手不够,三爷爷也只好硬着头皮去送,到了家里,老人会前后脚地跟着,三爷爷走后,还要把厨房打扫一遍。
三爷爷心思活泛,那时,煤气收费是以灌入煤气罐的实际容量为准,有一回,我去“送气点”玩,见他将用过的煤气罐拖到后院,打开阀门,放掉里面残余的煤气,这样再灌煤气时,进去的就多,他也能多挣钱。
眼看着,三爷爷的煤气生意越来越好,他攒了些钱,将“送气点”盘了下来。
4
那个“送气点”在我上学的路上,每次我经过,三爷爷都会从店里出来,招呼我搭上他的三轮,送我去上学。
我在车后面看着他蹬三轮的模样:的确良制服布满黑色油污,已看不出原本的颜色,脖颈被太阳炙烤得黧黑油亮,干瘦的手臂用力撑着握把,屁股稍离车座,向前倾身,使劲踩着踏板,将要拐弯时,还会扭头呵斥在后面调皮捣蛋的我:“着伙点,莫搭下去了!”在泥灰飞扬的窄路上,三轮车跑得飞快。将我送到了学校,他再赶忙去送人家的煤气。
爷爷知道我经常搭三爷爷的三轮车上学,他冲到“送气点”,愤怒地斥责三爷爷,然后将我拽回家,扇了我一巴掌,说:“煤气车你也敢坐?不怕炸死你个哈球?”
那之后,每天我就故意从前街快快地跑过去,三爷爷招呼我几次,我都故意不理。我仍然记得,他站在那窄小的门店前,不知所措地搓着手。往后,他就再也没有“正好”在门口看见我了。
可我很喜欢三爷爷,虽然不再坐他的车上学,但经常放学后偷偷跑到他店里。三爷爷总是会给我做很多好吃的,对我几乎是有求必应。
1999年孝感开始流行四驱车,价格很贵,5块一个的山寨货还没出来,全都是25块、45块的高级版。有钱的同学天天揣着他的宝贝四驱车,课间就拿出来假模假样地擦擦,羡煞了我。放学了,他们将四驱车放在地上跑,我就跟在他们屁股后头追,还跟着他们煞有介事地喊:“冲啊!天皇巨星!”
我也很想买一个,但知道考试经常不及格,父母肯定不会同意。有天中午,我去央求三爷爷,他一口就答应下来:“行啊行啊!我下午送完就给你去买!你记得来找我啊!”他兴奋地搓搓手,仿佛生怕我反悔了,“你一定放学来找我哈,我带你去买!”
下午放学,我像猴子一样窜出教室往校门跑,三爷爷早就在校门口等着,他向我使劲地招手,拍拍坐垫,大叫着:“走走,去买那个蛐蛐车!”
“是四驱车!”我一边纠正着三爷爷的说法,一边殷勤地帮他推三轮车,急切地赶往校外的玩具店。
我兴奋地指着一个蓝色的:“那个那个,那个厉害,跑的赞跳(快)得很!”我怕三爷爷嫌贵,一把就捞过来不放手。
“啊,这个呀,不贵嘛,不贵嘛,是这个吗,你挑好喔!”他乐呵呵地掏出腰间的塑料袋,里面都是一张一张摆得整整齐齐的块票,他小心翼翼地数给老板25块,又小心翼翼地将塑料袋埋回腰间。
回去的路上,我兴奋地跟三爷爷说:“你知道不,这个叫‘原始天皇巨星’!这里是尾翼,这里是底盘。8孔底盘你知道不,最厉害的那个!”
三爷爷根本听不懂,笑得露出大黄牙,一边蹬着车,一边说:“这样啊,这样啊。”他高兴地应和着我,三轮车依然嘎吱嘎吱地响,但又分明轻快了不少。
回到了家门口,他下车将我抱下来,拿手搓我的脸,认认真真地对我说:“溪娃儿,你要好好读书,不要再考鸭蛋,不然车我就没收了。”
我哦了一声,便兴奋地往家跑,我在楼上看到,三爷爷在夕阳的余晖里乐悠悠地掉头,他蹬着车,昂着头,仿佛真的做成了一件他心里天大的事。
5
爷爷对三爷爷的成见,一直没减。有次我父亲跟爷爷说:“三爷真是啃的住(有本事),要不是那几年……”
“瞎款(乱说)!”爷爷墩了墩手里的杯子,瞪了父亲一眼,他只好悻悻地低头走开。
四爷爷的小儿子建良在家终日无所事事,打听到三爷爷在送煤气挺挣钱,也加入到这一行。本身两边可以相安无事,但建良叔住在老家,那里没有多少人使用煤气,要找到一个新的住宅区开发客户,他又没有门路。于是,他便悄悄摸摸地,跑到我家这片区域,将自己的电话张贴在安置区住户的门上,抢三爷爷的客户,挖他的墙角。
建良叔的举动被三爷爷发现了,他很愤怒,跑到我家来,质问爷爷,我听到他大声对爷爷怒吼,像一头年迈的狮子:“你管不管?你管不管?老四年轻时害我,老了他儿子也来跟我抢生意!是要逼我去死吗!”
爷爷被逼得有些局促,将身子埋在椅子里,叹气,良久不语,最后似乎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终于将手抬到半空,说到:“老三哪……”
话还没讲完,三爷爷眼睛像被浇熄了一样,身子一下子砸到身后的椅子里,手一挥:“算了算了。”
而后他低头停顿了几秒,就拖着脚步从门边走了出去。这一声“老三”,他应是等许久了。
三爷爷从前街搬走,去了离我家很远的车站那边,重新再开张。不到几年时间,三爷爷便在车站附近买下一套房子,还找了一个女人。我不太了解这个“三奶奶”,只知道是从安徽过来的,还带着一个男孩,比我小些。
他们成家后,两人一起送煤气,扛上扛下,风里来雨里去。三爷爷说了,房子可以留给那个男孩,但有一个条件:孩子必须改名姓。他给男孩取了个名字叫“孝来”。意思是,孝道虽是晚了些,但总归是来了。孝来不爱读书,也不太听话,但倒不惹大麻烦,三爷爷也由他,说不盼孝来出人头地,只盼他成人。
三爷爷一直对我有特别的期待,常说,他没读什么书,但我一定要好好读书,“你才能走出去,你才能见识这个世界”。
慢慢长大的过程里,我也能更真切地感受到来自父辈的期盼,我开始更努力地学习,尽我所能地让成绩好一些。我渐渐不再去三爷爷那里玩耍,只是放假时偶尔跑到他店铺里,笑嘻嘻地陪他吃一顿饭,听他讲些话。
后来去了南城区上学,更是一个月难去一次。每每能见到,他都会用手紧紧搓我的脸蛋,刚开始我会躲开,后来每次我都会自己将头仰起来,跟他一样笑得露出牙齿。
6
从出狱到躺在病床上用呼吸机维持生命,三爷爷只用了8年时间——风湿性心脏病,这本来是可以控制的,但在监狱里那么些年,生活条件很差,保养得就不好,出了监狱又尽做卖力气的活,他的身体很快就撑不住了。三爷爷仿佛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拼了命地做活。
我接到消息从学校赶到他家时,他已委顿在床垫上,斜躺着,艰难地呼吸,嘴巴大幅地张合,仿佛要将空气咬进去。三奶奶困倦地躺在旁边的床上,她下不来床,只是坐起来听着我们说话。
我跪在旁边,小心翼翼地喊了一声:“三爷爷……”他眼睛一轮,扫到我,突然就睁大了,张口急促地喘着粗气,随后又闭上眼睛,几滴浑浊的泪从右边眼角落下来,突然就头往左边一歪,断了气。
三爷爷走了。
“三叔!”父亲一声哭嚎,双腿跪下来,头紧紧地压在地上。
三奶奶床上大叫着爬下来:“老三!老三!”我不敢看她的神情,只听得到她的哭嚎:“孝来你快回来啊,你爸走了!”
孝来在前街的网吧上网,邻居差人将他叫回,他“嘭”地撞开大门,看到头歪在一边的继父,愣在门口,眼里满是惊惶、无措。
爷爷奶奶知道三爷爷走了,颤颤巍巍地从家里一步一步走来。爷爷慢慢掀开三爷爷头上的白布,叫我搬了把椅子,便坐在那里,抿住嘴巴,低着头。末了跟父亲说:“叫你四叔来,过来送他。”
四爷爷来得很快,爷爷说:“事都过去了,老三走了,你给他净身,送他一程。”四爷爷答应得很麻利,他很快将三爷爷的衣服脱下来,搬三爷爷的腿时,把他的腿在地上砸得“咚”的一响,奶奶在一边心疼地说:“人都走了,你就尊敬一点吧。”
我心里没来由地悲恨,紧紧地将头贴在地上,我想让三爷爷体体面面地走。
7
当时邻近春节,老家的习俗,谁家走了老人,所有亲戚初一就得去谁家。
初一早上,在三爷爷的小房子里,三奶奶站在门口,脸上的悲戚让我觉得内心翻腾。吃饭时,孝来坐在叔叔伯伯那一桌——三爷爷这一房,从此由孝来顶了。十几岁的他仿佛一夜长大,跟叔伯们推杯换盏。
我没办法跟大家一样笑,只是埋头吃着饭菜,想早点吃完出去,屋子里似乎有一种污浊让我没办法呼吸。
大伯跟我爷爷说过:“这房子就这么给了?这是三叔命换来的。”
爷爷说:“他给了就给了吧,你们不要再说这个了。”
自此以后,我们家跟孝来娘俩来往得不多,只是过年时,大伯或者我父亲,会去看望一下三奶奶。
我总是回忆起买完“天皇巨星”的那天下午,三爷爷仰头对着夕阳洒下的余晖,奋力蹬三轮的样子。我觉得,那天的他,真的是一个英雄。
(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