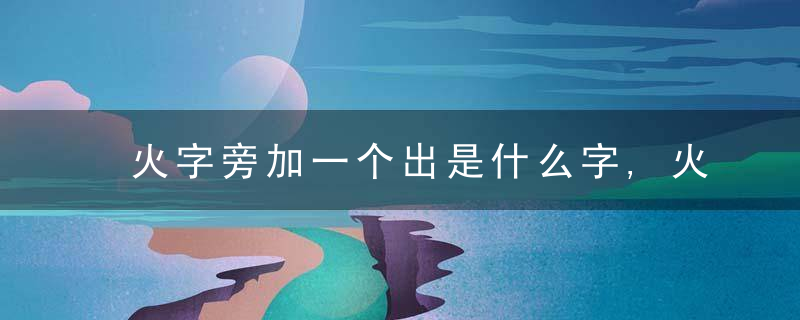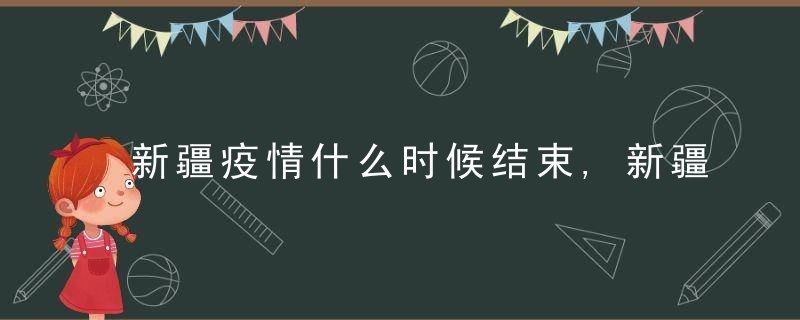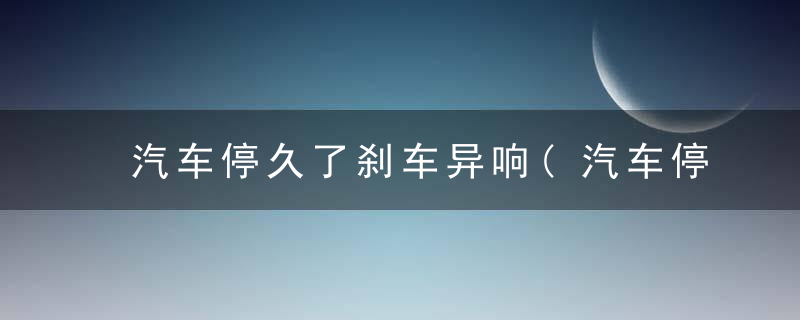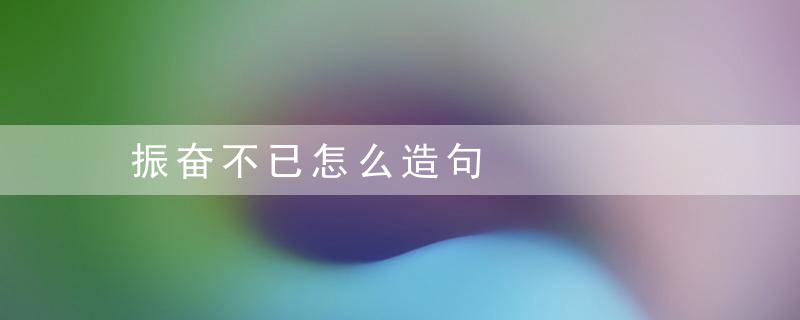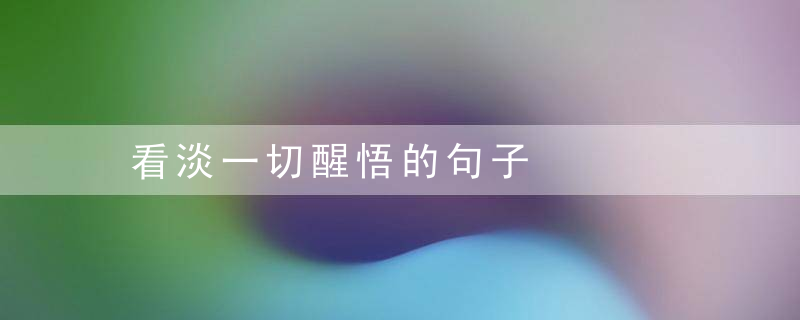揭高官腐败“路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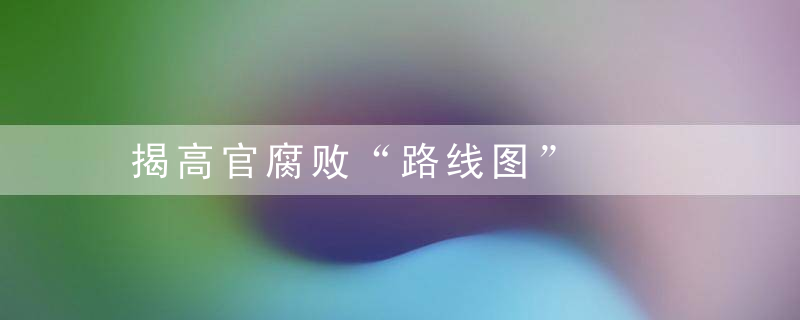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腐败与反腐败始终是一个热点问题。30年来,官员腐败的数量不断增加,层级不断提高。据不完全统计,贪腐且受到法律制裁的副省(部)级(含“享受副部级待遇”)以上官员已有百人。:(2012-02-09 法治周末)
从1921年7月1日建立,走过了91年的风雨历程。一直把保持廉洁、反对腐败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从革命战争时期被处决的谢步升、肖玉璧,到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刘青山、张子善,再到改革开放后的胡长清、成克杰……回望90多年历史,的反腐决心从来没有减弱过。党的发展实践证明,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将伴随着党的建设的整个过程。
2012年是制定的反腐败“五年规划”的收官之年。在这一年初始,回望25年来的100起省部级以上高官腐败案,厘清滋生腐败的“路线图”,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总结案件特征,剖析制度弊端,为未来的反腐败工作提供借鉴。(以下有关数据来源于出版社副社长田国良教授有关文章)
腐败的版图:滋生腐败的版图涵盖公共权力各个领域
据2012年初统计,上世纪80年代以来,被中纪委立案查处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分布于除西藏外的其他各省、市、自治区,涉及从到地方,从党政部门到司法机关,再到垄断性国有企业等各个系统,几乎涵盖所有公共权力领域。
从区域来看,经济发达地区,高官腐败案发率相对高于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但也有例外,像广西、贵州,经济相对落后,高官腐败却并不太落后);企业、银行金融系统、铁道系统、公安司法系统以及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高官腐败案例也相对较多。这表明,谁掌控的公共权力资源多,公共权力运作的空间大,腐败的几率就越大。
年龄结构分析:腐败高官开始犯罪时的平均年龄约51岁,最小的36岁,最大的65岁。其中,大多数腐败高官是在50岁到60岁这个年龄段开始犯罪的。
职务结构分析:这些高官都有显赫头衔,包括委员2人、地方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一把手7人、省政协主席5人、3人、国家机关的部长2人、副部长3人。
虽然是副省部级以上的高官犯案,但法律并没有为他们网开一面。纵观百名腐败高官,除3人自杀和外逃,7人待判决外,其余90人的量刑情况是:死刑6人,死缓26人,无期徒刑16人,这三项刑罚约占53%。另有42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腐败发展趋势分析:上世纪90年代前期,每年宣判的高官腐败案件也就是1至2起,个别年份空白,而从1997年开始,逐渐趋上升之势,2010年达到峰值(12例)。这说明,高官腐败案例的判决数量在呈逐年上升态势。
不仅如此,高官贪腐的涉案金额也在不断增加。百例案例中,除7例尚未判决、4例没有涉案金额记录或者涉案金额不在计算范围之内,其余89例共涉案金额约77699万元,平均每例约873万元。
上世纪80年代2例,1例受贿2万多元,另1例没有涉案金额纪录;上世纪90年代15例,共涉案金额约366万元,平均每例约24万元,其中最高涉案金额55万元;本世纪83例,其中3例没有涉案金额记录(或者涉案金额不在计算范围内),7例尚未宣判,其余73例,共涉案金额约77331万元,平均每例约1059万元,其中最高涉案金额达到19573万元。
腐败的线路:权力寻租的十条线路
高腐败犯罪线路大致可归纳为十个方面。
具体包括:
一,通过帮人办理各种证件、争取各种计划指标而受贿;
二,通过工程项目营私舞弊而受贿;
三,通过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问题而受贿;
四,通过土地、房产暗箱操作而受贿;
五,帮助公司违规运营而受贿;
六,组织人事腐败,如通过帮助升职、留任、调动工作、就业等而受贿;
七,庇护犯罪,如通过庇护经济犯罪,帮助走私或违规进口,干涉有关案件的办理,为律师谋利等而受贿;
八,贪污挪用公款公物;
九,滥用职权,如,支持开设“博彩”项目、支持和纵容违规经营、武断决策引进项目失败,造成国家财产严重损失等;
十,权色交易,如包养情妇、重婚等。
河南省原副省长吕德彬是因家庭变故而演变为雇凶杀人,由此成为唯一因普通刑事犯罪,不牵涉权钱交易而被处以死刑的高官。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前期,高官腐败涉案面相对单一,而且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当时,商品经济刚起步,实行价格“双轨制”,腐败高官利用计划内行政审批权,“走后门”、“批条子”,搞“权力寻租”活动。1987年宣判的两个案例,一个帮人办理香港单程通行证而受贿;一个为报答“红颜”而为公司货物走私开绿灯。上世纪90年代初宣判的两个案例,一个帮助农民联系水利工程和办理采金人员指标而受贿;一个收人钱物后,帮人办理计划外运煤手续。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高官腐败向权力集中、资金密集、利润丰厚、竞争激烈的经济领域各个层面延伸,涉及违规贷款、房地产开发、工程建设、股票上市以及产品审批等事项。
到了本世纪,高官腐败的霉菌开始触及司法、组织人事领域。如麦崇楷、丁鑫发、吴振汉、郑少东案,都和案件查处有关;韩桂芝、徐国健、侯武杰、王昭耀、荆福生、庞家钰案,就有“买官卖官”的味道。
腐败的点与面:高官腐败呈现由点到面连锁反应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腐败高官大都以“个体户”的形式单干,多以个体“点”上的腐败为多;90年代中后期以来,则开始出现“由点到面”的“集体腐败”,并且,陆续挖出了一系列所谓“窝案”,拔出萝卜带出泥的现象成为反腐常态。
如1995年王宝森的自杀,同时牵出北京的另外3名高官(陈希同、铁英、黄纪诚);海南的3名副省级干部(韦泽芳、辛业江、孟庆平)都是在1996年同时落网;广西的徐炳松、成克杰案都是在1998年和1999年前后被揭发。
本世纪初宣判的沈阳原市长慕绥新案就与马向东(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案纠缠一起,被称为“慕马案”。“慕马案”涉案人员100多人,其中,党政“一把手”就有17人。
与“慕马案”同时出现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600多人涉案,其中300多人被判刑,原副部长李纪周、福建省原石兆彬深陷其中。
2005年判刑的韩桂芝,曾多年担任省委组织部长、,后来当了省政协主席,掌控较大的人事任免权。以她为主的“黑龙江买官窝案”,牵扯大小官员百余人,其中副省级干部6人、地厅级干部30多人。
2008年宣判的陈良宇,是“上海社保基金窝案”的主角,该案也牵涉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和上海的一批官员。
2010年立案查处的铁道部腐败案,至今仍有新的线索被不断地曝光。
以上分析的案例仅是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如果按常用的“副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口径来统计,可能不是一篇博文所能叙述的了的。以上的分析已经是触目惊心,所以,也造成了社会上流传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反腐败曝光的案例多了,虽然表明党和反腐败的决心,但也折射出腐败问题的日益严重性,容易让人民群众丧失反腐的信心。
对此,中国监察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表示,要实事求是、历史、全面、发展地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战争年代、计划经济时代的腐败发生率作为参照物。在现阶段消极腐败现象处于易发、多发的情况下,不曝光腐败案件,不处理贪官,群众会更不理解。可以说,从我们党90年反腐败的历史看,反腐力度是越来越大,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现在的严峻形势也确实给我们提出更多挑战。比如大案要案的发生,且涉案金额和人数等都有所增加。如果说未来有什么能够对我们党造成致命伤的话,腐败就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坚持始终把反腐败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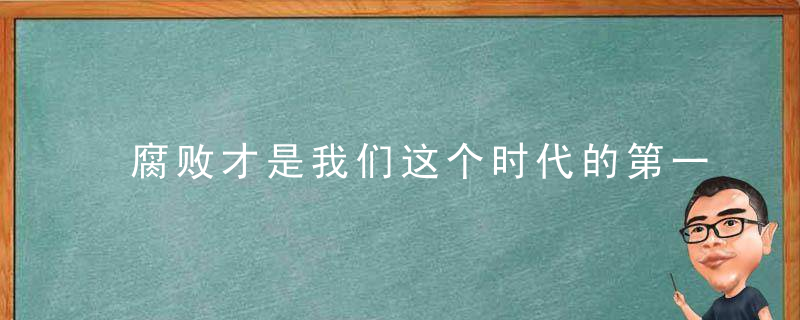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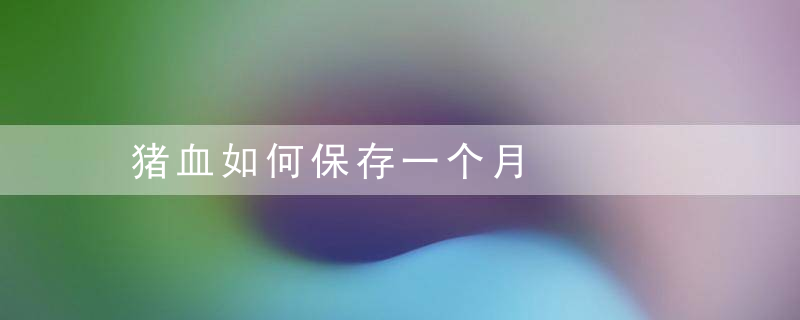

针灸为.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