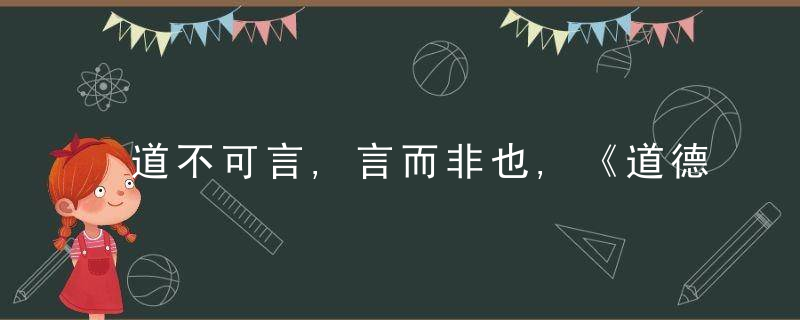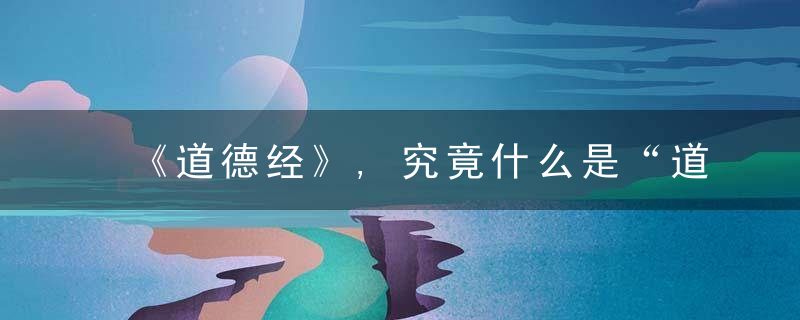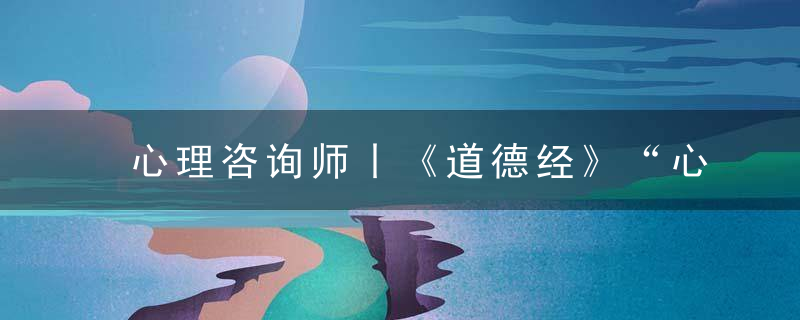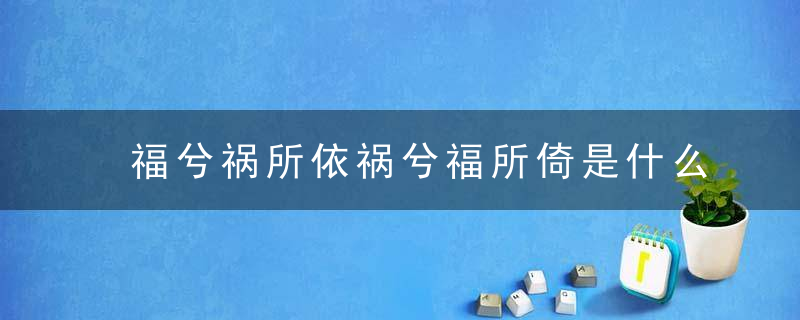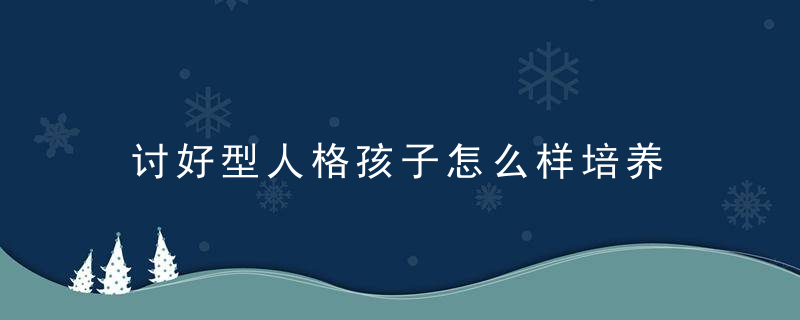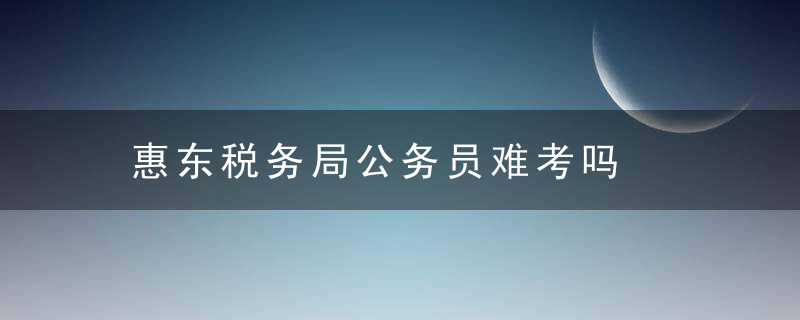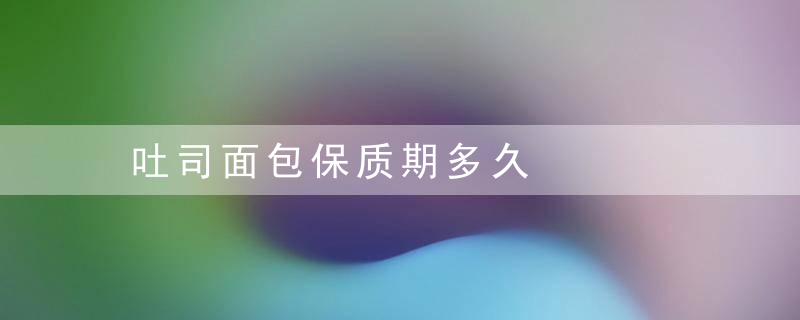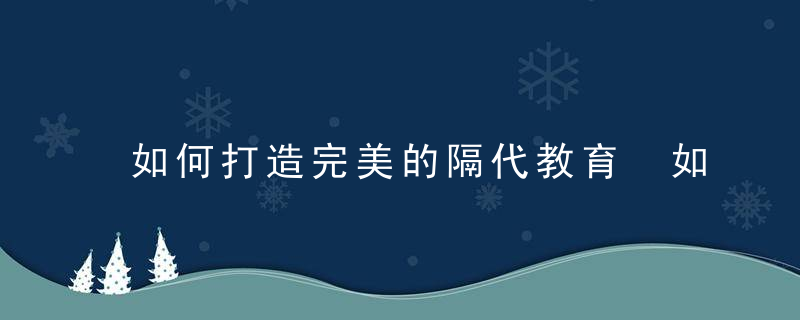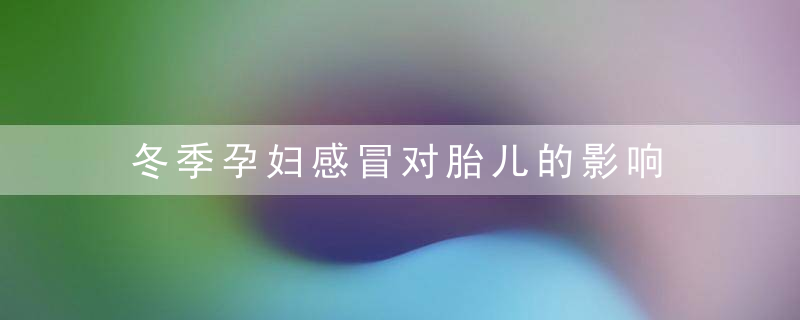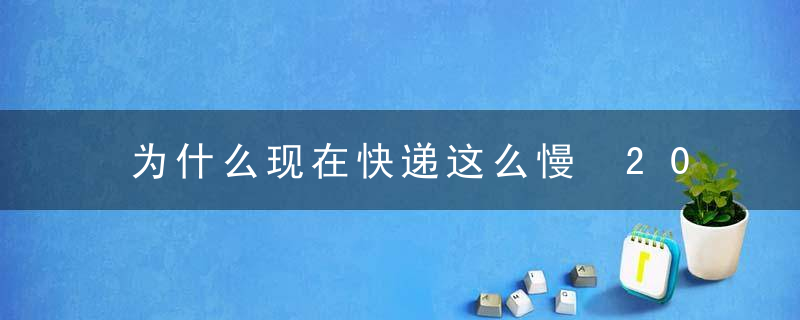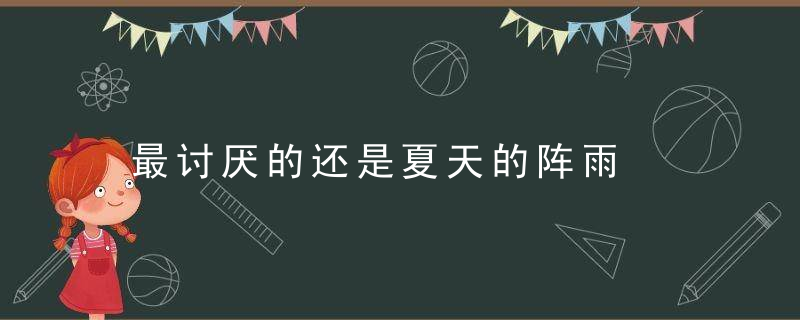《道德经》在道佛融合中的思想价值(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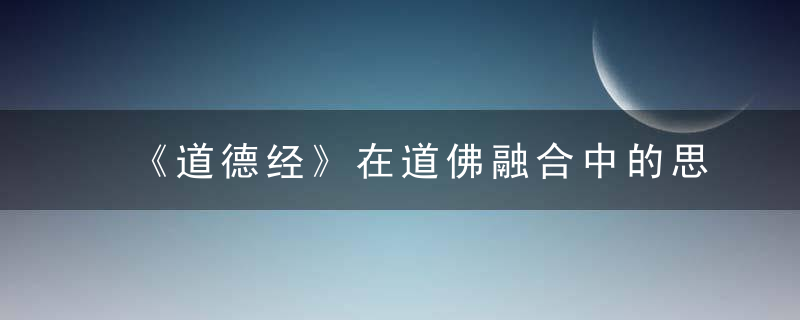
老子《道德经》的思想价值,不仅表现在自身极高的经文水准上,更体现在道佛融合关系中其引领和启示的作用上。如果中国没有佛教,《道德经》的传世一定会是另外一种情状,或许会逊色得多;而中国既已有了《道德经》,佛教的出现却又是一种必然。佛教在东汉传入促使中国知识阶层的文化觉醒,作为世俗文化的所谓“儒教”,与佛教对比相形见绌,而源自易经的道家文化虽然博大精深,却似乎够不上“教”法的严密传承,于是富有民族精神的文化人士便想建立自己的宗教。道教最初创立的动机,就是一种对佛教的对抗,这也是“夷夏之辩”的重要内容,佛教被斥为“夷”,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自始便想与之对立起来,但却没能长期做到。南朝时期,曾出现过道佛两家最尖锐的纷争,但终归是出于门户之见的“夷夏”之争,纷争现象难以掩盖两家共同的本质。由于在修炼证真的思想与方法上,二者已经开始融通互会,因而道佛的融合共存最终成为长期的主流趋势。本文拟说明,道佛能够长期融合共存主要有两个基因:一是《道德经》确立的“不可道”方法论;二是《道德经》揭示并弘扬的“人天同一”主体论。
道家是先秦延续至魏晋的学术派别,道教则是东汉后期才开始形成的本土宗教。道家哲学是道教最重要的思想渊源,道教创立之初即尊老子为教祖,奉《道德经》为祖经,魏晋以后道教经典层出不穷,但《道德经》始终被推尊为诸经之首。道教把“道”作为最根本的信仰和教义,只是它把道家思想进行宗教化的加工改制,将其视为超越形器的宇宙最高本原之“道”,赋予宗教上的意义。隋唐以后道家作为学术流派已不复存在,道教也就成为道家思想的继承者,以及道家文献典籍的保存者和弘扬者。本文中单独出现的“道”、“道家”、“道教”三个名词,是道家、道教兼指的。
(一)道可道乎——《道德经》在道佛融合中的方法论价值
(1)不重文字重修证
《道德经》开篇讲了一句传诵千古、亦是迷惑千古的话:“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潘世强教授发表在价值中国网上的《〈道德经〉新译》中,把这句话翻译为:“The Way, if expressed in words is no true or eternal Way, and if named, it is not the true name.”依据译文意思,道是不可言说、不可名状的,可以说出来的道,不是真正永恒不变的道;可以命名定义的名,也不是真正永恒不变的名。如此理解,亦是绝大多数人所赞同和认可的。这个意思正是古人所谓“得道者不言道,言道者未得道”之意,老子在《道德经》中也说:“行不言之教”(第2章),“悠兮其贵言”(第17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第56章),“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第81章)。潘世强教授译文中的“true”和“eternal”这两个词用得特别好,以前曾有经典译著把“常道”、“常名”译作“Unvarying Way”和“unvarying names”,这是按字面意思直译,相对老子原意就不太确切和到位了。
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曾写过一首七言绝句批判老子:“言者不如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老子认为夸夸其谈的人不如沉默寡言有智慧的人好,因为夸夸其谈者不可能懂道和得道;可是老子既然是这般沉默寡言的智慧高人,为什么还要写出五千多字喋喋不休的《道德经》呢?南怀瑾说:“世界上打老子耳光打得最好的,是白居易这首诗,纵然老子当时尚在,亲耳亲见,也只当充耳不闻,哈哈一笑,无所反驳了。”(《南怀瑾选集》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在佛教里边,也有类似令人迷惑的问题存在。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极致是禅宗,禅宗主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可是禅宗大师惠能却留下了两万多字的《坛经》,后续禅宗的高僧大德们都有许多文字著作留传下来,这是为什么呢?禅宗主张不立文字,在方法论上和老子的不可道、不可名是完全一致的。禅宗是中国的佛教,是中国佛教的象征,它既是佛教与道教斗争的产物,也是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将印度佛教的根本精神与老庄思想贯通而结出的成熟之果,更是在方法论上继承《道德经》传统的必然产物。事实上整个佛教都不提倡理论说教,读经万卷也只是方便法门,它强调修行实践,唯有在修行上成就功德才能成佛。而《道德经》亦是强调真修实证,唯有真修才可能得道成仙。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至少500年前,老子早已在中国开了实修不言之风,就已经有了“不立文字”法门,因此佛法初来中国,在修习道家文化的士大夫群体中很容易被接受,而且常常道佛不分,被视为一体。在中国最早崇信佛法的人并非平民百姓,而是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的宫廷贵族和大官僚,如《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楚英王传》就记载,“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楚王刘英信佛、敬佛是东汉初年的事情,到了东汉后期的桓帝时代,皇帝还在宫中为黄老和佛陀同时立祠加以祭拜,可见这时黄老、佛教已深入到最高统治阶层当中。佛教人士发现,佛教在中国立脚是得力于道家的接引,《道德经》的不可道、不可名“法门”更有利于传播佛法真谛,但囿于门户之见,不可能使道佛二者合而为一,于是禅宗便应运而生,把“不立文字”之风推向极致。
有包括《史记》在内的多种古文献记载,老子一生并无著述计划,据说老子晚年须发斑白,骑着一头青牛走过苍茫大地,过了新疆以北,往中东或是印度去了。但在离开函谷关出境的时候,遇到一个叫尹喜的关吏(也有说尹喜是老子的朋友或学生),他要老子把平生所悟得的天地自然法理写成经文留下,才肯放老子出关。老子在被逼无奈之下,便洋洋洒洒写了五千字的《道德经》,然后独自一人骑上青牛,出关扬长而去,消逝于西北大地的茫茫原野。那个守关的官吏得到老子五千字的《道德经》,肯定是如获至宝,欢喜无比。但是老子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其实是教导、教训这个关吏尹喜和世人的一句话,言下之意:你不要以为得了《道德经》文字就如同得道了,如果没有自己的亲身实践、真修实证,如何理论也是白搭啊。所以老子说这句话,他实际是指那种只说不做、只理论不修行的人,无论他们怎样地“可道”“可名”,如何地“能道”“能名”,都是没有办法知道和体会“常道”“常名”的。老子在《道德经》开篇就点明的这个道理或“教法”,被传入中国的佛家尤其在中土出生的禅宗继承了,因此佛家主张“依教奉行”,必须有修行实践才会有修行成就,只是空谈佛理恐怕一万年也入不了佛门。
可以说,不重文字重修证,甚至于不要文字只要修证,是近两千年来道佛能够融合共存的第一个基因,而且这个基因是由老子《道德经》植入其融合体系的。
(2)阴阳、万物可道,太极、无极不可道
老子说的可道、不可道,可名、不可名,在宇宙事物生成环节和地球人类修道层次上是有具体针对性的。《道德经》第42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生一”之“道”是最重要的宇宙力量,是狭义的道,老子称作“无极”。无极之道跨越时空,创生万物,包罗万象,人类生存的一切物质和机会,无一不是道所赐予的。宇宙由一、二、三等有极物构成,但有极物诞生自无极。“无极”一词是老子最早提出的,《道德经》第28章就说“复归于无极”。宋代理学家周敦颐说“无极生太极”,后来朱熹改为“无极而太极”,但意思没变。无极是无限虚无,是宇宙原始的浑沌状态,可表达为数学上的“0”。《庄子·天地》篇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泰初之时有什么呢?只有一个“无”,没有真实的有,也没有真实的名,因此是“0”。《道德经》第40章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有”就是太极,是从无极“0”(即道)生出来的。太极也是道,是绝对无偶的混沌之气,可表达为数学上的“1”,孔子在《周易·系辞》中说的“易有太极”,就是指的这个“1”。无中生有,即“0”生“1”,然后“1”生“2”,“2”是两仪即阴阳,就是《周易·系辞》说的“是生两仪”。老子说“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周易·系辞》说的“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个衍生过程蕴含的逻辑关系是:“无”是“有”的根源,第一个“有”是太极“1”,太极之前是无极“0”;第一个“有”(太极“1”)已经包含了阴阳,故能生出万物。“有”统统可道可名,“有”中的万事万物甚至还言说不尽,而“无”则不可道、不可名;但第一个“有”还不是万物,只能寡言,提一下就行了,因为无话可说。
犹如八卦有三爻,宇宙万物的发生演进总是不离三个层次。如《周易》是一部以言明象、以象尽意的书,卦辞爻辞是可名可道的文字,用来解释卦象爻象,属于“2”和“3”的层次;当通过卦辞爻辞理解了卦象,就应“得象忘言”,把“2”和“3”即卦辞爻辞忘掉。卦象爻象则是用来刻画事物意义的,属于太极“1”,当通过卦象理解了各类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无极之道“0”),就应“得意忘象”,不必再顾忌这些卦象,即把太极“1”忘掉,这就最后得道了。
宇宙万物发生演进终归是三个层次,与《周易》的辞、象、意三个层次一样,例如世俗社会的金融危机也有三个层次,处在最低层次的是研究,即研究金融危机是如何发生的;第二个信息层次是知道,例如在华尔街打工,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处在最高层次的人,他说你知道算什么,危机是由我决定和发起的。最高层次极为简单,是无极之道、大道无形,不可道不可名;知道的层次是太极,能够看清真相,但无决定权;研究的层次是两仪四象,把问题复杂化,可道可名,可是等道清名定、研究清楚,几百上千亿美元就打水漂了。所以看清这个真相,虽然我在北大给赵靖、厉以宁等中国最顶级的经济学者当过学生,我都不再研究经济学了,因为你怎么折腾都是“两仪四象”,进不到那个太极、无极的境界去。
从人们对宇宙万物发生的态度上,也可看出这三个层次的亲疏关系。《道德经》第17章说:“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太上”就是根本性的无极之道“0”,因为不可道、不可名,所以人们“不知有之”;如决定和发起金融危机的人,他大道无形藏在背后,如神仙一般无人知晓。第一个“其次”是太极“1”,是有名的万物之始,人们都知道它的伟大,因此“亲而誉之”;如知道危机的人,他总是寡言,欲言又止,神神秘秘,人们都想亲近他。第二个“其次”是对立统一的阴阳“2”,由于事物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具有截然不同和令人惊异的两面,这让人们感到惊奇可怕,故而“畏之”;如研究危机的人,制造一大套谈虎色变的理论,让大众敬畏恐惧。最后一个“其次”是“2”生“3”的“3”,阴阳生出能够为人类可感可用的万物来,人们便习以为常,不把万物当回事,可以随意“侮之”了;如社会底层众生,只管一日三餐、油盐柴米,他不懂你研究的理论,视之如草芥。“2”和“3”所代表的万物都是阴阳结合体,因此从阴阳角度讲它们共处一个层次,即包含有“畏之”、“侮之”的物质层次。
老子《道德经》所说的“道”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无极“0”和太极“1”,所谓修道,至少要修到太极“1”,最高层次修到无极“0”;二是指无极生太极,然后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自然逻辑关系(规律)。所以老子所讲的道,既是确立不可道、不可名的宇宙本源道体的本体论,也是揭示可道、可名的宇宙生成关系的方法论。
《道德经》开篇,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后,紧接着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我们阅读《道德经》,一定要明白和理解它所承接《易经》的阴阳法则,书中没有任何一个绝对概念。道这个东西,到底是可道还是不可道?我们通观全书可以发现——道可道,亦不可道;名可名,亦不可名。道不可以说,那是天地之始的无极道体“0”,本无一物,无知无欲,你说什么呢,那是真实永恒的道啊!道亦可以说,因为道并不是一个死的东西,道能产生万物,太极已经分阴分阳,阴阳怎么不可以说呢,阴阳是万物的特性,当然可以言说了,而且还言说不尽呢,但这已经不是真实永恒的道了。名不可以名,因为那是天地之始的名,天地之始的名是真实的名,真实的名就是无名(无极“0”),既然无名,那还名什么呢?同时名亦可以名,因为那个被名的东西是万物之母,具有创生的性质,万物都产生了,怎么不可名呢,但这个名已经不是真实的名(无极“0”)了。从不可道、不可名的“无”的角度,我们可以揣摩天地万物的本源(道,本体);但必须从可道、可名的“有”的角度,才能看清天地万物产生和运行的规则(徼,方法,规律)。如就社会生活来讲,从“无”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各种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这就是“道”;但必须从“有”的角度出发,方能看到和遵循社会运行的踪迹、程序、边界、法则,社会生活的实际开展才有可能,这就是“徼”。可见“无”和“有”都是同出一源,阴阳的玄秘就在这里,它是宇宙的万般奥妙之门!
老子认为大道无形,“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道德经》第14章),语言文字无法将道定义清楚,所以无名。产生于秦汉之际的道家著作《尹文子》,其中的《大道》篇就说:“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名和形是统一共通的,名用来命名有形态的事物,而有形态的事物也对应着有名的事物。大道无形,名空无着,自然就不可道、不可名了。“‘道’不是某物,它无形无象,不可感知,以潜藏的方式存在,玄妙无比,不可言说,只能意领,一旦道出,便落筌蹄,失却本真,只可寄言出意,勉强加以形容,也还须随说随扫,不留痕迹。”(尹继佐、周山主编,徐洪兴著《中国学术思潮史》(卷五),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
关于道的不可言、不可名,道家隐修诗人陶渊明有一首修道诗作了极好的描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陶渊明是道家的修道和得道高人,他忘我修行,人天合一,此中有真义,但是欲辨忘言,无法表达。冯友兰说,陶渊明“这首诗并未提到老聃,也未提到《老子》,可是讲的完全是老意。懂得‘欲辨已忘言’,对于《老子》的批判或赞赏都成为多余的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页)为什么批判或赞赏都会成为多余呢?因为在“0”无极状态下,人天合一之道不可道、不可名,只能付诸无言的观、赏、行,如要辨说,那个真义便会忘得一干二净,它本身是个“0”,那你所说的不是废话是什么呢!
这里举两个例子说明。如一少女,她属于“天地之始”,是无极道体“0”,如何能够用诸如“生子失子”、“生男生女”以及那个“子的模样”等概念去言说她呢?当她开始与异性交合,于是阴阳便出现,女孩产子后,她就从无极变太极,变成万物之母“1”,她的子孙便是阴阳“2”和“3”。女人与男人阴阳交合、生儿育女,一生二、二生三之后,可道可名的话题便是千言万语述说不尽了。在此我们会有一个惊人发现,造物主把人生最快乐、最美好的状态安排在青春年少阶段,原来它是与无极道体“0”天然吻合啊!道家、佛家修行,就是要归根复原,修回到青春年少以至婴儿状态,这即是《庄子》所说“齐生死,同人我”的境界。所以我们看到有些成年女子甚至老太婆,她在慢悠悠地打“太极”拳,显示出不同一般人的幸福与快乐情态,无一不是因为有修行素养或天赐福分,青春气息还洋溢脸上,无论历经多少坎坷,这种青春气息依然像排毒一样排除其生活的沧桑。
再如一个公司组织的诞生,这个组织根本不存在,那是无极道体“0”;有人产生开办公司的念头,他就是太极“1”;然后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他人,邀约他们一起创业,这时阴阳就产生了,发起人自己为阳,他人为阴,这是“2”;阴阳一产生,整个公司数不清的事业事务,即子子孙孙的阴阴阳阳便会缤纷出现,这就是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公司发起人在“0”无极状态时,没有什么可道可名之事;在“1”太极时,可道可名之事极少,因此道或不道、名或不名都无所谓。而当他处在“1”生“2”之后的状态,各种问题、矛盾、纠纷便会层出不穷,于是就言说不尽了。那么不管这个公司所有的工作如何地阴阴阳阳、千头万绪、生生不息、问题百出,假如这个公司老板有最大的修行成就和天赐福分,那么他就会如老子所说的“复归于无极”,生活在“0”的境界中——办公司跟没办一样,他成了神仙,整天优哉游哉过日子,创业成了一种快乐生活。
老子是世界思想史上第一个阐述天地万物起源即无极“0”和太极“1”的人,道家修道就是要修到无极去,至少要修到太极去,无论执政或修生,必须超越万物和阴阳,达到无极、太极,才能成为圣人,从而“抱一为天下式”(《道德经》第22章)。无极、太极都是道,只有在道的状态才能人天合一,永生不灭,衍生万物。这和佛家修行是完全一致的,空观是佛教修行成就的标志,没有修到“空”,就不能算是修行有大成。道、佛两家的修行法门,内中精要有其高度的一致性,这是道佛融合共存最重要的基因。
(3)不可说的“禅宗第一义”
最能说明佛家在修行法门上吸取《道德经》精髓的,是所谓“禅宗第一义”。佛家重要的修行法门是“观”和“止”。所谓“观”,就是观察《道德经》揭示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过程。佛家和道家一样都是反观,首先观察万物,然后回溯到万物所由来的三、二、一以至“道”那里去。通过反观,佛家发现一切事物时时刻刻都处在生生灭灭之中,一切事物没有自性,都是众缘和合,缘聚则生,缘离则灭,如《金刚经》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反观到宇宙万事万物的虚幻不实,获得见性正见,就要停止对那些造成烦恼的虚幻不实事物的留念贪爱,这就是止。止在哪里呢?儒家《大学》说“止于至善”,道家、佛家要止在人天合一的“空”那里,即道家的无极之道“0”或太极“1”那里,在“止”的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禅宗第一义。
现代藏传佛教上师、大圆满著名成就者纽舒堪布,他的《人生五章》一诗(转自索甲仁波切著、郑振煌译《西藏生死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38-39页),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一个人观止的过程:
1.我走上街,人行道上有一个深洞,我掉了进去。我迷失了……我绝望了。这不是我的错,费了好大的劲才爬出来。2.我走上同一条街,人行道上有一个深洞。我假装没看到,还是掉了进去。我不能相信我居然会掉在同样的地方。但这不是我的错,还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爬出来。3.我走上同一条街,人行道上有一个深洞。我看到它在那儿,但还是掉了进去……这是一种习气。我的眼睛张开着,我知道我在哪儿。这是我的错,我立刻爬了出来。4.我走上同一条街,人行道上有一个深洞,我绕道而过。5.我走上另一条街。
观的过程也是反省的过程,它会慢慢带给我们与自然合一,寻到规律、规则的智慧。由于人的疏忽和习性,免不了一再掉入不断重复的陷阱里,这时人会观,就会不断纠错,跳出错误模式,然后“绕道而走”、“走上另一条街”——这就是“止”,止在了与自然过程及其规律、规则合一的境界。
佛家“观”这个词最早就出自《道德经》,《道德经》说:“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道德经》第1章),“万物并作,吾以观复”(《道德经》第16章)。“观复”就是反观,与佛家的反观过程完全一致,先观“并作”的“万物”,然后至无极之“道”而止。反观至“道”而止这个地方,即是禅宗的第一义或第一句。《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说:“若第一句中得,与佛祖为师。若第二句中得,与人天为师。若第三句中得,自救不了。”(《古尊宿语录》卷四)“第三句”就是老子讲的阴阳万物“2”和“3”,人沉浸在纷纭万物中,不会具有光明慧眼,因此“自救不了”;“第二句”是太极“1”,修行进了一大步,开始认识宇宙本源,已经知道人天合一;“第一句”就是无极之道“0”,实现了人天合一,成佛成仙了,故而“与佛祖为师”。在禅宗的第一句、第一义,亦即老子说的无极之道“0”这个地方,是不可言说谈论的。《文益禅师语录》记载,有人问文益禅师“如何是第一义?”禅师回答说:“我向尔道,是第二义。”(《古尊宿语录》卷一)第一义是不可说的,我一说,不管说什么,就是第二义了。可见这个“不道之道”是禅宗继承了道家尤其老子的道法,禅宗由此在方法论上还走得更远,发展出以不修行为修行的“无修之修”,这其实也是对老子“无为之为”的继承和发展。
反观回去,最低的第一层次是阴阳万物即“3”和“2”,第二层次是太极“1”,最高的第三层是无极之道“0”。“0”是不可说的,冯友兰说:“无”根本不能成为知的对象,要知“无”,只有与“无”同一即人天合一,这种与“无”同一的状态,就是佛家的涅盘,“所以在第三层次上,什么也不能说,只有保持静默。”(《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7-288页)道家的无极之道“0”,就是佛家空宗所谓的第三层真谛,禅宗谓之“第一义”。在空宗第三层次,即禅宗第一义上面,任何话也不能说,这就是源自老子人天合一道体的不可道、不可名。
为什么禅宗第一义不可说?冯友兰分析认为,第一义所拟说者不能说是心,亦不能说是物,称谓什么或称谓非什么都不是。如拟说第一义所拟说者,其说必与其所拟说者不合,即禅宗讲的“有拟议既乖”;如拟说第一义所拟说者,其说必不是第一义,至多也不过是第二义,也许不知是第几义了。“凡对于第一义所拟说者作肯定,以为其一定是如此如此者,都是所谓死语。说死语的人,用禅宗的话说,都是该打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5页)无论关于宇宙或人事,只要一说,就不是无极、太极之道的第一义,而必然是阴阳第二义以至第N义了,因为一说,就是明暗、黑白、大小、方圆、软硬、刚柔、厚薄、轻重、长短、多少、上下、前后、左右、高低、远近、内外、真假、好坏、是非、善恶、彼此、有无、生克、吉凶、难易、生死、正反、对错、成败、利害、善恶……等等“死语”。所谓“是非从口出”、“人言是非多”,就是因为说了“死语”。不能用死语来定义的禅宗第一义,就是《华严经》上佛陀要求佛子应劝学修为的十种广大法:“何者为十?所谓:说一即多、说多即一、文随于义、义随于文、非有即有、有即非有、无相即相、相即无相、无性即性、性即无性。”(《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十六·十住品第十五》)全是“一”和“无”,还能说什么呢。可见这个广大法,就是老子的太极和无极之道“1”和“0”。《华严经》进一步说:“一世界即是不可说世界,不可说世界即是一世界;不可说世界入一世界,一世界入不可说世界。”(《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十七·初发心功德品第十七》)如此,便真是无话可说了。
事实上不止禅宗,世界上所有顶级的思想文化,都遵循了老子“道”的法则。例如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都是不可道、不可名、不可象的,可是它又无为而无不为(犹如制造金融危机的人),这就是老子的无极之道“0”,就是禅宗第一义。上帝、真主不可说,它一说,必然通过“道成肉身”的“上帝之子”、“真主之子”落实到人能够感知的经验界,成为第二义、第N义了。“上帝自己没有手,没有足,他必须藉着人作器皿继续他的作工。”(罗伦培登著,陆中石、古乐人译《这是我的立场——马丁·路德传记》,译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页)伟大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有一条重要经验:“除了借着上帝自己在耶稣基督里的自我显现去经验上帝以外,任何其他的途径全都是死路。”(同上,第197页)在这里上帝就是第一义,是不可道、不可名的无极之道“0”,耶稣基督是太极之道“1”,基督训导、万事万物和修行者是可道可名的“2”和“3”,修行者唯有经验感悟上帝落实在基督身上的旨意、法则,才能认识上帝,与上帝同在。“2”和“3”是可道可名、可用几何概念量度的事物,但是路德认为“几何学的观念不能用来描写上帝的临在”(同上,第296页),所以上帝作为第一义,它看不见摸不着、不可道不可名。“上帝的道是在基督里的救赎工作”,“上帝在基督里变成在肉身中的化身”(同上,第307-308页),因此认识上帝要通过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犹如认识佛菩萨要通过其化身在人间的诸法形体。我们可以任意推测,世界上所有探寻宇宙万有之源的思想文化,无一不遵循老子道的法则,只不过这些探寻者没有像老子那样自觉和透彻到极点。由此可以说,《道德经》是人类思想史上经典中的经典,而老子则是人类思想史中高人之上的高人。
第一义不可说,但是总要有方法来表现它啊,否则不是就没有第一义了吗?冯友兰认为,其实说第一义不可说,这就是用“遮诠”说第一义,因为人们若了解为什么不可说、不可谈,他也就了解了第一义,这就叫不道之道。冯友兰举例说:“中国画画月亮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在白纸上画一个圆圈,一种办法是在白纸上涂些颜色作为云彩,在云彩中露出一个白圆块,这就是月亮。这种办法叫烘云托月。它不直接画月亮,只画云彩,用云彩把月亮托出来,这可以说是不画之画,用佛学的话说,前者是用‘表诠’,后者是用‘遮诠’。”(《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第266页)
《道德经》通篇论道,可是却没有一句话从正面肯定“道”是什么(表诠),可是从它通篇论说道不是什么的文字中,我们已经懂得道是什么了,这就是“遮诠”。禅宗传教的方法,其实就是袭用了老子的“遮诠”法。冯友兰说:“形上学的任务不在于,对于不可知者说些什么;而仅仅在于,对于不可知是不可知这个事实,说些什么。谁若知道了不可知是不可知,谁也就总算对于它有所知。”(《中国哲学简史》,第393页)“遮诠”的方法其实就是“减”的方法,从纷纭复杂的万物减下去,从“3”、“2”、“1”减至“0”,用冯友兰的话来讲,“这样一层一层地剥下去,到了最后也是要归于无言。郭象所说的‘以言遣言,遣之又遣,以至于无遣’,也就是这个意思。”(《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第242页)《道德经》第48章说:“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是得道、体道、为道者之所为,这就是老子的“遮诠”法。用禅宗的形容语来形容这个“遮诠”减法,即是“如桶底子脱”,桶底子一脱,桶中之物统统脱出,这就悟道了。悟道之后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以前所有问题、所有烦恼全部解决。如何解决的呢?没有解决啊,因为原来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是个“0”而已,只是自己先前受骗罢了!所以解决问题是通过悟道、得道,使自己走出受蒙蔽状态而解决的,这样还有什么可说呢,真是无话可说了。
写作《美国理想》、自称“最后的American”的美国学者尼德曼(Jacob Needleman),他在给华裔学者冯家福的《道德经》译本所作导言中说:“道”这个词难以用非中文准确翻译,“我更想指出的是,非但是关于‘道’这个词,实际上整部《道德经》都不能被译成任何文字……其中也包括了汉字!”看来尼德曼是能够体道和用道了,因为道不可言,道不能被译成包括汉字在内的任何文字,译出来就是第二义以至第N义了,所以他用“遮诠”法说了这段话,如此一说,道就不言自明了。
佛家《古尊宿语录》卷三一记载舒州佛眼禅师说,人“只有二种病,一是骑驴觅驴,二是骑却驴了不肯下”。因此人最可怕的,就是在万事万物当中喋喋不休、废话连篇地折腾,而不能超越其间;其实“3”、“2”、“1”地从事物当中超越出去,从驴背上掉下来,或如桶底子脱,最后是个“0”。“0”的状态如惠能在《坛经》中所说的“本自无生,今亦无灭”,冯友兰认为,无生无灭,“不是时间中的生灭相续,而是永恒;永恒不是长时间,而是无时间。”(《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第277页)
由于人的认识和悟道过程(规律)是一种“减法”,即从“3”、“2”、“1”减到“0”,因此从修道角度讲,对于道的体悟,没有彻悟之前总离不开道理说明,说明本身也是入道的重要法门。但悟彻以后看待一切说教,自然就有缺陷的一面了。道理说教也像佛家讲的乘筏子过河,过河上岸到了目的地,就要抛弃筏子。若一味地乘着筏子而不超登彼岸(犹如“骑却驴了不肯下”),终究会被风浪埋没。北宋道教南宗紫阳派鼻祖张伯端有一首《西江月》词说:“未悟须凭言说,悟来言说皆非。”冯友兰也说:“在使用负的方法之前,哲学家或学哲学的学生必须通过正的方法;在达到哲学的单纯性之前,他必须通过哲学的复杂性。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中国哲学简史》,第395页)这段话是冯友兰著作《中国哲学简史》的结语,他正是说了很多话,然后才静默。道佛一脉相承的教法,精要正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