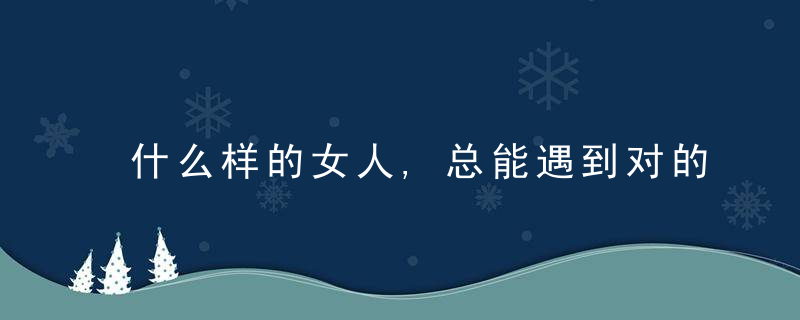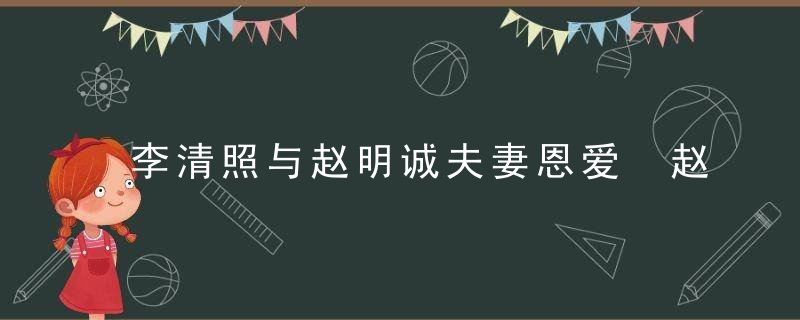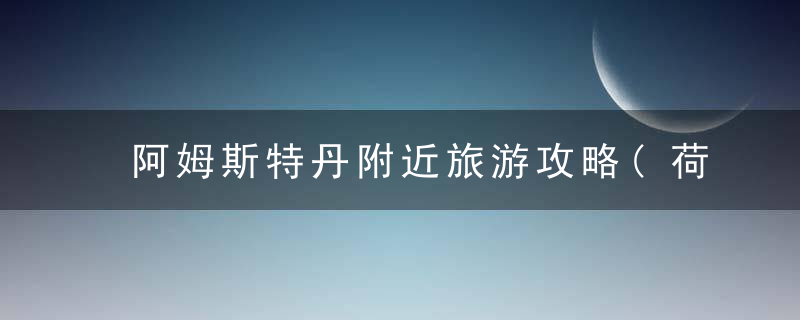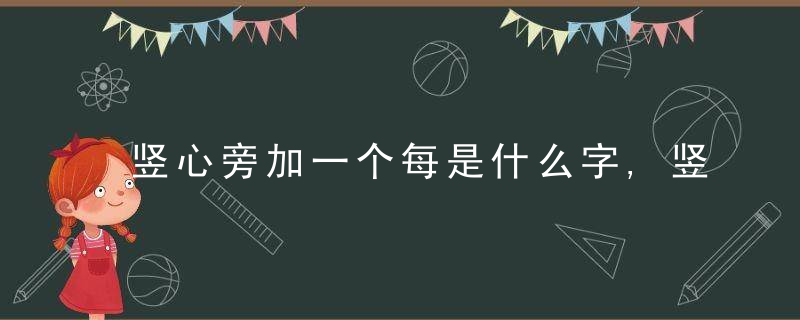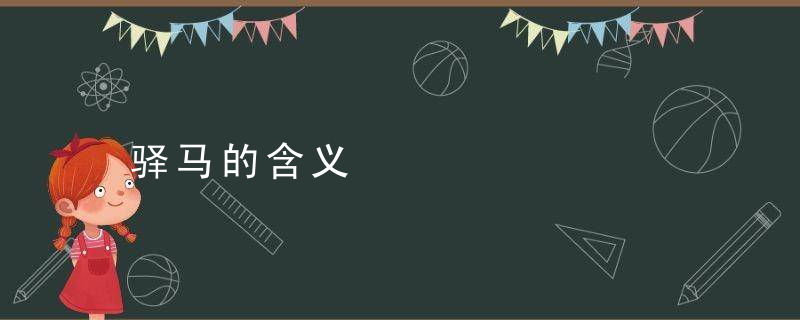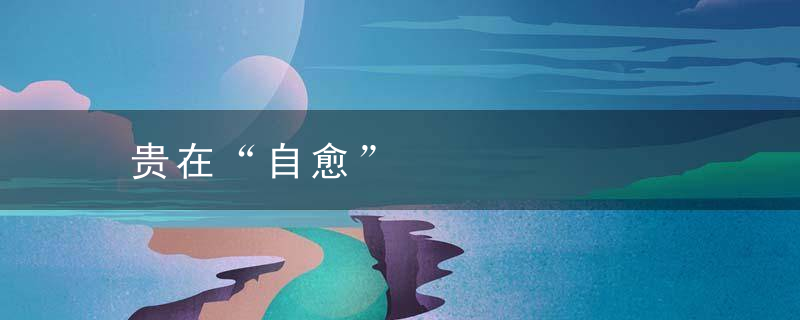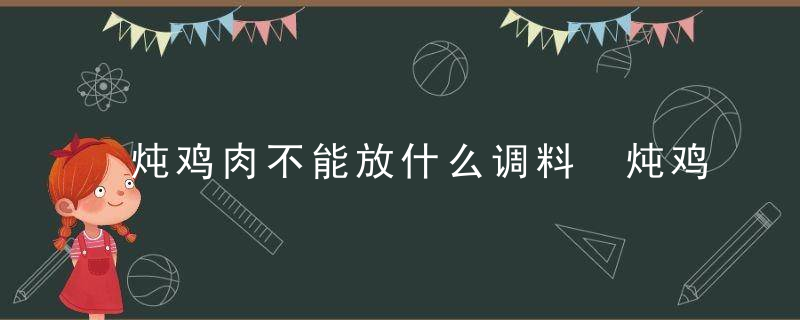半生繁华,半生空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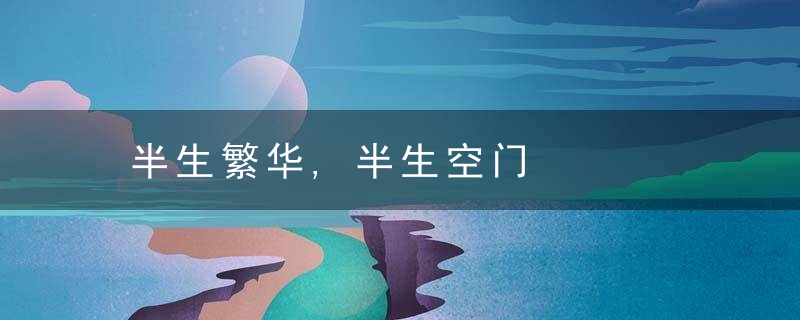
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终如瓦上霜。
他有着旷世之才,无论做什么,“做一样像一样”。
年少轻狂是才子,浪迹津沪,诚然一个翩翩公子;学成归国做教师,诲人不倦,自有天下名士风度;遁空门为法师,精研律法,终成一代律宗高僧。
前半生浪迹燕市,厮磨金粉;后半生晨钟暮鼓,青灯古佛度流年。
他的一生,活出了别人的好几辈子。
半生繁华
1880年,李叔同出生在天津一个亦官亦商的富裕人家,李家世代经商,到李叔同已经是名门望族,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李叔同其实是个“富二代”。
李叔同出生时,父亲六十八岁,母亲十九岁。
仿佛不是巧合:孔子出生时,父亲七十岁,母亲十七岁;欧阳修出生时,父亲四十九岁,母亲二十岁……
天高地厚的结合,往往产得麒麟之才。李叔同亦如此。
虽然李叔同五岁即遭父丧,他少年时的生活仍非常优裕。他的兄长和母亲很注重他的教育,延请了天津名士赵幼梅教他诗词,浙籍名士唐静岩先生教他书法篆刻,聪颖的李叔同小小年纪便积累了深厚的国学艺术修养。
8岁读四书五经,13岁攻历朝书法,15岁那年惊才绝艳,名噪一时。
不过,有意思的是,他的父亲李筱楼病重之时,自知命不久矣,请了几位高僧,于卧室朗诵金刚经,只允许李叔同入内探视,同聆佛音。在空寂悠远的佛音中,李筱楼安然而逝。
那时候,李叔同不过五岁,并未感受到亲人死别的撕裂之痛。反倒是丧仪的佛事活动,让他意犹未尽,以至于童年时经常装扮成大和尚,口中不断念念有词,叫着小伙伴们一起,煞有介事地模拟一场法事。
这种无忧无虑的嬉戏,犹如昙花一现,却绝不是巧合。
李叔同在上海票演京剧《黄天霸》造型
时至二十岁,李叔同已不但是才华横溢的文士,也是一个颇为放浪的富家公子。
他与一些艺界女子来往不断,“奔走天涯无一事。何如声色将情寄,休怒骂,且游戏”。
1905年,他的母亲病逝于上海,举哀之时,李叔同在数百中外来宾面前自弹钢琴,唱悼歌,寄托深深的哀思,甚至成了“民国奇事”。
之后,他便再无牵挂的东渡日本留学,说一口纯正流利的日语,并主攻音乐和美术,并立志要将新剧引入中国。
李叔同绘《少女》(木炭画,留日时作品)
李叔同自画像
1906年第一个中国戏剧艺术社团春柳社诞生,一年后,春柳社的第一次公演——《茶花女》开演,李叔同自告奋勇扮演女主角。
李叔同(左)在《茶花女》中的扮相
他一上台,装束时髦得体,体态优雅,动作轻盈,恰如人们心中的巴黎女子。
随后,一位日本女子走进他心里——诚子。
两人因为绘画相识,不久结发为夫妻,1911年4月,李叔同学成携妻回国。
1911年3月,李叔同(中)在东京美术学校毕业,此为毕业时的合影
回国后,应一位校长之邀,任浙江两级示范学校(后更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图画、音乐教师之职。
他大胆开设了人体绘画课程,请来男性裸模,“裸体写生”就此在中国美术教育开端。
李叔同最早在中国开设人体绘画的课程
在音乐课上,李叔同率先讲起了乐理和弹琴的指法。教材都是他亲自编撰,不少是他选曲填词或自创词曲的乐歌,一律都用五线谱记谱。
他填词选曲的《送别》,传唱至今
在他从事艺术教育的七年间,培养了不少现代中国早期艺术人才,漫画家丰子恺,国画家潘天寿、沈本千,音乐家刘质平、李鸿梁,古文学家黄寄慈、蔡丐因,艺术教育家吴梦非,作家曹聚仁等等,都曾师承于他。
至此,他的人生繁华旖旎,是风流富贵的翩翩公子,是无所不精的留洋才子,搞戏剧、做音乐、写书法、玩篆刻……是万众瞩目的艺术家,享尽风光。
但也许正如他15岁所写的诗:“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终如瓦上霜。”
父母早亡,生性敏感,加上早熟的思悟,其实让他过早地看到了人世间的无常与悲苦,他希望借助艺术,来安抚内心的痛苦,但却屡屡不得。
前半生的繁华,对他而言弹指一挥间,不值得留恋。
于是在盛名抵达巅峰之际,他抛妻弃子,遁入空门,从此苦修半生,留给世人难以揣测的玄迷。
半生空门
1918年的春天,一个日本女人和她的朋友,寻遍了杭州的庙宇,最终在一座叫“虎跑”的寺庙里找到了自己出家的丈夫。
38岁的他原来是西湖对岸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教员,不久前辞去教职离开学校,在这里落发为僧。
十年前他在日本留学时与妻子结识,此后经历了多次的聚散离合,但这一次已经是最后的送别,丈夫决定离开这繁华世界,皈依佛门。
人生本是修行,从俗世,到禅门,从身外,到心间,李叔同,不,应该是弘一法师从“戒”中领悟。
弘一法师说:“律己,宜带秋气;律人,须待春风。”
戒律是为律己,不为律人,他平时持戒甚严,口里却从不臧否人物,不说人是非长短。
他处处苦行,处处随缘。
他去虎跑寺断食二十天。晨钟暮鼓,青灯佛卷,远离浮华尘嚣,灵魂漂浮四十年,他似乎找到最终归宿。
他认为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小旅馆好,粉破的席子好,咸苦的蔬菜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
悲悯处世,福缘布施。
弘一法师圆寂时有两件小事令人深思。一是他圆寂前夕写下的“悲欣交集”的帖子,无论是这句话本身,还是他所写的墨宝,都使人看到一位高僧在生死玄关面前的不俗心境,既悲且欣,耐人寻味。
二是他嘱咐弟子在火化遗体之后,记得在骨灰坛的架子下面放一钵清水,以免将路过的虫蚁烫死。
他对万物都心怀悲悯,惜物、惜人、惜福。
林语堂说:“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
张爱玲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丰子恺说:“人生境界可分三等。一曰物质生活,此大多数也。二曰精神生活,即学者之流也,此亦不在少数。三曰灵魂生活,即宗教也,得其真谛者极少数耳。弘一法师则安步阅此三层楼台也。”
是的,李叔同,恰恰属于第三种。
艺术已经不足以安放他的心灵,所以,他选择了宗教,以此来超越无常的苦痛。
在《见字如面2》中,演员黄志忠朗读了弘一法师出家前写给日本妻子诚子的信:
这个决定看似薄情,但却又显得无比真实。
在很多人心目中,李叔同就是杭州那个决绝、冷酷、看破红尘、心如死灰的僧人形象。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生逢乱世,每个人都被裹挟在时代的洪流中,身不由己。但他,却犹如江流中的一叶扁舟,逆流而上,认真、勇敢地做自己。
一如丰子恺所言:他是一个像人的人。
他的后半生,“以戒为师”,晨钟暮鼓,青灯古佛度流年,淡泊无求,一双破布鞋,一条旧毛巾,一领衲衣,褴褛不堪,了寂无色,却供养出了更超然禅意的花枝。
电影《一轮明月》中有一段剧情:他的妻子知道已挽不回丈夫的心,便要与他见最后一面。
清晨,薄雾西湖,两舟相向。
李叔同的日本妻子:"叔同——"
李叔同:"请叫我弘一"。
妻子:"弘一法师,请告诉我什么是爱?"
李叔同:"爱,就是慈悲。"
所以,当日本侵华时,他举笔题词:“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
众生皆苦,生老病死,爱憎会,恨别离,求不得,放不下。
而佛,便是舍弃个人的爱恨,普度众生的痛苦。
一念放下,万般从容。
因为放下了个人的爱恨,也就回避了无常的悲苦,了悟小爱的无常,也便成就了大爱的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