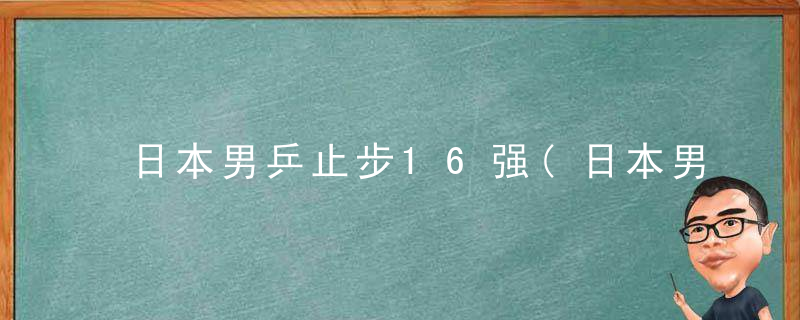我的人生经过了两次流放

他是世界华语诗坛泰斗、被誉为“诗魔”。
他以诗探万物之本,究生命之意,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2018年3月19日,洛夫在台北去世,享年91岁,
冬去春来,而他却不再。
“有时候炮弹就在头上打,我还在地下写诗”
名人面对面
| 追忆洛夫
“40年,离开家乡,走了以后,没有回去过”
2017年12月,余光中离世。三个月后,与其并称台湾诗坛双子星的洛夫也溘然长逝,中国诗坛的一个时代结束。时光倒退39年,香港落马洲,两位诗坛巨匠驻足遥望,近乡情怯,诞生洛夫最著名的诗篇《边界望乡》。
洛夫:1979年,好像我记得那时候3月份,香港中文大学邀请我去做访问,访问一个礼拜,那时候余光中先生在香港教书,他就带着我,自己开车,带着我到落马洲,落马洲就是香港跟深圳交界的一个地方。
他有个望远镜可以看到整个大陆上,你想想看,我有40年,离开家乡,走了以后,没有回去过,也不知道哪一天能够回去。从望远镜里面看到的故国的河山,就是过不去,就是有家归不得,那种心情非常痛苦,非常难过。
说着说着
我们就到了落马洲
雾正升起,我们在茫然中勒马四顾
手掌开始生汗
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
乱如风中的散发
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
一座远山迎面飞来
把我撞成了
严重的内伤
......
--《边界望乡》
1988年,洛夫终于第一次回到故乡衡阳,距离他阔别故乡,已经整整40年。
洛夫:我可以说是一直在战火中生活长大。最早是抗战、抗日,从10岁就开始吧。那个时候,天天开始是跑警报,日军来轰炸,就看着那些被炸死的人啊,在我家里的邻居啊,朋友啊,也死伤的很多。在衡阳,我还参加过半年的游击队,当时我只有15岁。就是日本军队来了,把衡阳占领了,所有的学校都停止了。
半年的游击生活中,做了一次很大胆惊人的事情。那个时候,我的家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房子,原来是开旅馆的,那个日本的军队一个小队驻扎在这里面。我那个游击队队长他就把我叫去,说日本军带了很多武器,我希望你今天晚上啊,有没有这个胆去偷他们的枪。
当时我就躲到一堵墙的底下,等士兵睡熟了以后,我再摸到那个房间里面去,那个时候烧煤油,有一个空的煤油桶,我看不清楚,晚上没有灯光,我就一脚踢了,那个煤油桶哐啷响,所有的日本兵就起来了,哇啦哇啦叫,吓得我赶快躲到另外一个墙角里面,待着不敢动在。后来他们一看,也没什么动静,以为是一只猫或者耗子,我还没有死心,还是继续等机会。
等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他们又睡着了,酣声四起,那我就还是就偷偷地摸过去,那个排击炮太重了,我也搬不动,大队长交给我的,希望我摸一个轻机枪,我就摸了一个轻机枪,那个轻机枪就摆在他们一个日本士官班长肩头上,差一点摸了他的头去了,摸了他的头那就完蛋了,这要抓了以后,那肯定就死路一条了,后来居然就把它偷出来了。
1949年,陆训部在衡阳招生,很多学生报名,洛夫也成为其中的一员。他说自己一直向往有机会乘船出海,看波涛汹涌,看海阔天空,因此在出发的时候甚至有些欣喜,却不曾想他与送行的母亲今生都没有再见面。
洛夫和妻子
“有时候炮弹就在头上打,我还在地下写诗。”
洛夫写诗、译诗、教诗、编诗五十余年,著作甚丰,在华语文坛影响深远。1954年,他和张默,痖弦共同创办了著名的诗刊《创世纪》,三人被称作诗社的三架马车。
《创世纪》创刊的三诗人:左至右洛夫、张默、痖弦
洛夫:我做总编辑差不多20年的时间吧,要求很严格很高。经常退稿退得很多,所以那些年轻诗人啊,很不服气,有时候写信来骂我,说我有什么了不起啊。我回他一封信,我说我并不是说你这个诗完全不用,希望你在某些地方修改一下,改得更好一点给我们寄来,我不是完全拒绝。这个他能接受,后来都成了朋友了。
洛夫说相比起痖弦和张默,自己人生中的负面经历更多些,因为处于战争中的时间太长,离死亡太近。可以说战争对于洛夫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最为人称道的长诗就诞生于金门的炮声中,而他唯一没有进行诗歌创作的两年恰是在越战中度过的。
洛夫:金门炮战的那个时候,我在军官外语学校,毕业以后,专门去接待外国来参观的一些新闻记者,因为他们要到金门去采访,所以我在那里待了整整一年。在这一年中,我有两个大收获,第一个,就是我认识我太太,我太太她就是金门人,在金门那个时候是一个小学教员。关于另外一个收获,就是我有一首长诗,叫做《石室之死亡》。
只偶然昂首向邻居的甬道,我便怔住
在清晨,那人以裸体去背叛死
任一条黑色交流咆哮横过他的脉管
我便怔住,我以目光扫过那座石壁
上面即凿成两道血槽
我的面容展开如一株树,树在火中成长
一切静止,唯眸子在眼睑后面移动
移向许多人都怕谈及的方向
而我确是那株被锯断的苦梨
在年轮上,你仍可听清楚风声、蝉声
......
--《石室之死亡》
洛夫:金门的所有的军队、部队都住在那个山洞里面,就是坑道,住在坑道底下。一个一个洞穴在里面,那才是真正的石室。部队住在里面,炮弹打不到里面。我就在里面住了一年,有时候炮弹就在头上打,我还在地下写诗。
洛夫和妻子
“变是天才的另外一个名称 ”
洛夫说自己的人生经过了两次流放,一次流放到台湾,一次流放到温哥华,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的选择。这两次流放造就了洛夫最为人称道的两首佳作《石室之死亡》和《漂木》。
洛夫:我刚到温哥华来1996年,那一年下很大的雪,我就在我的书房窗口看雪,看雪而且写大字,把衣服脱掉写得满身是汗,外面很冷,里面室内很热,因为写字很热嘛,就形成很大的一个落差,是一个很微妙的意思,后来我就把我的书房名字,起了一个书斋的名字,叫做雪楼,所以以后所有的朋友都知道,雪楼就是洛夫的这个书房。
2001年,三千余行、新文学史上最长的诗篇——《漂木》出版,并且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震惊世界华语诗坛。
洛夫:就是因为没得奖,我觉得这个事情何必去讲它呢,所以我自己的资料里面,我的小传里面,我不提这个,我没提这个。我觉得长诗是对一个诗人很大的考验,它不仅仅是需要一种灵感,需要一种心灵的启发,更需要对那个诗的结构的把握,这个掌握不了,就松垮下来,像散文一样了。所以我那首诗花了整个一年的时间才把它写出来。
没有任何时刻比现在更为严肃
落日
在海滩上
未留一句遗言
......
--《漂木》
洛夫:过去我说了一句话,我说变,就是一个作家的变,不断地变化,变是天才的另外一个名称,你江郎才尽你就是老是死守着那个规则,诗歌的那个规则,诗歌的语言,诗歌的意象,固定了,就适应那些。你不知道如何去变化它,不知道如何去调整你的语言,调整你的意象,表现的技巧也固化了,当然慢慢写就死掉了,就江郎才尽了。所以我就经常地不断调整自己,从这个诗的观念方面,从美学的观念方面,一直到表现的方法,表现的技巧方面,我都一直在变化。
所有中外的诗歌都是如此。能够存世不衰的通常都有比较大的思考,形而上的东西,虽然不是非常流行,不是大众化的东西啊,但是它能够保持一种永恒的生命,就是有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人来读它,这样就是它的艺术生命永远在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