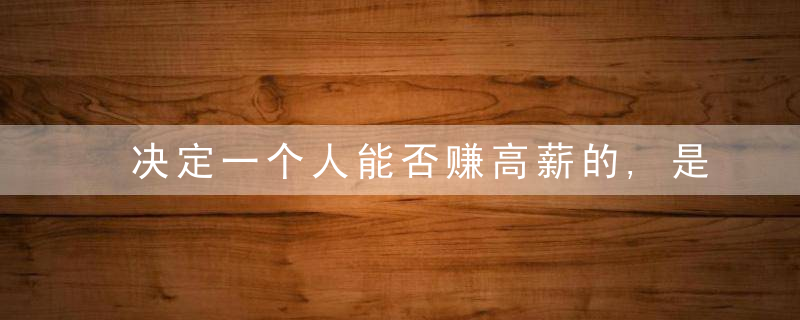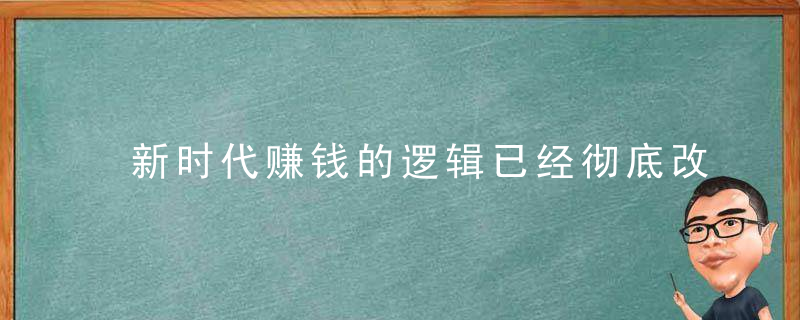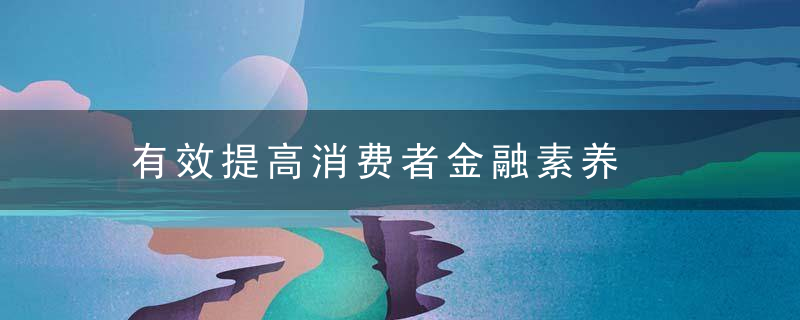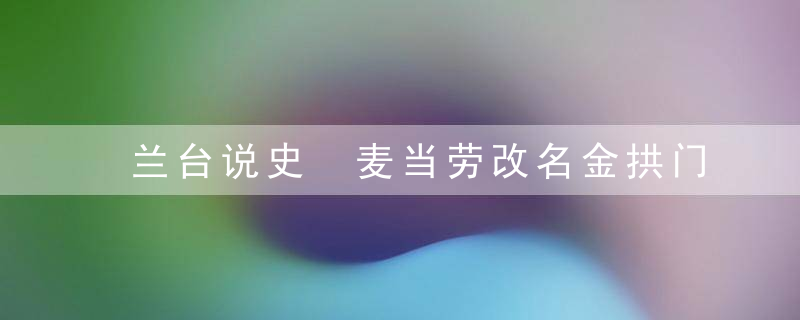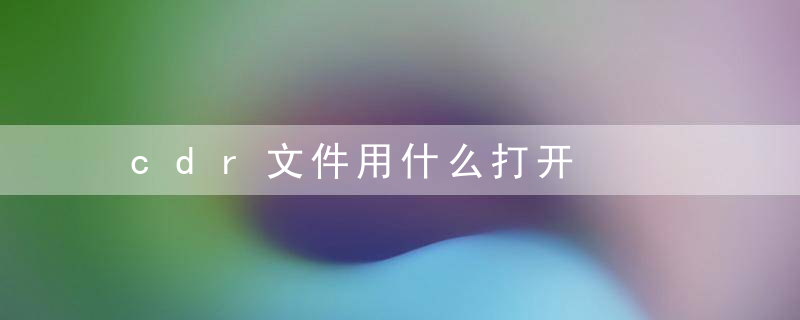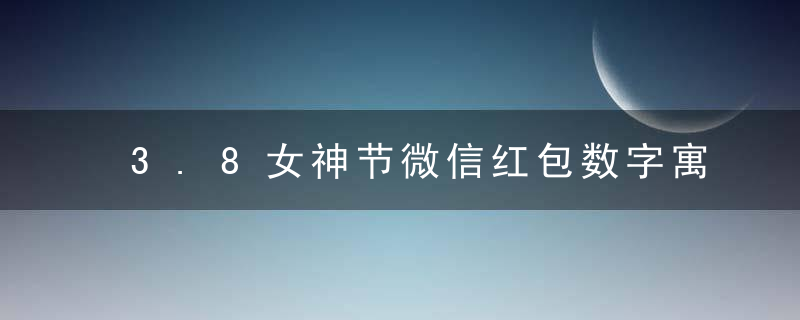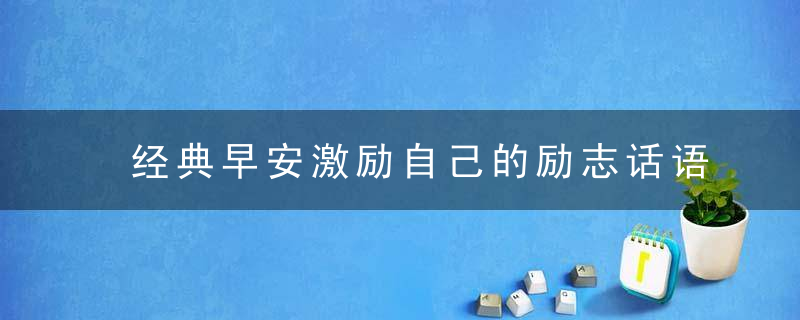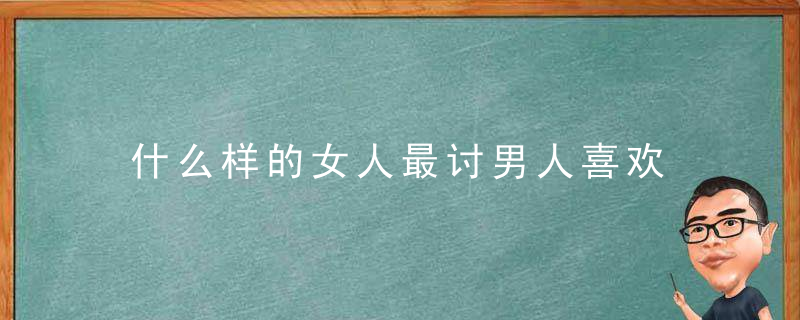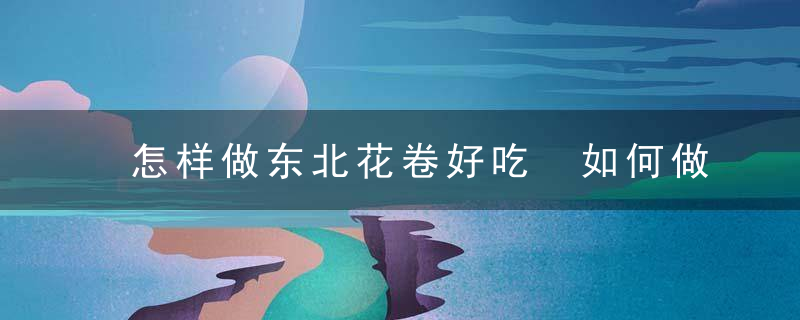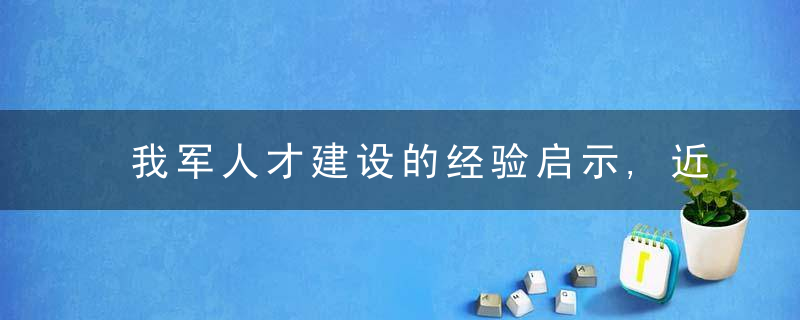中國金融危機遠在天邊

這裏尤為值得關注的是美國。特朗普就職以來,道瓊斯指數從18000點升至26000點,上漲了整整8000點。道瓊斯指數每上漲一個點,美國人民的財富就增加15億美元,因此總共增加了12萬億美元(75萬億人民幣)的財富,相當於2017年美國GDP的2/3,超過中國GDP的總和。強勁的財富效應助推了美國人民的消費和整體經濟的走強。最新數據顯示,美國不僅整體經濟持續走強,“再工業化”也有了突破性進展。2017年美國工業增速自2007年危機以來甚至是90年代初以來,首度超過GDP增速。如果計算美國2018年頭4月的工業增速年率,已經高達6.7%,可比肩同時期中國工業增速了。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2018年一季度,中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8%,其中3月份增速為6.0%,比1~2月份回落1.2個百分點。進一步分析美國工業的強勁復甦,主要又是重工業領域帶動的,因此如果沒有特朗普引發的股市大漲提振美國的消費信心,以及對歐日的貿易戰擋住重工產品進口從而提振了美國重型製造業的信心,是不會出現這種情況的。“特朗普經濟週期”是實實在在的。
美國經濟的走強更加強化了美國的通脹預期,由此加大了美聯儲收緊貨幣及加息政策的必要性。當前,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達到4年新高,美國十年期國債價格今年以來跌幅達到5%。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最新會議紀要顯示,美聯儲官員預計經濟將加速增長和通貨膨脹將會加劇。經濟學家們普遍預測,美國大概率在6月份還會加息一次,今年還將繼續加息2到3次。同時,美國經濟的強勁對比於歐洲及日本經濟的疲軟導致了美元指數的走強。歷史上,美元走強和美聯儲加息周期沒有直接對應關係,主要還在於美國與歐元區、日本以及英國等主要經濟體在經濟增長周期和貨幣政策周期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以及市場對此預期不斷變化造成的資金流向變化。今年以來,這些經濟體宏觀數據出現惡化,而美國經濟保持相對穩健,刺激美元指數再次上漲。應該說,這次美元指數走強具備較好的宏觀基礎,也可以說是對美國長期相對穩健基本面的回歸。從下面兩個圖,我們分別對比中美國債利差和中美匯率,以及德國和美國國債利差和美元兌歐元的匯率,目前美元指數仍然具有較強的支撐,美元相對於歐元和人民幣都有上漲的空間。美元是國際主要的貿易結算貨幣、儲備貨幣和“錨”貨幣,是全球流動性的“總閥門”。美元利率走高、美元指數走強,必然引發國際資本回流美國本土,導致全球資金面緊張和利率水平上升,進而在世界經濟鏈條上相對脆弱的國家引爆金融危機。無論是1982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2007年的美國次貸危機、還是2009年的南歐債務危機,美元利率走高及美元指數走強都是很關鍵的因素。而目前土耳其、阿根廷等新興市場國家已率先出現了股、債、匯市的巨幅動蕩,特別是貨幣匯率的自由落體式下降,這讓投資者的擔憂不斷上升。除阿根廷、巴西及土耳其等國受不斷增強的資本外流壓力影響、貨幣快速貶值外,亞洲貨幣也均出現一定幅度貶值。其中,印度盧比兌美元的匯率自今年年初以來已下滑超過6%。香港港幣受到資本利差擴大和資本外流衝擊,近一個月以來一直在死亡線上掙扎,可能成為亞洲貨幣風的風暴口。在美元放鬆以及美元指數走低的時期,低成本的美元營造了全球寬鬆的貨幣環境。而在美元指數上升的最近幾年,新興市場國家仍不斷借債尤其是美元債以繼續保持經濟繁榮。國際金融協會(IIF)4月數據顯示,2012年-2017年的五年時間裏,包括所有部門在內的全球債務增長了25萬億美元,新興市場國家的債務從42萬億美元增長至63萬億美元,佔全球增量的84%,其中絕大部分為美元債。而中國的情況可能非常嚴重。眾所周知,貨幣洪水助推中國經濟一直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但也蓄積了未來的洪災風險。2018年3月份,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數據,人民幣廣義貨幣供應量達到173.99萬億元或27.67萬億美元,一舉超過“美元+歐元”M2的總量27.66萬億美元的規模。中國經濟總量不如美國,也比不上歐盟,但現在中國一家的貨幣供應量已超過美歐兩家之和。這意味着中國巨大的貨幣洪災已如懸在天上的黃河之水。
在過去幾年,中國的資金外逃一直是一個大問題,嚴重影響到中國國內的投資,不得已在2016年我們用了房地產泡沫來繼續吸引資金保持在中國國內。而在過去一個半月的時間裏,大約有80億美元的資金逃離了發展中國家的債券與股票市場,相信未來這一趨勢還會繼續。中國的情況又將如何?可想而知,資金外逃的壓力只會加大不會減小。以目前情況判斷,本次美元指數反彈的高點必然在100以上。加上美國鐵心了要壓縮對華逆差,意味着未來中國外儲最大的來源,面臨着被美國掐斷的風險。如果在這波美元走強的過程中,中國的人民幣匯率不能維持在6.9以上,那麼人民幣匯率貶值的預期將再度回頭並成為市場主流。而人民幣的貶值趨勢可能會再次引發資金外逃,從而令中國經濟面臨資金失血以及泡沫被刺穿的危險。
美元回流的風險本來就夠大的了,而現在中國還將面臨美國貿易戰的嚴峻挑戰。今年以來,特朗普發起的貿易戰已經對全球貿易特別是中國的出口造成了非常嚴峻的負面影響(下圖顯示全球貿易增速下滑)。數據顯示,2017年進出口貿易對中國GDP的貢獻約9%,但是到了2018年一季度,貢獻就迅速變成了負數。2018年3月份,中國出口金額同比超預期下滑變成了-2.73%。
展望未來,壓力顯然會更大。美國東部時間5月29日,白宮發佈聲明稱,美國將在6月15日前發佈針對中國500億產品加徵25%關稅的最終產品清單,在6月30日前公佈對華技術投資和加強技術出口管控的限制措施,並將分別在前述日期後“很快實施”。白宮還稱將繼續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框架下,針對中國在知識產權許可方面“違反了《貿易相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的歧視性行為”展開訴訟。美國同時還決定對歐盟、加拿大、墨西哥鋼鋁製品課徵懲罰性關稅,各國均表示將推出反擊措施。股市對全球貿易戰作出劇烈反應,因全球貿易是全球經濟復甦的基礎,而貿易戰令全球經濟復甦蒙上陰影。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戰,不僅僅涉及到關稅以及貿易順差的問題,更涉及到美國對華戰略的調整,即中美不再以合作關係為主,而以戰略競爭關係為主。如果僅僅是500億到600億的出口產品加稅,對中國GDP的影響只有0.1%到0.2%,大可忽略不計;但如果是全面爆發貿易戰,則後果則不堪設想;更嚴重的是,如果貿易戰演變成新常態甚至中美“新冷戰”,影響就更是長期和深遠的,甚至有可能改變對中國大國崛起的長期向好預期以及對中國經濟向上信心的嚴重打擊。對於中國當前發展環境的變化,習近平主席在5月28日的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會議上用了“三個逼人”來加以強調即“目前形勢逼人,挑戰逼人,使命逼人”。在動蕩的國際環境下,從去年12月以來,強力監管一直是中國金融業和金融市場的主基調,顯明意圖在經濟比較平穩的時候主動釋放金融風險、排除地雷。從全社會融資水平來看,累計同比增速大幅下降。由於資管新規的影響,銀行將巨額的表外業務併入表內,民營企業和部分地方融資平台過去在銀行借不到錢,需要依靠理財產品、資管計劃融資,但是表外融資受到嚴厲限制,其融資受到很大的限制。
在此背景下,中國國內近月中國債券市場出現了連續違約,密度之大、頻率之高前所未有。2018年以來,億陽集團、神霧環保、富貴鳥、凱迪生態、中安消、上海華信、大連機床、春和集團等相繼爆出債券違約,其中多家是上市公司。截至2018年5月31日,債券違約已達20隻,違約金額167億,同比增幅超過30%。在二級市場,5月21日,東方園林發佈公告,稱公司原計劃發行10億公司債券,但實際發行規模僅有0.5億,只是一紙公告,瞬間引發市場恐慌,500億市值,一週時間跌去百億。中國多數企業習慣於用短期融資去解決長期投資的資金需求,一旦無法借新債償舊債,資金鏈便面臨斷裂的窘境。根據中誠信國際測算,預計2018年實際需要償還的信用債規模約為5.3~5.5萬億元,企業再融資壓力仍然不小。
5月15日,劉鶴副總理在“健全系統性金融風險防範體系”專題協商會上發言指出:“要使全社會都懂得,做生意是要有本錢的,借錢是要還的,投資是要承擔風險的,做壞事是要付出代價的。”此話意味深長,讓市場意識到:中國2017年以來主導的去槓桿不會一蹴而就,必定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問題在於,正確的做法在目前風聲鶴唳的時間點上會不會變成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呢?我們的判斷是,就在中國去杠桿的重要時刻,美國對華發起了貿易戰,實則增加了中國對金融風險防範的難度和複雜度,央行和相關監管部門都將處於騎虎難下的局面。如繼續加槓桿穩增長,則容易重蹈日本的覆轍;如繼續堅定地去槓桿,則在對外貿易收縮的情況下,貨幣被動緊縮也許會觸發周小川所提到的“明斯基時刻”。在這種情形下,的政策選擇將被逼到日益窄逼的鋼絲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