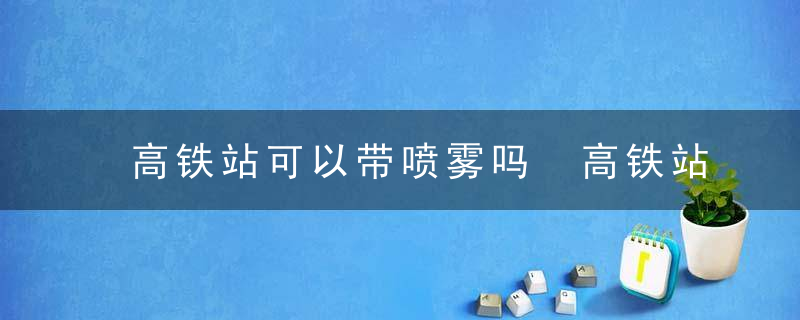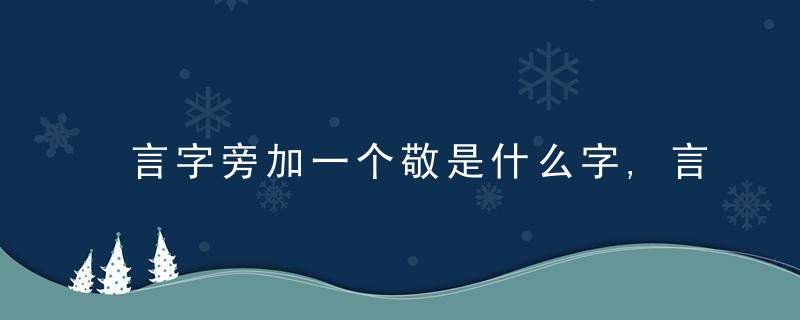人生不开怀,须读丰子恺

丰子恺
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
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
——丰子恺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天,丰子恺翻开上海某报纸,一篇文章赫然映入眼帘——《丰子恺画画不要脸》。
丰子恺狐疑,素来温润如他,怎会招致如此诋毁。
原来文章并非对他人身攻击,评论的是他所画《乡村学校的音乐课》。
画中的孩子们没有眼睛鼻子,却一个个大张着嘴唱歌。
数笔简单铺白的线条,孩子们投入唱歌的神态、课堂上欢乐的氛围便跃然纸上。
这样的画,在他之前没有人画过,在他之后,也没人画过。
泰戈尔曾称赞:“用寥寥几笔,写出人物个性。脸上没有眼睛,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看什么;没有耳朵,可以看出他在听什么,高度艺术所表现的境地,就是这样。”
1898年,浙江石门镇的丰家迎来第一个男丁,在他之前,母亲已经生了六位女孩了。
父亲给他取名为丰仁,小名为慈玉,希望他心怀慈悲、温润如玉。
后来中学国文老师单不庵给他取了双字大名“子顗”,又改为“子恺”。
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丁,丰子恺6岁进入私塾读书,那时他就对色彩和线条很感兴趣,便将《千字文》上出现的各色人物,逐一填色,活泼生动,趣意盎然。
私塾先生也不拘一格,见到丰子恺的“恶作剧”,便鼓励他画张孔子像,他也不拘束,画得惟妙惟肖,从此“小画家”的称号就流传开了。
1914年,16岁的丰子恺离开家乡进入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求学,在这里他遇到了慈母般的夏丏尊和严父般的李叔同。
夏丏尊担任舍监,对学生们无微不至,这让从家乡小镇初来杭州、性格腼腆的丰子恺倍感温暖。
夏丏尊也教授国文,丰子恺很在意他的看法,每写一篇文章,便在心理自问:“这样写,夏先生会满意吗?”
老师提倡“白话文”,这种通俗平易的主张,更是影响了丰子恺一生的创作,从文章渗透到了漫画。
李叔同的绘画课教石膏写生,学生们大眼瞪小眼,无从下笔,他就画好一张示范画,贴在前面,以供临摹。
丰子恺却偏不,他要啃这块硬骨头,按照李叔同教的方法,对着石膏体,一笔一笔画了下来,每节课如此,进步神速。
一天晚上,李叔同将他叫到身边说:“在我所教的学生里,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快速进步的。”
老师的话轻轻的,像春风吹入了一颗艺术的种子,从此在少年丰子恺心里生根发芽了。
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下:“当晚这几句话,便确定了我的一生。”
学校宿舍的集体生活、繁复约束的校规,都令丰子恺喘不过气。
一次,他与训育主任发生了口角,两人还厮打了起来,气不过的训育主任将这件事上报了学校,并要求学校上报教育厅,开除丰子恺学籍。
会场上老师们都不作声,只有平时话极少的李叔同开口了。
他先是承认,学生打老师固然错误,但这也有老师教育不当之过,理应双方都有责任。
再者,丰子恺天资甚好,过往也无犯错史,如若因一件可以改正的事,就牺牲他的前途,实在草率。毕竟学校是育人场所,绝非毁人之地。
李叔同声音不大,却很有分量。最后学校决议,丰子恺记大过,李叔同亲自带他登门向训育主任赔礼道歉。
事后,李叔同又将丰子恺叫到办公室,翻开《人谱》,一字一顿地念道:“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
先做有器识的人,再做文艺,知行合一,这话丰子恺铭记了一生,也践行了一生。
正如他说:“大约是我的气质与他有一点相似,凡他喜欢的我都喜欢。李先生的人格和学问统治了我的感情。”
李叔同上课、下课都会朝讲台下的学生们鞠躬,有人在地上吐了痰,他会轻声说“下次不要这样了”,微微一鞠躬,夹着书本走出了教室。
虽然温和,自有一股威严,学生们往往不敢再犯。
难怪夏丏尊说:“他做教师,有人格作背景,好比佛菩萨的有“后光”,他从不威胁学生,而学生见他自生敬畏,他从不严责学生,而学生自会用功。”
1919年,从浙一师毕业的丰子恺,追随老师李叔同的步伐东渡日本留学。
留日期间,他废寝忘食学习了日语、美术、音乐,更是找到了创作的新方向。
竹久梦二的画浅白洗练,通俗易懂,在日本广受民众欢迎,以及在日本颇有名气的中国画家曾衍东,二者的画作,正与丰子恺一直苦苦追寻的艺术风格一拍即合。
从此,他丢弃了西方的油彩、画布,回归了东方的纸墨。
十个月后,丰子恺回国,应邀回到了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执教音乐和美术,他的同事有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等。
谈笑有鸿儒,月下倚栏品茶、聊聊诗画自然少不了,丰子恺便创作了这幅《茶》。
1924年发表在杂志《我们的七月》上的是相似意境、画风更为简洁清透的《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也是丰子恺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作品。
仔细看,画上的新月朝右,有人提出残月才是朝右的,丰子恺犯了常识错误,实在贻笑大方。
后来天文学家出面解惑:画中所绘是后半夜新月,朋友小聚,尽兴聊到深夜正好对应此景。
外行人弄巧成拙,殊不知丰子恺心思之细腻,洞察之深刻,平淡的笔风之下,蕴含了深深的情致。
郑振铎曾说,“虽然是疏朗的几道笔痕,我的情思却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
朱自清也说:“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一幅幅漫画,就如一首首小诗,带核儿的小诗,我们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
后来,郑振铎张罗着要给丰子恺出画集,约上叶圣陶、胡愈之一起去选画,结果一股脑带走了全部画作。
1925年《子恺漫画》出版了,中国终于有了第一本漫画集。
上世纪30年代,他的画遍及大街小巷,馄饨摊、理发铺,车夫脚夫,小商小贩手里都是,人人喜闻乐见。
好景不长,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丰子恺被迫回到了阔别了18年的家乡石门镇。
他用积攒多年的稿费,盖了一座书斋,老师李叔同赐名“缘缘堂”。
外面炮火纷飞,石门镇依旧波澜不惊,缘缘堂更是。
丰子恺在缘缘堂写字画画,闲来给孩子们读鲁迅的文章,孩子们听哭了,他一抹眼睛也是泪水。
不仅要自己的孩子知道日本人的暴行,他还要用手中的画笔,画出一部日寇侵华史,让所有国人都能看懂,认清侵略者的面貌。
1937年,当敌机飞过石门镇,投下罪恶的炮弹时,丰子恺正在缘缘堂画《日本侵华史》,九岁的小女儿丰一吟还在学校。
炮弹击中了学校,顷刻间一切都毁了,丰一吟狂奔回了家,这时丰家老小都躲在八仙桌下,丰子恺听到小女儿的声音,急切地把她招呼了进去。
万幸,一家人团聚了。
当丰子恺再从家中走出来时,石门镇已经换了天地。
仅缘缘堂后门就躺了六具尸体,当天三十二人身亡,随后陆陆续续死了一百多人。
这对于与世隔绝的石门镇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
丰子恺在家乡度过了五年平静的时光,直到这一年,石门镇也不再是他的堡垒了。
丰家和那时的大部分国人一样,踏上了流亡的逃难之路。
再见了,缘缘堂的万卷藏书;再见了,石门镇的平静岁月。
好不容易乘上了逃难的小船,丰子恺却辗转难眠,他的行李中有未完的《日本侵华史》。
虽说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可一旦被查出,必将连累家人和同船的人们。
想到这里,他抱着这部饱蘸民族愤慨的画稿,走到船头,扑通一声,画稿沉入了漆黑的河道。
而丰子恺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扑通一声,好比打在了我的心上。”
流亡之路,远比想象中艰辛。
一次,丰子恺将全家人都安排到了车里,实在挤不下了,他就跟车走,一天走了九十多华里。
雪上加霜的是,缘缘堂在空袭中夷为了平地,亲戚只捡回了几块搭建的石头和焦黑的门板。
缘缘堂没了可以重建,可是乡亲们呢?
杜甫为贫苦百姓大发感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当日军的铁蹄践踏家乡这片土地,丰子恺悲鸣:“恨不得有条大船,把乡亲们都接出来。”
他没有大船,可他有画笔,他把痛都用画笔传达了出来。
在沿途画下这《无头图》。
空袭也,
炸弹向谁投?
怀中娇儿犹索乳,
眼前慈母已无头,
血乳相和流。
在哺乳的母亲,被炸掉了头颅,怀中的婴孩还在索乳。
1929年,李叔同50岁寿辰前,与丰子恺约定,“我五十岁生日你画五十幅画,我写五十幅字,我六十你画六十幅我写六十幅。”
丰子恺回信道:“是寿所许,定当遵嘱。”
转眼1939年到了,李叔同60岁了,他和老师李叔同约定的《护生画集》第二集也要开始了。
流亡路上,生灵涂炭,战争惨状,活似人间炼狱。
但第二集《护生画集》却更恬静了,越在绝望恐,眼不见光明的处境中,人们对美的渴望越强烈。
毫不夸张的说,这一集《护生画集》让人看到了希望。
却有人不这么想,他的多年好友曹聚仁说:“1939年出版的《护生画集》十分荒唐,可以烧毁了。”
好友都不理解他的苦心,丰子恺愤然与之绝交。
画《护生画集》的同时,丰子恺也在画鲁迅的《阿Q正传》。
漫画版《阿Q正传》的诞生一波三折,丰子恺画了三遍。
早年在上海他画完了,学生带去印刷,不料一二八事变爆发,原版画稿与锌版一并被炮弹吞噬。等到丰子恺逃亡广州,又画了一次,在付印时,画稿却再度遭遇厄运,化为灰烬。
直到1939年,这一次漫画《阿Q正传》54幅画稿终于面世了,丰子恺的头发已经全白了。
丰子恺在漫画《阿Q正传》写道:“敬告鲁迅先生在天之灵,全民抗战正在促吾民族之觉悟与深省,将来的中国,将不复有阿Q及产生阿Q的环境。”
唤醒国人的自觉意识,这是他心中义不容辞的责任。
鲁迅弃医从文,以笔为器,而丰子恺的武器是画笔。
时人评论:“鲁迅的文章里,有丰子恺的画,丰子恺的画里,有鲁迅的精神。”
1942年,老师李叔同在福建泉州圆寂,丰家一家刚逃难到重庆,只能遥寄缅怀。
从此与老师再也不是天各一方,而是阴阳两隔,丰子恺心痛得无法言语。
很久之后,他说:“我时时刻刻防他死,同时时刻刻防我自己死一样。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所以我并不惊惶,亦不恸哭。老实说,我的惊惶与恸哭,在确定他必死的一日之前早已在心中默默做过了。”
1946年,恩师夏丏尊离世,临终前丰子恺仍旧未能见面。
两位老师相继离世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但日后漫长的折磨中,老师仍旧是他心头的信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丰子恺迎被选为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他开出了三个条件:不坐班、不领工资、不开会。
后来他只领一点薪资,只参加重要的会议,其余时候都在家中画画、翻译。
年近花甲,他着手翻译《源氏物语》,满怀虔诚,手稿上每个字都写得端正秀丽,文风十分古雅。
1958年,《源氏物语》翻译完成,可直到老人去世,也没等到它面世。
1959年,《护生画集》第四集80幅已完成,却被当作封建残余,难以刊印,丰子恺只得交与新加坡的广洽法师付印。
这件事为日后的灾难埋下了祸根,丰子恺生命中另一场风雨即将到来了。
1963年,周作人同友人说:“丰君的画,我向来不甚赞成,形似学竹久梦二者,但是浮滑肤浅,不懂 ‘滑稽 ’。”
对于丰子恺的批判拉开了序幕,越来越多的人批判他,批判他不写工农兵形象,批判他不歌颂社会主义,批判他揭露社会阴暗面过多,就连画猫狗,也成了攻击的借口。
冥冥之中,或有预感,原本1969年刊发的《护生画集》第五集,丰子恺赶在1965年就提前完成了。
1966年来了。
丰子恺成了“上海十大重点批斗对象”,家被抄了,书画被没收焚毁了,就连他蓄了三十几年的胡须,也被强行剪了。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他反倒摆出一副乐观的样子,捋着空空胡须,吟叹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野火还在烧,丰子恺的春风却迟迟不来。
快70岁的他又被拉出去批斗了,跪在画院的地上,有人用滚烫的热浆糊浇了他一背,剧烈的灼痛让老人怎么也站不起来,身后的皮鞭毫不留情地挥下、抽打、催促着快走。
这一天,对于饱受身体与精神折磨的丰子恺来说,格外漫长。
回到家中,女儿为他倒了一杯以前常喝的老酒,端起酒杯,他的泪就落下来了。
一生行善、崇尚美育的丰子恺,怎么也不明白为何要这样针对他。
明明1959年周总理还接见他,拉着他的手问:“你还画吗,画的多吗,要为人民多画一些画。”
陈毅说:“彻底改造自己,将心交与人民。”这话他也很赞同,还画成了漫画,他的心始终和人民在一起,这又有什么错呢。
喝完这杯酒,他恢复了往日的平和,走入书房继续工作了。
文革期间他白天挨批斗,晚上埋头翻译书籍,完成了《大乘起信论新释》《落洼物语》和《竹取物语》的翻译。
还写了一本《缘缘堂续笔》,笔触依旧诙谐轻快,不乏情致,几乎没有人相信他是在那样的处境中写出的。
再后来,丰子恺被下放到干校改造了,便不能工作了。
一次女儿来干校看他,百十来亩的田地上,他正佝偻着腰、颤颤巍巍地摘棉花,动作迟缓,步履蹒跚。
他见了女儿,还宽慰道:“他们见我年纪大,就安排了这种不太重的活给我。”
干校条件极差,丰子恺在日复一日的身体、精神双重煎熬中,健康每况日下。
吃水要去河里打,丰子恺行动不便,一天就只用一盆水,没人知道那么多日夜,他是怎样靠一盆水过下来的;
住的地方四处漏风,一下雪,雪花就对着脸飘到枕头边上;
还时常半夜紧急拉练,他年纪大了,穿衣动作慢,去晚了,又要遭到辱骂,他索性睡觉就不脱衣服了。
超负荷的劳动量、恶劣的生活条件,再加上无休止的精神折磨,年迈的丰子恺终于垮了。
他被查出肺部感染,不能再劳动了,医生开了证明,才得以在家休养。
1979年还远未到,他就要画《护生画集》第六集,和老师的约定还差这最后一百幅了,他唯恐自己的身体撑不到那时。
可倘若配合治疗,按时吃药,一旦病情好转就要返回干校,《护生画集》就更遥遥无期了。
1973年,75岁的丰子恺开始和生命赛跑了,他把药都偷偷扔掉,每天凌晨四点起床画《护生画集》。
造反派随时都可能给闯进家里,给他安上更多罪名,施与更惨痛的惩罚,家人担心他的安危,就把画具都藏起来。
丰子恺苦苦哀求,像个孩子,是啊,如果不能继续画画,他的生命之光也就将熄了。
从第一幅《马恋其母》到第一百幅《首尾就烹》,《护生画集》第六集完成了。历时45年,共计450画,从一到六集,《护生画集》也终于圆满了。
这比原定的1979年,提前了六年。
丰子恺的《护生画集》从老师五十岁寿辰画到了百岁冥诞,他经历了抗日逃亡、建国后的荣光、文革无休止的批斗。
无论在哪,情况如何,他都谨记嘱托,恪守诺言,是寿所许,定当遵嘱。
1975年,78岁的丰子恺给自己画了张日历,每过一天就划去一天,他知道生命也将走到终点了。
春天他在家人陪同下,回了一趟石门镇,乡亲们夹道欢迎,让他写字画画,他都高兴得应允。
走的时候,丰子恺说:“明年一定再来。”
只是这明年,永远也不会来了。
半年后,丰子恺忽然说:“不知道周总理过得怎么样呢?”
说完不久,他也与世长辞了。
丰子恺一生信奉美,无论战争逃亡,还是文革批斗,他都一如既往歌颂和平、善良、纯真。
可以说,他用一颗温柔博大的心,包容了不公和丑恶,再用画作翻译成美感化世间。
“他画画的手和笔,不是自己的手和笔,是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心灵。”
美学大师朱光潜也说:“形成丰子恺人品和画品的,主要还是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
丰子恺深爱着这片土地和人民,所以在他的画里,“ 一片片的落英,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