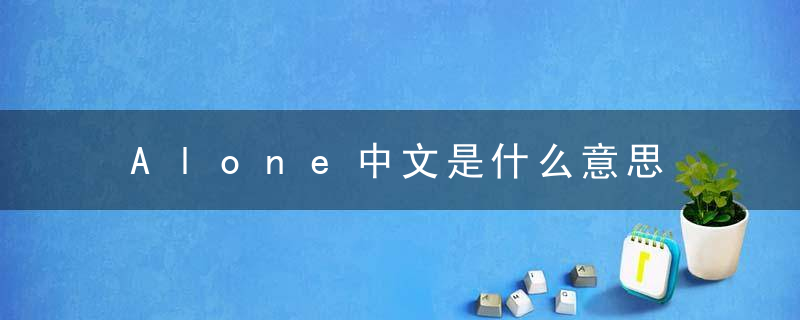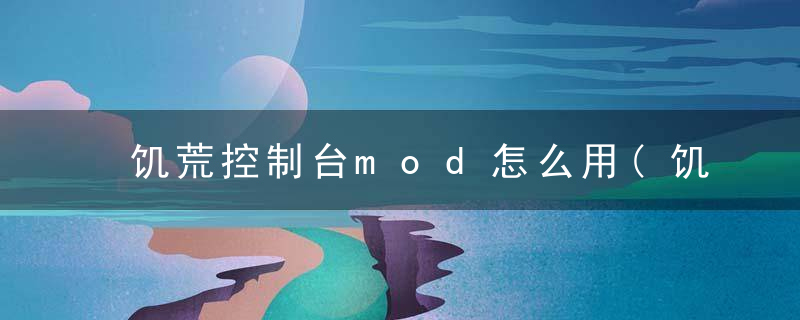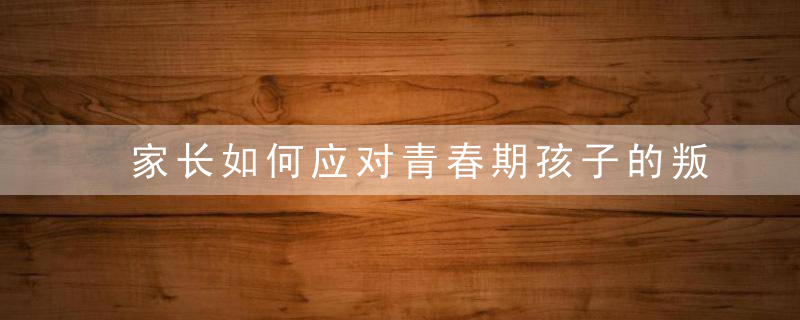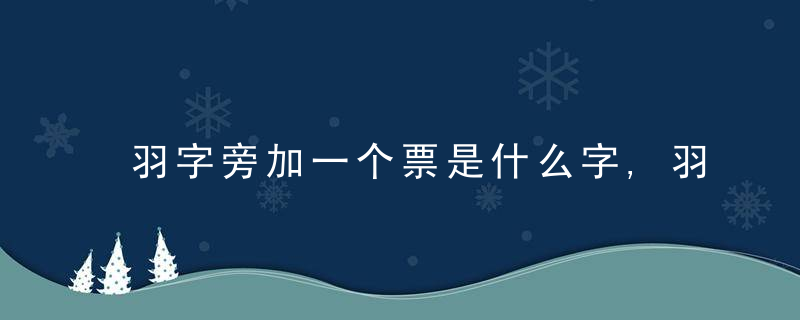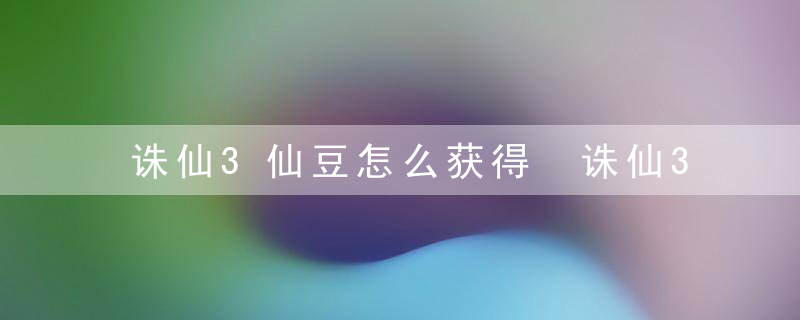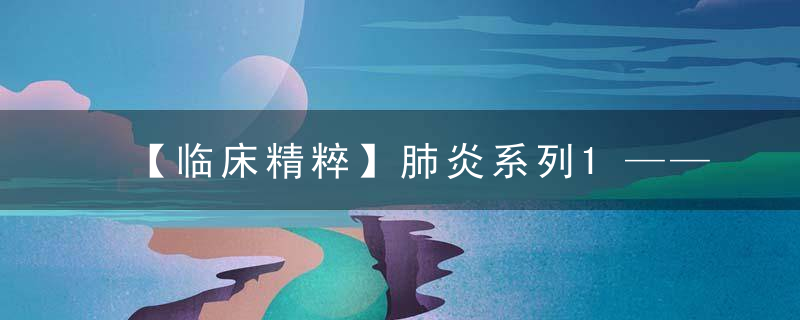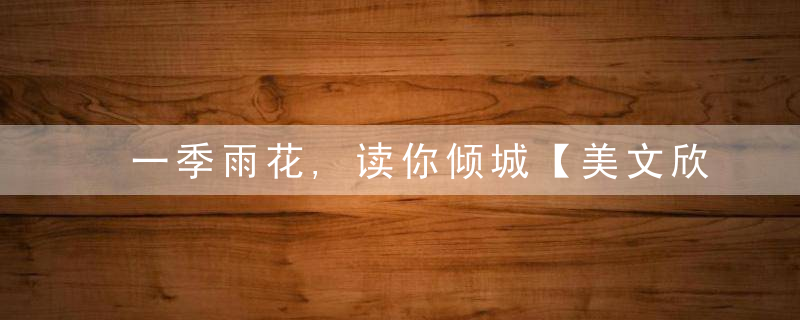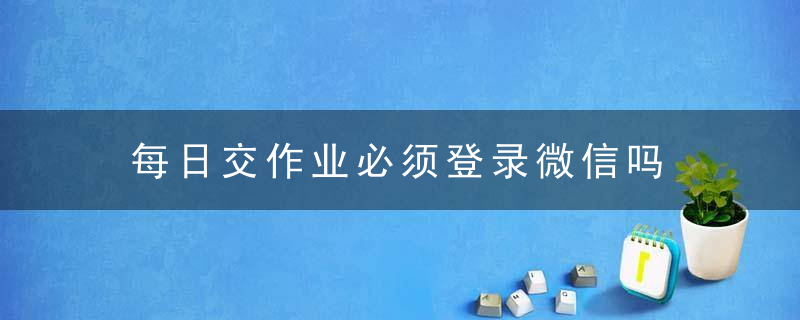有关大跃进运动的几个问题(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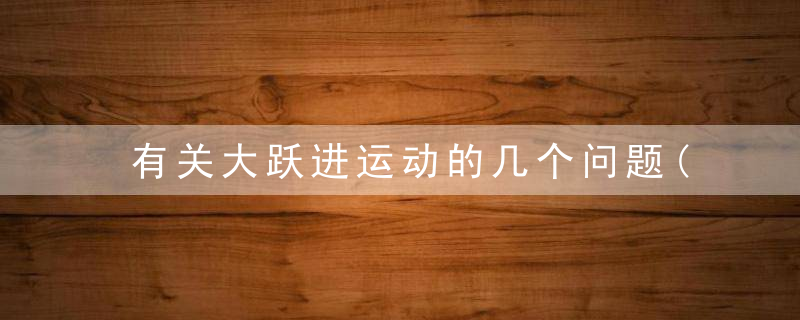
三、大跃进与毛泽东
大跃进运动是农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出现的,毛泽东同志反映了这一客观必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大跃进运动。但是作为一个生产建设的群众运动,研究其成因和得失时,本来可以抽象掉他个人的作用。但是,近些年来发表的专著或文章中,往往把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全部扣在毛泽东的头上,把毛泽东反对过的一些错误也说成是毛泽东的错误,严重地歪曲了事实。因此有必要专门作为一个问题来进行讨论。
有人说;“毛泽东好大喜功脱离了中国实际,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晚年》第125页)。有人写道:“毛特别强调政治挂帅,……总路线就完全将客观经济规律搁在一边。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很短时间里,大跃进运动进入高潮,狂飘聚起,云海翻腾,浮夸风、瞎指挥、高指标迅速泛滥。各地农村争相出现高产‘卫星’…”(李锐:《毛泽东的早年和晚
年》贵州人民出版社 第242—243页)。有人形象地描写道:“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在听取重工业部门汇报时,就主张钢产量每五年翻一番,今后就采取这种‘一番加一番的增长法’。”((交锋》第18页)看!在这些人的笔下,毛泽东成了一个主观主义者,完全不顾客观经济规律,喜好浮夸、高指标;是不顾实际情况主张“一番加一番的增长法”的人。那么实际情况真是这样的吗?
毛泽东在大跃进运动中的表现,充分证明他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家,而且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正是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学,运用在我国的经济建设的实践中。
在发动大跃进时,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畏气概,提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口号,号召广大劳动群众“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建国以来的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236页),从剥削阶级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在群众发动起来之后,他又反复强调“办事要留有余地”,“要压缩空气”,“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等等;在群众运动中出现浮夸风、高指标时,他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竭力说服干部、群众,提出要“尊重科学”,要“实事求是”,不要“务虚名得实祸”。但是他不给群众“泼冷水”,当运动出现失误时,他做自我批评,承认“第一仗打了败仗”(以上参看吴冷西:《忆》)。在国家面临严重经济困难时,他身体力行,与群众同甘共苦,“七个月没有吃一口肉”,“两腿浮肿”(《晚年》第126页),但并不惊慌失措,而是冷静地分析形势,改正错误,绕过暗礁,坚持正确航向,经过短短的三年,又把国民经济领上了正确的航道。这难道是主观主义者吗?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吗?当然不是。下面就通过事实作进一步的说明。
在发动大跃进运动时,毛泽东批评了“反冒进”。“南宁会议开始时,毛泽东一上来就讲……1956年‘反冒进’是错误的。这里说的‘反冒进’是指1956年6月到11月一些同志发现不少地方和部门的基本建设(包括农田水利建设)过大,造成财政赤字,原材料非常紧张,因而提出反对急躁冒进”,“认为,一个时侯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提出‘反冒进’的口号。‘反冒进’挫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是错误的方针。”(《忆》第48页)可见,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是为了给包括1955年冬至1956年春的农田水利建设在内的建设高潮撑腰,为了保护劳动群众的积极性而提出来的,
此后在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等一系列的会议上,他又反复讲要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对劳动人民的影响,号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批评贾桂式的‘奴才习惯’,赞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风格等等,充分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这些就不再叙述了。
当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他反复强调要“留有余地”,要“压缩空气”。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当毛泽东看到辽宁省计划要一年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本省自给)时,他说;“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又说:“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指基本改变面貌——引者注)。我就是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忆》第63页)虽然在估计发展速度的问题上,只有主客观符合不符合的问题,并没有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分歧,但是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留有余地的态度却鲜明地表现出来,宁肯被说成是机会主义也要坚持。
1958年4月,毛泽东对《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现在报纸宣传报导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订指标要留有余地”(《忆》第64页)。“他在武汉会议上讲,今后〈人民日报〉不要轻易宣传什么化了。有些地方稀稀拉拉地种了几颗树就算绿化了,这怎么行。……他提出宣传工作要务实:一要深入,二要细致,三要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晚年》第133页)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同志和社领导汇报说,亩产10万斤。他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的同志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往水稻上站。他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晚年》第138页)。在湖北省时,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试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信’。外国朋友问他,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晚年》第138~139页)
“从1958年11月初的郑州会议开始,到1959年7月中旬庐山会议前期,和接二连三地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左’倾错误”,“在一片‘胜利冲昏头脑’的气氛下,虽在赞赏‘六亿人民尽舜尧’那热气腾腾的局面,却最先冷静了下来。”(《回顾》第806、807页)
“在11月2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对热衷于搞翻番的同志说;你们说服我是可以的,你们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们得打通我才通。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准备作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连别人,将来算起帐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凡是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晚年》第140页)他说:“现在要减轻一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千9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千万人。...你搞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晚年》第 138~139页)尽管他反复讲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的道理,但是仍纠正不了高指标、浮夸风的盛行。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以他个人的名义,用党内通信的形式写信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其中说:“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包多少。……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文稿》第八册第237页)。“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成了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同上书)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无产阶级领袖的气概,实事求是的作风,本是历史上罕见的。但是,有些人却不深入研究毛泽东的所作所为,认真宣扬这种高尚的精神,反而把大跃进中出现的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等等,统统扣在毛泽东的头上。他们认为反正大跃进是毛泽东发动的,因此存在的问题也都是毛泽东造成的,什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什么‘毛泽东好大喜功,脱离了中国实际,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等等。这些说法,有的歪曲了事实,有的甚至颠倒了黑白。由于毛泽东坚持“气可鼓不可泄”的原则,主张对“热心搞大跃进的同志,应该是既批评又鼓励,不要挫伤他们的积极性”。通过循循善诱,组织学习等办法解决,不主张用反冒进办法,因此形成了一个渐进的转变过程。
直到庐山会议召开的前夕,“关于高指标,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指标订得高了,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农业究竟增产多少?对增产三成,表示怀疑,他说:‘假定有三成,全国也只有4800亿斤。今年根本不要理那个10500亿斤的指标,就是按去年的实际产量,今年只增产一成、二成、三成。听说包产的结果是6000亿斤,但是我看,我们过日子还是放在4800亿斤的基础上。本来是富日子,也照穷日子过,这样安排好。”对“工业,明年的指标切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按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回顾》第846页)。类似的事实还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为了反对浮夸,了解事实的本来面目,他不仅自己下去调查研究,而且派工作组去调查;组织干部学习等等。后来由于反对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扭转了斗争的方向,造成高指标、浮夸风继续蔓延,经济生活困难加重。直到1960年底,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错误才得到纠正。
毛泽东对大跃进中的失误也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和唯物主义者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的。他勇敢地面对现实,不讳疾忌医,不坚持错误,而是认真地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他首先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指出;“省委自己全面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回顾〉第901—902页)他率先身体力行,组织调查组深入农村调查,自己“带着急于了解农村真实情况的紧迫心情”,用近一个月的时间,离开北京到广州,沿途听取了七个省委和三个调查组组长的汇报,还同一些县委书记谈了话。正是他的这种实事求是态度和一抓到底的精神,使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基层核算单位,由公社到大队,再由大队放到生产队,使生产与分配统一于生产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几亿农民的生产情绪,成为我国农村摆脱连接三年的严重灾祸,迈向60年代中期新发展的转折点”((回顾)第900页)。
毛泽东同志对自己的错误也不隐讳。1959年在一次扩大会议上他说:“去年(指1958年——引者)我们至少有三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在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等等。吴冷西回忆说:“从去年(指1958年——引者)11月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到上海会议,曾多次作自我批评,但像这次会议上这样的自我批评还是第一次。”(《忆》135—136页)以后他多次作自我批评,承担责任。如谈到闯‘1070’这个祸时他说:“第一个负责任的是我”(《回顾》第701页)。1962年初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在会上不仅作了自我批评,而且带头承担所犯错误的责任,体现了党的领袖的广阔胸怀”。所以薄一波同志以亲历会议者的身份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所以它的意义和作用,在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人当中,永远不会忘怀,而且我相信会历时越久,影响越深”(《回顾》第1027、1029页)。
面对上述事实,能说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失误是由毛泽东的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造成的?能把大跃进说成是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事实证明,只有毛泽东这样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和辩证法大师,才敢于在广大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思想束缚时,号召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把广大劳动群众的主人翁自豪感、责任心调动起来,作大自然的主人,作社会的主人;当广大劳动群众发动起来,出现浮夸风、高指标等倾向时,又首先提出“压缩空气”,“留有余地”,抑制浮夸等错误;当运动出现重大失误时,敢于面对现实,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找出问题的症结,认真解决,并且坦率地作自我批评,承担责任。这里有主观对客观认识的失误,但决不是什么主观主义,更不是什么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是事实和历史的结论。经历过困难时期的人,都深深地感受到那几年的艰难处境。但是,还有一些更尖锐的问题可能是一般人所感受不深的,这就是苏修对我国的压力,苏修与美帝、印度等反动派联合对我国所施加的压力。以为首的除了面临国内的困难外,还要承担国际上的巨大压力。只有经过艰苦磨练的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才能在短短的几年内,扭转乾坤,重新走上了康庄大道。
从发动大跃进至今已四十年了。四十年在人类历史上不过是短暂的瞬间,但是,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显示出划时代的意义。让我们认真地总结大跃进运动的宝贵经验教训吧!


八年级历史下册.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