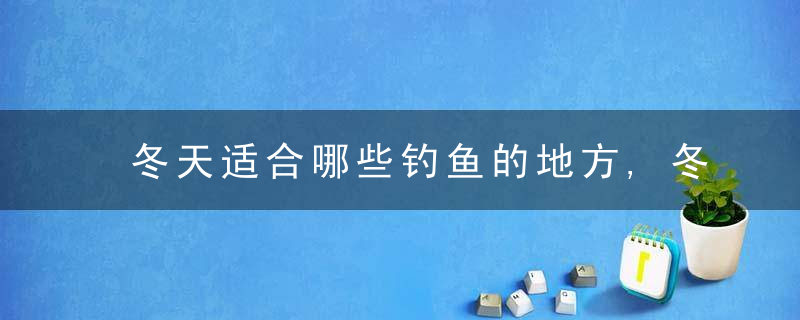中国央地关系向何处去

首先,最重要的是政治逻辑。政治逻辑主要是围绕着GDP主义发生的。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改变往日贫穷社会主义的局面,中国把经济发展作为的头等议程。不过,经济发展议程很快就演变成为唯GDP主义,以GDP论英雄。这对地方及其官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很长时间里,地方GDP的增长速度成为衡量地方官员政治业绩的最重要标准,即便不是唯一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演变成公司类型的,被学术界称之为“地方发展主义”。当经济成绩可以转化成为政治资本时,GDP数据的造假变得不可避免。
其次是利益逻辑。利益逻辑涉及作为组织的地方及其个体官员。地方如何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在典型的市场经济体中,因为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地方必须通过法治建设、税收政策和劳动条件等改善投资环境,来吸引资本和劳动者。但在中国,地方拥有更为直接的手段,包括直接搞经济项目和工程、向企业提供廉价土地等生产要素、与企业共同开发项目等。
对地方来说,这样做可以增加地方税收;对个体官员来说,这样做可以创造很多有利可图的机会,即腐败。人们说,中国是“市长经济”,而非“市场经济”,这并非没有道理。那么多年里,每一任新的地方领导到任,都必须通过这些手段来应付地方经济发展问题。每一任领导都会动用最大的资源来达到目的,而把问题(即责任)推给下一任领导。
其三,经济逻辑。经济逻辑最明显地体现在1994年分税制上。根据分税制的计划,根据各省1993年上交的税收为基数进行税收返回。结果,1993年各省上交的税收大增。道理很简单,各省为了多分一块国民经济的大饼。这次一些地方自爆GDP造假现象是一个刚好相反的案例,但逻辑是一模一样的。
地方背负巨额债务,但不管债务如何沉重,地方是不可倒闭的,所以最终总会有“人”来救,即最终的责任还是由来担负。主动暴露GDP造假就是要解决一个“谁来负责”的问题,减少地方自己的负担。再者,对新到任的领导来说,他们不用负很大的责任,因为这是前任历史积累起来的老问题。在十九大这个政治背景下,卸下历史包袱,轻装上阵,是新任地方领导的一个理性选择。
地方行为既然是地方关系的逻辑产物,要改变地方的行为,就须反思地方关系,并对此进行必要的变革。就其本质来说,当代地方关系所产生的种种问题,是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脱节的结果。
中国在理论上是单一制集权体制,但就其运作来说,是事实上的联邦体制。更具体地说,单一制只是体现在政治层面,在经济层面则是事实上的联邦体制。地方政治权力的基础源自,但在经济上则依赖地方。在政治上,地方仅仅是的执行机构,但在经济上,地方则具有很大的自治性。因为中国地方差异巨大,在社会经济方面,地方必须具有这种自治性,才能对地方进行有效的治理。
1994年分税制之前,和地方之间实行的是经济上的激进分权,结果出现了很多问题,主要是地方“藏富于地方”“藏富于民”,恶化,不仅影响在全国层面的统筹能力,也影响控制地方的政治能力。1994年分税制改革彻底改变了这种情况,从前是经济上依赖地方,改革之后则是地方依赖,即使是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也是如此。通过分税制改革,实现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集权。
不过,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后,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主要是在把经济权力集中起来后,并没有把责任也集中起来。地方失去了经济权力,但仍然要负责地方事务。地方的钱从哪里来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土地和房地产是地方收入的主要来源。
必须指出的是,土地和房地产问题后来发展到如此严峻的程度,也是1994年分税制的结果,因为分税制事实上把土地支配权给了地方。地方也各显神通,发展出包括地方融资平台在内的各种推动地方发展、增加收入的方法。地方的做法也是理性的,一方面是地方建设和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政绩的需要。
同样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地方的一些领域可以说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地方本身和地方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这些变化被大大地忽视了。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地方组织机构领域。的层级增多、城市的层级增多、地级市和计划单列市增多,而且每一级都是几套班子齐全。
这些变化在很多方面并没有法律依据,地级市就是一个例子。在改革开放前,地级市并非一级,而只是行署。这些变化导致了规模的急剧扩大,支出增加。有学者说,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规模并不算大。这里的问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福利制度,担负提供广泛社会服务的功能,规模的扩大是福利国家的必然产物。
但中国到目前为止,仅仅只是达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900美元的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远非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就是说,中国并没有提供广泛社会服务这方面的压力。除去社会服务方面的需求,中国规模无疑已经过大。在很多年里,规模不仅没有压缩,反而在扩张。只要“僧多粥少”的局面继续下去,地方肯定会成为很多问题的根源。
要解决地方问题,就必须重塑地方关系。这里至少有几个方面是可以考量的。
其一,通过确立国家统筹制度,重建现代国家。现代国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公民的出现,就是生活在国家之内的所有居民都能直接得到的服务。这是政治合法性的社会基础。不过,中国距离公民国家仍远,因为统筹级别低下,目前只实现了市一级的统筹,连省一级的统筹都还没实现。中国如果要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国家层面的统筹不可避免,否则国民很难确立其深层次的国家认同。
其二,压缩中间层。中国数千年来维持了、省、县三级的体制。日本直到今天仍然维持着从中国借鉴的秦朝体制。中国越来越多的层级不仅没有强化集权,反而在体制内部有效弱化集权,同时增加社会的负担。压缩中间层不仅有空间,而且有可能。例如,中国的城市不管大小一般都是“三级、四级管理”。
新加坡近600万人口只有一级,加上几个提供服务的市镇理事会,至多也是一级半。相比之下,珠海一个120多万人口的城市也实行“三级、四级管理”体制。无论是社会控制还是提供服务,新加坡都比中国有效,人们看不出为什么需要这么庞大的机制。
其三,除了纵向压缩中间层之外,横向的党政机构也可以压缩以减少支出。机构改革的其中一个目标便是精简机构,减少官员人数。这在过去数十年已经历多轮机构改革,该做的也已经做了。十九大提出“党政合署办公”的改革新思路,是很大的一个改革空间。
的机构改革从来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这次如果能够通过“党政合署办公”,把机构改革和机构改革结合起来,统筹考虑,机构改革就可以进一大步。在地方层面,无论机构还是机构,两者都面临同样的具体问题,为什么还需要两套行政班子?两者的整合可以减少机构和提高行政效率。
其四,进行新的税制改革,为地方寻找新的税源。讨论了多年的房地产税应当加快实施。在任何国家,房地产税是地方的重要税源,也是地方居民为地方做贡献的义务。除了既得利益的阻力之外,今天的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实施房地产税。
其五,大力进行国有企业改革,使得国企成为真正的企业,减少甚至断掉地方国企对的依赖。在一些领域,国企的确应当做大做强,例如在一些公共事业领域。但国企应当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改为通过税收体制和企业建立关系。市场化的国企改革不仅可以控制和减少国企债务,也可以控制和减少地方党政官员的腐败行为。
其六,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和地方关系方面建立政治责任制度。如上所说,改革开放以来,从到地方,在这个领域犯了不少错误。一些改革,例如设立计划单列市和地级市没有法律依据。这些错误都被忽视了。对和地方的领导层应至少做到一个任期进行一次大检查。随着监察制度的确立,经常被忽视的地方关系也应当引入被监察的领域。
数千年的中国政治历史经验指向了地方关系的重要性。大多数历史学家在论述中国兴衰时,都会把地方关系提到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一个稳定的地方关系,不仅决定了国家政治是否稳定,更决定了国家的兴衰。
* 本文作者郑永年教授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主席。
微信ID:zhengjiaopingl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