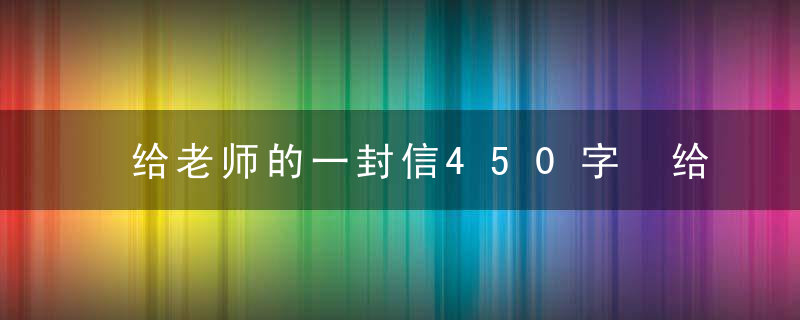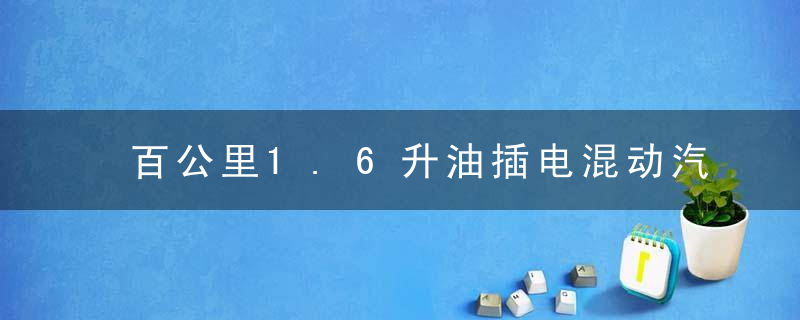在中国,有3.5亿诗人,他们的名字叫农民工

一颗花生的死亡报告
商品名:花生酱
配料:花生、麦芽糖、白砂糖、食用植物油、食用盐、食品添加剂(山梨酸钾)
产品标准号:QB/T1733.4
食用方法:启盖后直接食用
贮存方法:开盖前于常温避光通风干燥处储藏,开盖后请密盖冷藏
生产者:汕头市熊记食品有限公司
厂址:汕头市龙湖区新溪镇北中村远东工业园B2厂房
电话:0754-86203278 85769568
传真:0754-86203060
保质期:18个月 产地:广东 汕头
:stxiongji
生产日期:2013.08.10
起初看到这段文字
蛋蛋姐以为
这是哪个厂家的花生酱产品说明
你也这么以为是不是
但其实
这根本不是什么产品说明
而是一首诗
《一颗花生的死亡报告》
这是一颗花生
被压榨谋杀的故事
生产者就是谋杀人
厂址就是谋杀地点
生产日期就是死亡时间
这首诗的作者叫许立志
是一名90后
富士康流水线操作工
就是那个工作强度极大
许多工人跳楼自杀的富士康
而诗里的花生
就是他一个个被压榨
直至跳楼自杀的工友
至于他们
究竟被压榨的有多惨
在许立志的诗出现之前
极少有人知道
因为这个群体的任务是:
在社会底层
默默劳动
社会底层
意味着他们的工作又苦又累
默默则是说
他们根本就没有话语权
他们只能
像许立志诗里写的那样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他们把它叫做螺丝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
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
他们咽下生活的一切
困顿、艰难和挣扎
直到装满他们的整个胸膛
再也咽不下一丝一毫
便在绝望中
从高楼之上一跃而下
宛如一颗掉在地上的螺丝钉
不会惊起任何波澜
这群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叫农民工
他们有多少人呢
超过3.5个亿
邬霞曾经是个
大山里的留守儿童
农村里的教育条件自不必说
13岁的时候
初中二年级都没读完
她就去了深圳宝安
成了一个打工妹
在深圳这个
高楼大厦林立的城市里
她在城市一角
一个很老的居民小区里生活成家
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
他的爸爸患有严重抑郁症
曾经两次试图服毒自杀
可除了照顾父母
她还要养育两个年幼的孩子
生活过的有多艰难
我们可想而知
在一个服装厂里
邬霞成了一个熨衣妹
每天穿着宽松的工服
拿着烧红的熨斗
熨烫着一件件吊带裙
工厂里的热气
让邬霞大汗淋漓
可这些吊带裙
永远也不会穿在她身上
因为她根本就买不起
作为一个女人
又有谁不爱美呢
于是
她去地摊上买来
20元、25元一件的吊带裙
在每个夜深人静的晚上
坐在床上穿好
然后飞快地跳下床
跑到厕所里
对着那扇可以模糊看到自己的窗户
一次次的旋转
这是她对美的全部向往
即使生活
已经如此艰难
她却没有一丝抱怨
即便她只读到初中二年级
她却一直在坚持做一件事
——写诗
写给她的爸爸妈妈
写给她的家庭
写给这个世界
写给可能穿上她亲手
熨的吊带裙的陌生女孩
吊带裙
包装车间灯火通明
我手握电熨斗
集聚我所有的手温
我要先把吊带熨平
挂在你肩上才不会勒疼你
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
多么可爱的腰身
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
林荫道上
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
最后把裙裾展开
我要把每个皱褶的宽度熨得都相等
让你在湖边
或者在草坪上
等待风吹
你也可以奔跑
但,一定要让裙裾飘起来
带着弧度
像花儿一样
我要洗一件汗湿的厂服
我已把它折叠好
打了包装
吊带裙
它将被打包运出车间
走向某个市场
某个时尚的店面
等待惟一的你
陌生的姑娘 我爱你
但邬霞这样
还算是好的
最起码父母子女都在身边
贫寒小巢里
有他们一家人的幸福
同样作为农民工
陈年喜是一位爆破工人
他来自中国秦岭
南坡的一个小山村
中国最穷苦的地区之一
穷苦意味着什么呢
根本就生活不下去
在他儿子一岁半的时候
村里开始陆陆续续
有人出去打工
隔一段时间
就会捎点钱回来
有一天晚上
天快黑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捎来口信说
西秦岭南坡的金矿上
有一个架子车工的缺口
这又苦又累的活
在他眼里却如获至宝
陈年喜连夜收拾好行李
在天亮之前
便赶到了工地
这么多年一直生活在大山里的陈年喜
生平第一次见到了
比他生活的大山
更加闭塞的矿洞
陈年喜说:
如果不是亲历
你一辈子也想象不出矿洞的模样
它高不过一米七八
宽不过一米四五
而深度常达千米万米
内部布满了子洞
天井,斜井,空釆场
像一座巨大的谜宫
机缘巧合
陈年喜成了一名爆破工人
全世界最危险的工作之一
远离故乡和家人
他每天唯一面对的
就是雷管、炸药和死神
是真的会死
陈年喜妻子的弟弟
也曾是一名爆破工
在他妻弟28岁那年
一个漫天大雪的日子
他的妻子撑着怀孕的大肚子
送他出发去打工
可他这一走
就再也没有回来
只因为在炸药炸响之前
他跑错了方向
直接粉身碎骨
陈年喜亲手处理了他的后事
在矿山整整16年
经他手使用的炸药
甚至要用火车皮来计算
他也比比平常人
看到了更多的死亡
而他自己
即使侥幸没有失去生命
常年钻孔和爆破
已经使他的耳朵大半失聪
和他说话要用喊的
真的不仅仅因为矿山吵
而是真的听不见了
他的颈椎也严重错位
甚至还植入了3块金属
可是又能怎么办呢
就连母亲得了癌症
他都不能回家
2013年底
还在一个银矿的他
接到一个电话:
母亲查出食道癌,晚期
那一刻的陈年喜
恨不得立马飞奔到母亲身边
可是他知道他不能
因为母亲生病了
最需要的不是他
而是治病的钱
不留在矿上工作
哪里来的钱呢
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句话异常残忍
叫“男儿有泪不轻弹”
心里明明已经痛苦到极致
却不能哭
也不能跟任何人说
对于陈年喜来说
写诗便是他
输出情感的唯一通道
那天晚上
他写下这么一首诗:
炸裂志
早晨起来 头像炸裂一样疼
这是大机器的额外馈赠
不是钢铁的错
是神经老了 脆弱不堪
我不大敢看自己的生活
它坚硬 铉黑
有风镐的锐角
石头碰一碰 就会流血
我想告诉你
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
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
借此 把一生重新组合
我微小的亲人 远在商山脚下
他们有病 身体落满灰尘
我的中年裁下多少
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
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
他们是引信部分
就在昨夜 在他们床前
我岩石一样 轰地炸裂一地
“我的中年裁下多少
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
我不知道
他是怀着怎样一种心情
写下了这首诗
陈年喜在照顾常年卧床不起的父亲
即便他已经
经历过人间最深重的苦难
可对于千里之外的儿子
他没有办法见到
他也害怕他知道
只能默默给他写下这首诗
儿子
我们已经很久不见了
我昨夜抱你的梦
和露水一起
还挂在床头
你在离家二十里的中学
我在两千里外的荒山
你的母亲
一位十八而立的女人
被一些庄稼五花大绑在
风雨的田头
我们一家三口
多像三条桌腿
支撑起一张叫家的桌子
儿子 这也是我们万里河山目下
大体的结构
儿子
我们被三条真实的鞭子赶着
爸爸累了
一步只走三寸
三寸就是一年
儿子 用你那精确无误的数学算算
爸爸还能够走多远
你说母亲是你的牡丹
为了春天
这支牡丹已经提早开了经年
如今叶落香黯
谁能挡住步步四扰的秋天
儿子
其实你的母亲就是一株玉米
生以苞米又还以苞米
带走的仅仅是一根
空空的桔杆
儿子
你清澈的眼波
看穿文字和数字
看穿金刚变形的伎俩
但还看不见那些人间的实景
我想让你绕过书本看看人间
又怕你真的看清
但其实
抛开这些苦难
像所有正常的男人一样
他也爱他如花似玉的妻子
可这种浪漫
不属于苦难的生活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写下这些诗行
爱人
爱人,当你接过我流浪的双手
我猝然感到自己比鸿毛还轻
那双手里有我全部的黄金啊
爱人,十月庄重的天空下
我比死亡更静 爱人,
我用了二十七年的漂泊来换取 你的一握
我点燃五千首诗歌照亮你深深的居所
面对我纯金的爱,你要小心呀
你要把我牢牢牵在手心
爱人,我愿象一直驯良的小狗
为你役使,为你占有
或者象水,一生一世在你的骨骼中行走
爱人啊,如果能拥有你
我愿意没有自己 是谁把我们一起带到今天
让我们成为彼此的刀子和灯盏
我水银一样纯净的爱人
今夜,我马放南山,绕开死亡
在白雪之上,为你写下绝世的诗行
在无数个
下完矿井的夜晚
在那间破旧的
连把椅子都没有的房间里
他就那么坐在床沿上
佝偻着身子
趴在那张用杂物架起来的木板上
在昏黄的灯光下
思念着妻子儿子
独自咀嚼着人间苦难
再把它们雕琢成
满含血与泪爱与恨的人间世行
和陈年喜一样
老井也是一名下井工人
不过
他工作的地方是煤矿
用老井的话说
他们的工作:
不见天日
每天乘着升降机
一路降到600多米
甚至上千米的地底深处
甚至比全世界最高的楼还要高
单是这个过程
都要持续好久
他们看着井口的光
一点点缩小缩小再缩小
从一个大圆
凝成一个光斑
直到完全是一片黑暗
外界的喧哗
从他们的耳边
一点点缩小
直到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井下有多暗呢
大白天的
唯一的光
就是他们头上的矿灯
井下有多静呢
老井每次走路的时候
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自己
老井在矿井下工作
这是我们在走夜路时
才会有的感觉
在这样的黑暗和死寂中
他们一工作便是一天
可老井却希望
井下永远都是
这样的黑暗和死寂
因为当有声响的时候
就意味着出事了
最常发生的事情是
瓦斯爆炸
有一次爆炸时
老井的27位工友遇难了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大家慌忙抢救
却只抢救出6具遗体
可外界源源不断的氧气进去
爆炸随时有可能再次发生
无奈只能把洞口彻底封死
那没来得及抢救的21具遗体
永远留在了地底深处
和无边的黑暗融为一体
即便那是
他朝昔相处的工友
是27条活生生的生命
老井也无可奈何
只能用他的笔写下诗行
在辽阔的地心深处
有一百多个采摘大地内脏的人
不幸地承受了大地复仇时
释放出的万丈怒火
已炼成焦炭
余下惊悸、爱恨,还有……
若干年后
正将煤攉入炉膛内的那个人
在呆呆发愣时独对的
一堆累累白骨……
老井称他和他的兄弟们
是采摘大地心脏的人
他称那次瓦斯爆炸是大地的复仇
可享受成果的
明明不是他们
却为何他们要承受这复仇
他跪在那个
早已成为废墟的洞口
想念当年的兄弟们
他为那永远埋在地底深处的
21条生命鸣不平
地心太黑,太封闭,兄弟们
不要在此悄然低泣了
把你们悲戚、潮湿的灵魂
这条条闷热、漆黑的闪电
都伏到我的肩上吧
把你们所有的怀念、悲愤、渴望
都装入我的体内吧
他说:
我愿做一口活的棺材
一座移动的坟墓
殓载上你们所有的残梦
一直往上走 ,一直走到地表
那个阳光暴涨的地方,再把它们释放出来
先晒去悲痛的水分
然后让它们赶紧去追赶
那缕缕飘荡了两年仍未
斜入地心的,清明寒烟
不管有多少不甘
不管内心有多少不平
在很长的时间里
老井都没有办法
为他的兄弟们讨回公道
一如那无数
在深山老林的矿难中
被埋入地底的生灵
因为
就连活着的人们的苦难
大家都看不到
又怎么会想到死人呢
一如21岁就离开四川老家
在东莞流水线工作的郑小琼
除了每天机械的流水线
她就只能默默
记下自己的生活
你们不知道
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
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
身体签给了,合同……
一如从大凉山深处
到浙江嘉兴打工的吉克阿优
从那一出来
许多年他都没回去
所有的思念
也只能化作无声的诗行
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
从大凉山到嘉兴,我在羽绒服厂填着鸭毛
我被唤作“鸭头”时遗失了那部《指路经》
好些年了,村庄在我的离去中老去
此刻它用一条小兴场的泥路
反对我的新鞋,欢迎我的热泪
好些年了,我的宇宙依然是老虎的形状
一如引用古老《梅葛》的毕摩所说
颤抖的村寨跳进我的眼瞳,撕咬我
好些年了,儿时的伙伴已建起小楼
我也回到了大地的中心,我的土掌房
三块锅庄石,三根顶梁柱
父亲笑呵呵在火塘边抽兰花烟
像温暖的经书,让我念诵不已
他的拐杖又长高了不少
而母亲笑呵呵在我心里
今夜我要睡在她的旧床上
今夜我必须做梦
他们在城市的边边角角
在矿山深处
默默苟活着
真真正正践行着
“生如蝼蚁”
在许多年后的一天
一个转机到来了
因为诗歌
没错
有心的人也许会发现
他们的共同点是写诗
有一天
吴晓波在一本《读书》杂志上
看到一首写工人诗歌的文章
一度以为诗歌在21世纪
已经消失的他
第一次发现
居然还有这么好的诗
存在于各个角落里
他才终于再次注意到
遍布城市各处
却一度被人们忽略的
农民工群体
他的第一个念头是
为他们出一本诗集
第二个念头是
为他们拍一部纪录片
他们开始寻找
散落在各处的工人诗人
工人被他们一个个找到
当找到许立志的时候
他拒绝了
因为他早已不再写诗
在曾经的很多年里
这位富士康流水线工人
在微博里一字一句写下的孤独
不会有人关心
他的才华
也不会有人关注
几个月后
他选择了纵身一跃
告别这个给他带来巨大痛苦
却没有办法解脱的世界
他的最后一条微博
停留在2014年10月1日
第65个国庆节
内容是“新的一天”
这一年他24岁
只是新的一天
再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他的最后一首诗
这么写道:
我想再看一眼大海
目睹我半生的泪水有多汪洋
我想再爬一爬高高的山头
试着把丢失的灵魂喊回来
我想在草原上躺着
翻阅妈妈给我的《圣经》
我还想摸一摸天空
碰一碰那抹轻轻的蓝
可是这些我都办不到了
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所有听说过我的人们啊
不必为我的离开感到惊讶
更不必叹息,或者悲伤
我来时很好,去时,也很好
他的家人
把他的骨灰撒向了大海
也许从那一刻起
他真正得到了解脱
他再也不是底层
他再没有痛苦
在这个世界上
他和任何人
再没有阶层的差距等级的分别
历时17个月
79位工人诗人的273首诗
终于被结集出版
书名是《我的诗篇》
许立志的诗
也得以众筹出版
书名是他微博的最后四个字
《新的一天》
而《我的诗篇》纪录片
也终于拍摄完成
在1349位素昧平生的
众筹观影发起人的努力下
在205座城市
完成了1000场点映
成为了一个世界电影史的纪录
这些发起人小的只有10岁
年龄大的已经77岁
小学生们参与众筹观影
向来被我们忽略的农民工
在他们的奔走呼号下
在“写诗”这个和他们极不搭调的标签
的带领下
终于进入大家的视野
人们这才注意到
那些吊在高墙之上
建设高楼大厦的农民工
那些在大热天里
默默清理污水管道的农民工
那些在矿山深处
一脸乌黑的农民工
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
一座座高楼大厦才拔地而起
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
我们的城市才变得干净美丽
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
才有了超市里供我们所需的琳琅满目
这是一个农民工
普遍被嫌弃和忽略的时代
可这个时代
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绝对不能没有农民工
如果不是那些诗歌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会注意到农民工
这个3.5亿
占我们人口四分之一的庞大群体
他们在数十年里
默默地离开他们的故土
和父母妻儿
在异乡谨小慎微地建设着
我们所生活的城市
成为3.5亿城市里的隐形人
可是
在这个世界上
人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即使有
我们也该知道
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
酷玩实验室整理编辑。
首发于微信公众号:酷玩实验室(ID:coollabs)
参考资料:
纪录片《我的诗篇》陈年喜 纽约大学演讲 《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
许立志、邬霞、陈年喜、老井、郑小琼、吉克阿优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