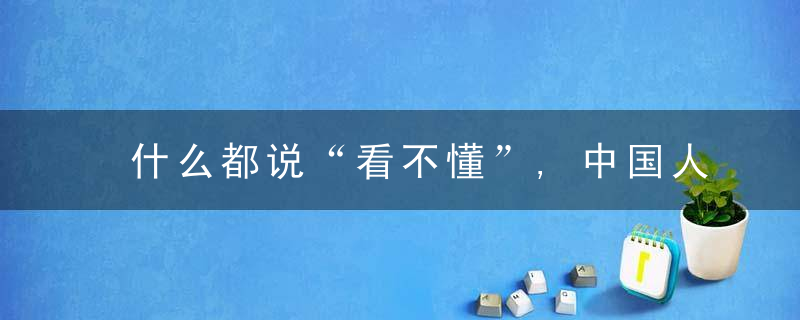有“病”,才有个性——明朝文人的另类活法

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穿
唐寅的风流与疯癫可谓直开晚明文人“颠狂”的先声
《唐伯虎点秋香》剧照
◆ ◆ ◆ ◆
自古以来,儒学所推崇的圣人人格与现实中文人的人格,完全是两回事。文人人格通常受到批评。如《颜氏家训·文章》中说:“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唐朝书法家李邕更说过:“不颠不狂,其名不张。”在明初,像宋濂与方孝孺这些儒家学者,就拒绝被人称之为文人。但到了晚明,因为程、朱理学逐渐失去崇高地位,个性之风崛起,文人追求独特个性的兴趣,远远大于对规范性完美人格的兴趣。因此,晚明文人更为欣赏的恰是有特点的文人人格,而不是完美的圣人人格。
今日与大家分享吴承学教授《晚明小品研究》的最新修订版,内容摘自“闲适与放诞”一节。
◆ ◆ ◆ ◆
晚明文人的精神,受到当时思想界风气的浸染。他们的文化品格,多少都有心学的影子。王阳明心学,崛起于明中叶,盛行于晚明,对文人的心态产生了极大影响。阳明心学取代程、朱理学的地位,既有其积极意义,也有其消极因素。阳明心学引发人们对传统与权威的怀疑,弘扬人的主观意志。在文学创作上,阳明心学对晚明文学弘扬个性、不拘传统的创作思潮,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程、朱理学本身具有两重性:作为文化理想的理学和被政治异化而作为官方哲学的理学。程、朱理学的初衷,是要弘扬一种大同、和谐、亲情、友情的文化理想,弘扬人生理想、精神价值和道德境界的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因此,它注重人性的崇高和理性意志,追求理性升华。平心而论,程、朱理学讲求理想和理性意志,以理性主宰和支配感性,这些对培养注重气节品德、自强不息的美德,是有益处的。然而,它一旦成为官方哲学,成为统治工具,也就逐渐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绳索。当这种哲学被人们所推翻和否定,程、朱理学对人们思想意志的束缚消失了,而其原先合理与积极的部分,也可能被抛弃。晚明心学代替了理学,理学作为官方哲学的衰亡,不但对于官方是一种巨大的威胁,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整个社会秩序和社会心态。传统价值观的崩塌,引起人们强烈的幻灭感,人们否定了程、朱理学的理性意志,并竭力消除了它的约束,必然带来感性和生理自然欲望方面的膨胀。于是,一方面,人的理性力量丧失;另一方面,耽于声色、追求安逸和享乐的风气盛行。这正如张瀚在《松窗梦语》卷七中所指出的:
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
晚明文人和魏晋名士一样,都追求个性自由,蔑视礼法,放诞任真。但魏晋名士的文化品格,带有世袭门阀制度下的贵族气息。他们言谈玄远虚无,清高绝尘,眼不看俗物俗客,口不言阿堵物。晚明文人的文化品格较为复杂,他们总体上是放诞风流,充分地肯定人的生活欲望,“好货好色”:既追求精神超越的愉悦,也追求世俗的物质享受;既狂狷、潇洒、超逸、旷达,又善于“玩味”生活;不但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这些传统文人的把式,连花卉果木、禽鱼虫兽、器物珍玩、饮食起居等寻常的生活事物,皆被导入艺术的殿堂,以之表现雅人高士的澄怀涤虑、与物熙和的风流格调。
晚明小品最大限度地展示了晚明文人理想的生活方式与风雅修养的具体标准。这种生活,既世俗,又雅致,是生活情趣与艺术诗情的结合,显示了一种享受人生的文化气质和处世态度。闲适,其实也是一种享受。晚明小品比较集中的主题,便是表现文人闲适的生活理想。例如以下文字:
竹楼数间,负山临水,疏松修竹,诘屈委蛇,怪石落落,不拘位置,藏书万卷其中,长几软榻,一香一茗,同心良友,闲日过从,坐卧谈笑,随意所适,不营衣食,不问米盐,不叙寒暄,不言朝市,丘壑涯分,于斯极矣。
凄风苦雨之夜,拥寒灯读书,时闻纸窗外芭蕉淅沥作声,亦殊有致。
洁一室,横榻陈几其中,炉香茗瓯,萧然不杂他物。但独坐凝想,自然有清灵之气,来集我身。清灵之气集,则世界恶浊之气,亦从此中渐渐消去。
这种生活情趣,相当具有文人色彩。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平民百姓,也不同于商贾富豪、仕宦贵人,在平静幽深的环境中,追求一种富于艺术意味的恬淡、冲远、淡泊、自然的生活情趣。这种情调的小品,在晚明文坛,可谓俯拾皆是。它们除了反映传统道德和审美理想对文人的影响,更多地折射出当时庄、禅之风对文人心态的影响。
明·仇英《临宋人画轴》
但是,闲适只是晚明文人生活理想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放纵的、侈靡的享乐。这种兼闲适与放纵于一身的生活态度,都明明白白地反映到晚明小品之中。袁宏道在《龚惟长先生》一信中,谓人生有五种“真乐”,理想的生活要“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安,口极世间之谭”,非把人世间物质和精神方面种种“快活”享受尽了不可。他的“真乐”,还推崇“恬不知耻”的生活方式。张岱《自为墓志铭》,说他少年时“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从这真率得肆无忌惮的表白来看,说他们是一帮纵情声色、放浪形骸的“大玩家”,恐怕正是他们乐于接受的雅号。明代中叶以后,文人奢靡淫纵的社会风气日盛。从朝廷以至民间,莫不如此。纵情声色,成为当时文人的通病。他们一方面摆脱了伦理纲常的束缚,另一方面又坠入情波欲海之中而难以自拔。其中有一些文人确是借醇酒、妇人来发泄精神上的苦闷,但多数只不过是一种放浪不羁的生活爱好。他们往往以高雅的理由和理论来为自己解脱,以堂皇的借口巧饰渔色纵欲的放荡行径。袁宏道在《叙陈正甫会心集》一文中,批评有些人“或为酒肉,或为声伎,率心而行,无所忌惮,自以为绝望于世,故举世非笑之不顾也”。其实,他们所批评的,也正是自己在现实中的行径。比如,袁宏道就曾说:“弟世情觉冷,生平浓习,无过粉黛,亦稍轻减。”又说:“弟往时亦有青娥之癖,近年以来,稍稍勘破此机。”袁宏道所言,虽是带有忏悔心情来说的,但也道出他以往的生活情趣。事实上,在晚明整个社会,可谓上恬下嬉,竞尚浮华。文人流连风月,沉湎花柳,纵情声色。要完全归之于个性解放,似评价过高。
从晚明小品中,也可以看出晚明文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在晚明许多文人笔下,人生的价值就在于追求物质和精神的享乐。传统知识分子那种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功业和道德理想的追求,已经不怎么吸引人了,而许多人都把满足个人生活欲望和精神需求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在那个时代,人们所追求和欣赏的是如何及时行乐,传统安贫乐道的清苦生活方式并不为人们所欣赏。从晚明大量的清言、清赏一类小品来看,当时文人对于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享乐的讲究十分艺术化。不但生命的每个阶段、每个季节、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有一套周密和系统的享乐计划。这个时代的文学,充满着高雅情致的精神追求与感官欲念的物质追求相结合的享乐意识。在晚明小品文中,反映出当时文人相当矛盾的倾向。一方面,他们鼓吹清心去欲,绝尘去俗,追求长生。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追求物质享受,追求犬马声色之乐。可以说,纵情耽乐和清心寡欲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矛盾统一地并存于晚明文人的生活和创作中。
晚明时期,文人对于人格方面的追求,也是相当有时代特点的。古代儒家传统的理想人格以修身为本,文人应该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养,成为能够安贫乐道、自强不息的真、善、美兼备的正人君子。但是,晚明一些文人既无兼济天下之志,亦未必有独善其身之意。他们最为欣赏的,并不是这种道德完善的君子人格,而是狂狷癖病的文人才子人格。晚明文人并不追求人格的完美,在他们看来,有弱点、有缺陷的个性,才是真正的优点。张大复有《病》一文说:“木之有瘿,石之有鹆眼,皆病也。然是二物者,卒以此见贵于世。非世人之贵病也,病则奇,奇则至,至则传。”“小病则小佳,大病则大佳”,“天下之病者少,而不病者多,多者吾不能与为友,将从其少者观之”。有“病”,才有个性,有情趣,有锋芒,有不同于世俗之处。这是晚明文人普遍的看法。袁宏道在《与潘景升》中说:“弟谓世人但有殊癖,终身不易,便是名士。如和靖之梅,元章之石,使有一物易其所好,便不成家。纵使易之,亦未必有补于品格也。”林和靖对于梅,米芾对于石,都有一种痴迷执着的爱恋之情,故成名士。因有“殊癖”,才有个性,有理想,有追求,有忘于一切的执着之情。当然,袁宏道所说的这种“癖”,指的是对于高雅事物的执着。但也有不少人,实际上倒多是对于声色的“癖”。同样,张岱也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无癖”“无疵”之人,不可作为朋友交往,因为他们缺少“深情”“真气”。晚明人推崇的是突出而又真实的个性,“癖”与“疵”,其实就是那种不受世俗影响,没有世故之态的人格。人有“癖”有“疵”,才有执着的深情和真实的个性。
蚌病成珠,文人之“病”,则成为一种不同世俗的情致。晚明程羽文在《清闲供》的“刺约六”中,详细论及文人的六种“病”,以及这些“病”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这六种“病”是癖、狂、懒、痴、拙、傲:
一曰癖。典衣沽酒,破产营书。吟发生歧,呕心出血。神仙烟火,不斤斤鹤子梅妻;泉石膏肓,亦颇颇竹君石丈。病可原也。
二曰狂。道旁荷锸,市上悬壶,乌帽泥涂,黄金粪壤,笔落而风雨惊,啸长而天地窄。病可原也。
三曰懒。蓬头对客,跣足为宾。坐四座而无言,睡三竿而未起。行或曳杖,居必闭门。病可原也。
四曰痴。春去诗惜,秋来赋悲。闻解佩而踟踌,听堕钗而惝恍。粉残脂剩,尽招青冢之魂;色艳香娇,愿结蓝桥之眷。病可原也。
五曰拙。学拙妖娆,才工软款。志惟古对,意不俗谐。饥煮字而难糜,田耕砚而无稼。萤身脱腐,醯气犹酸。病可原也。
六曰傲。高悬孺子半榻,独卧元龙一楼。鬓虽垂青,眼多泛白。偏持腰骨相抗,不为面皮作缘。病可原也。
他们不理生计,不修边幅,傲对权贵,蔑视众生,多愁善感,行为古怪。这些“病”,正是文人名士的个性和习气。他们的感情与脾气,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处世方法,都与俗人俗事不同。不同于世人,故称“病”。文人的生活情趣,都是由这种种“病”所生发的。有了病,才有诗意,才有意趣,才有不同寻常之处。程羽文写道,“病可原也”,岂止“可原”,更是可赞可叹。这里所写,也正是对于种种“病”的赞歌。晚明文人的风习,固然很少“乡愿”之风,但大多是玩世不恭、放达跌宕的。
袁宏道赠给张幼于一首诗,诗中有“誉起为颠狂”之语。大概张幼于对“颠狂”二字的评价不满,袁宏道给他写了一信,信中说,“颠狂”两个字,是一种很高的赞词:“夫‘颠狂’二字,岂可轻易奉承人者。”他引经据典,说明“颠”与“狂”的价值:“狂为仲丘所思,狂无论矣。若颠在古人中,亦不易得,而求之释,有普化焉……求之儒,有米颠焉。”实际上,孔子并不推崇“狂”,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狷”都违背了中庸之道,偏于一面,过于偏激。中郎借用孔子大旗来高度评价“颠狂”的品格,接着说:“不肖恨幼于不颠狂耳,若实颠狂,将北面而事之,岂直与幼于为友哉?”可见,“颠狂”不但是晚明文人喜欢的人品,也是他们推崇的理想。
自古以来,儒学所推崇的圣人人格与现实中文人的人格,完全是两回事。文人人格通常受到批评。如曹丕《与吴质书》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颜氏家训·文章》中说:“自古文人多陷轻薄。”都是对文人才士人格的批评。自从宋代以后,尤其是程、朱理学之后,许多文人以儒学的圣人人格作为人生修养所追求的目标,力求获得尽善尽美的人格。在明初,像宋濂与方孝孺这些儒家学者,就拒绝被人称之为文人。但到了晚明,因为程、朱理学逐渐失去崇高地位,个性之风崛起,文人追求独特个性的兴趣,远远大于对规范性完美人格的兴趣。因此,晚明文人更为欣赏的恰是有特点的文人人格,而不是完美的圣人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