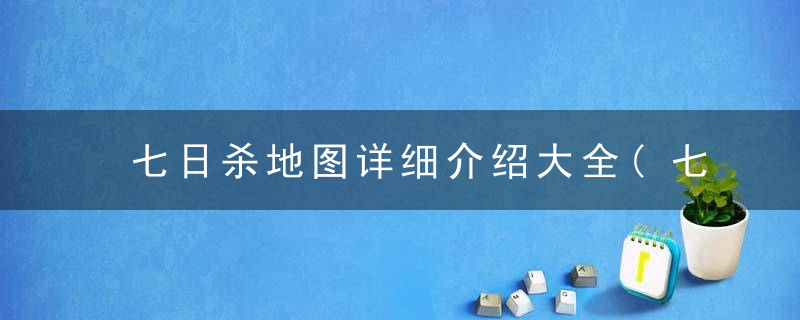那些人流手术室门口的男人们|真实故事

文:罗蓓蓓
离2018年情人节不远的深冬,北京某人流医院门口,零零星星地有人进进出出。他们大多成双结对,各自保持着与别人的距离。
医院的落地窗拉着大幅藕粉色窗帘,里面的光线沉而黯淡。几个男人带了厚厚的墨镜,拎着女伴的包跟在她们身后,由导医领着走来走去。一对学生模样的男女见状,就在旋转门边停了下来。男生摸来摸去,从书包里找到一个带空气阀的防霾口罩,给短发女生戴上。他小声说:
「怪我没有考虑周全。只有一个这种口罩,就你戴吧。我怎样都行。」
手术室门口的家属区里,几个男人在默默等候。有人在玩手机,有人半张着嘴发呆,有人靠在墙壁的阴影里一动不动,仿佛时间在此处难以流通,堵在他们身体的某处,让他们疲于动弹。
谁也不在意,谁是谁的先生,谁的男朋友,谁的情人,谁的包养者,谁的友情陪伴前来的Gay密友。
站在阴影里的那个男人,突然开始浑身上下里里外外地翻自己的口袋。羽绒服,衬衫,牛仔裤的口袋,都一一翻遍了。可是,他仿佛一无所获,陷在一种闭合的沉思里,以至于最终屁股后面的口袋还翻在外面,像一条哑口无言的舌头。
「手术中」的灯光指示牌还亮着,他却站起身来,大步朝医院门口走去,逃似的。
二十分钟以前,他的女伴进手术室的时候,他还吻了她。想起她马上就要遭的罪,想象着血与刀,他觉得这辈子一定不能负她。他吻她吻得嘴唇发烫。现在,他的嘴唇已经凉了。在这二十几分钟的时间里,他的头脑经历了风暴和雪,把他吹得远远的,头也不回。
「被下套了。」
这个念头不知是什么时候钻出来的。它一钻出来,就把他吓了一跳。他不愿相信,却又忍不住自我说服,最后不得不信。他在脑子里追踪细节,求证,推翻自己,再追踪,再求证…最后他认输了。他不想再推翻自己。他顺势认定:
「被下套了。被下套了。肯定是被下套了。」
这种想法,在此刻让他如释重负,让他可以逃得头也不回。
大概两个月前,他在去天津出差的动车上,认识了邻座的天津女孩。他承认自己一开始有些动机不纯地与她搭讪,等也等不及地只想赶紧下车,顺理成章地在人流中牵起她的手,摸她的头发,搂她的肩,进而至少要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天里跟她发生亲密关系。
可20几分钟的聊天,让他打消了这种想法。这个女孩是与以往那些都不同的。她皙白的皮肤凑近了看,竟然没有抹过BB霜,这让他相当惊异。
女孩把她每天唱给流浪猫狗听的歌也唱给他听,嗓音温柔。他觉得她不是那种可以随意轻薄之后就互删信息走人的女孩。他甚至在某一刻希望这是一趟没有终点的列车。
一路上,他铆足了劲发挥北京人耍贫嘴抖机灵的特长,哄得女孩笑颜如花。
下了车,他们去坐「天津之眼」摩天轮,看傍晚的万千灯火飘在空中和水中。那种温度与甜度交融的幻觉,一直延续到女孩的床上。
之后的周末哪怕只能抽出半天空闲,他也会踏上往返于北京与天津的快车。
两个月前的事现在回想起来恍如昨日。但今天,她就已经躺在手术台上了。他站在白墙的阴影里胡思乱想,问题抑制不住地一个接一个加速席卷而来。没有任何逻辑表明,这些问题可能解答他心里的任何怀疑,但他脑子里依然掀起了一场没有温度的暴风雪。
「医生说怀孕日期是42天,也就是一个半月以前。两个人总共认识才两个月。我也不是每周都会去天津。42天的那周我去了吗?车票呢?车票上哪儿了?身上没有。在家里吗?还在吗?有没有扔掉?洗衣服洗坏掉?还能找到吗?现在回去看看?几点能回来?…」
「医学可以精确到天吗?医生说42天就是42天?她还说现在医学发达了,人流可以无限制地做呢!活见鬼!无限制是几次?人的一生都是有限的,人流手术怎么无限?这医生道德有问题。她还说从她办公室里走出去的那个女生是小三,马上就要做第四次手术了,前三次都是她做的。她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拿小三和多少次手术这种隐私去劝别人堕,生怕她们想留下肚里的孩子似的!这个医生真没道德。人品绝对有问题。她说的42天肯定也是蒙事儿的。」
「那盒冈本101是我买的,从她家小区门口的小店买的。发票还在不在?一盒10只,到现在应该还剩几只?要数清楚,还得回趟天津。就在床头柜里。」
「上次回天津,她阳台上挂了那么多条洗干净的内裤,晾衣架的夹子都夹满了。她那么懒那么爱撒娇的人,都是我去给她收拾卫生洗内衣内裤。她怎么突然自己洗了那么多?这是跟谁撒娇了?她为什么用脏那么多内裤?好像还全是蕾丝的。她又不喜欢蕾丝,从来没见她穿过蕾丝。这么多蕾丝内裤都是哪儿来的?」
「本来只想一夜情,后来真的爱上,不知不觉陷进去,越陷越深。她是不是才是那个猎人?」
「前台问她要身份证登记的时候她说没带。谁不知道上医院得带身份证?她是故意不带防着不给前台看的,还是防着不给我看的?她的身份证我还从来没见过呢!上面的信息,跟我了解的会不会有差异?」
「被下套了?背锅?还是遇到了托儿?咨询的时候说2000就能搞定。现在多开出这么多检查单,补交了3次费用,多花4、5000。她会不会是托儿?医院给她返点?这家医院是她选的。人流医院遍地开花,为什么偏偏是这家?她说取款机在最靠里的一步电梯旁边,她怎么这么轻车熟路?之前堕过很多次?还是根本就是医院的托儿?」
他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想出这些问题来的。它们没有逻辑,没有答案,却挤在他的头脑里,让他头痛欲裂。他愤怒起来,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一个受害者,如同邻人盗斧中那个怎么看邻居怎么像小偷的人,直至终有一日在自家院里找到了斧子。这个怀疑自己被下套的男人,也许永远也找不到一把可以终结疑问的「斧子」。但他却在这些越滑越远的问题上越陷越深,仿佛已经出离了那个曾经获得过爱欲和情感而奔赴在路上的身体。
也许,这种愤怒是潜意识里自我选择的一种结果。愉悦是短暂的,却让人不得不面对一整场疑点重重的生活。不如愤怒!
有了愤怒,就有了理由,头也不回地走。
那个躺在手术台上的女人,或许在某一刻曾想象过,走出来以后两个人的戏将如何继续。但他一个人,已经独自在脑子里把戏演完了。
愤怒的男人,不止他一个。除了愤怒,那个隐在这群沉默不语的影子里半张着嘴发呆的男人,更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如果不是认识了手术台上的女人,他以为与他结束了8年长跑走入婚姻的妻子,将与他把下半辈子消磨下去。结婚以前,两人各自向亲友借齐头款,一起贷款买了房,过上了负担重重的房奴生活。他们早出晚归,常常连一起吃饭的时间也没有。早晚餐都在公交车上匆匆对付过了。回家累得不想说话,就只剩看手机和倒头大睡。
男人渐渐玩起了手机游戏。从睡前消遣,到每晚只留3小时的睡眠时间。他甚至在游戏里结了婚。8个月以后的一天,那个在游戏中成为他妻子的女孩问:
「我们可以见面吗?」
他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但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反问:
「你在哪个城市?」
「郑州。」
他买好票,女孩用自己的名字为他订了酒店。
从酒店前台拿到钥匙,房号829,正是他的生日。打开门,里面已经摆好了花、零食和卡片。
那天他送女孩回家。隔着一楼的铁门,他们向相反的方向告别了很多次,又回过头来走向彼此,再告别,再回来。最后他们互相凝视,默默地在北方的冬夜站到临晨4点。
他对于沉默不语的状态早已习以为常,但这次的沉默却是完全不同的。这是此时无声无以诉说的那种沉默。此刻,他觉得自己只有一个妻子,而这个妻子,就是眼前这一个。他忘记了与她无关的一切生活。
回到北京,他很快离了婚。因为愧疚,他把房产全部留给前妻,净身出户。他企图走出游戏,开始新的现实生活;他渴望把游戏中的妻子,变成现实的妻子。
可现实,毕竟不是戏。
作为一个失去了房产几乎一无所有的男人,他败给了郑州当地的富商。女孩嫁给一个比自己大二十几岁的男人,理由是「父亲做生意亏了钱,只有他,可以帮忙周转减轻负担。」
至此,他已没有什么可以失去。
心灰意冷之时,她说「我只爱你。」他信了,不然呢?他甚至更信了,以作为对自己的宽慰和补偿。只要她说「我想见你」,他就马上出发。这种关系维系了几年,直到她生下孩子。
他觉得这种日子彻底没了尽头。他的情感生活,仿佛将随着她忙忙碌碌相夫教子的节奏滚动下去。但自己真的可以这样,东一天西一天,没有尽头没有永远地活吗?他觉得够了。
他想忘了她,想摆脱这种生活。他尝试与其它女孩约会,并逐渐以工作繁忙为由,减少与她见面的机会。有一天她打来电话说「我怀孕了。」他觉得那就是他的孩子。虽然他知道,她还有别的情人,但既然她给他打来电话,他就认了这个孩子。
「你离婚吧,把我们的孩子生下来,我们好好在一起。」
电话那头不置可否。他不再问。或许他能做的,依然只是等待,等待她的决定,然后陪伴,跟着她转。
时间一天天过去。因为怀孕的关系,她的脾气越来越坏。因为接电话的速度慢了,因为临晨5点天都要亮了他却没有撑到日出就睡去,因为各种鸡毛蒜皮,她对他破口大骂。
终于,他忍受不了了。他像一个吸尘器吸附了她身上所有的黑点和负能量,却无处释放。一个大雪的夜晚,他在温暖如春的酒吧里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把送他回酒店的小姐带进了房间。他挂断郑州打来的电话。手机震得越来越凶,他就关了它。
但是,她通过手机定位,发现他凌晨5点不在家,在家附近的主题酒店。
这一次,她没有哭,没有尖叫没有大骂。她拉黑了微信,发了一条短信说「你必须跟我去把这个孩子处理掉」。
他说「好」。
于是,他就坐在手术室门口了。他张着嘴发呆,嗓子干得快要烧起来。
「连孩子都能做,还有什么不能做?她就是在报复我!用最残忍的方式报复!报复!孩子没了,我们也他妈没了。」
他愤怒,更绝望。他看着之前那个男人快速离开医院的背影,觉得他可笑。他想「我是绝对不会悄悄离开的。一会儿我就要当着她的面走。一句话也不说。」
「咕噜咕噜…」一辆手术车推了出来。
是那个短发女学生。
护士四周看了一圈儿,到处找那个进门时帮女学生戴防霾口罩的男生。刚刚他还坐在角落里刷朋友圈。此刻,他没在。
护士大喊「XXX家属」。
一个面目清秀,戴着棒球帽的男生赶紧从走廊的另一端一路小跑过来。
他伸手摸了摸女学生的额头问「你还好吧?」
「还好。怎么是你?他呢?」
「他打电话让我来的。他先回去了。你肚子痛不痛?冷不冷…?」
女学生没有想到,来迎自己的,不是她那个暖男男友,却是这个跟她出柜的男同性恋密友。
前几天,她体贴入微的男友还亲自登门向她的单亲母亲道歉。他说自己没有照顾好她,一定会负责到底。
他受着白眼四处借钱,连不那么熟悉的人都厚着脸皮开了口。借遍一圈,最终筹到5000。他对她说:
「我们要去最好的医院,我要好好照顾你。」
那时,她一点儿也不感到害怕,觉得福祸所依。她甚至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让自己看清了一个好男人。
她觉得他们一定是那1%,逃得过「毕业就分手」魔咒的男女。他们一定会很快结婚的。因为她几乎已经见过了他所有的亲友。他们中的好几个带着夸赞的口吻告诉她:
「你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他喜欢的短发女生。我们还以为他有审美缺陷,只会欣赏长发飘飘。」
他们笑起来,好像是在恭维她。虽然她听起来觉得有些别扭,但她依然感到幸福。
时间还早。病房里空得只剩满屋阳光。她一身冷汗。还没来得及问他上哪儿去了,什么时候回来,短信来了。他说对不起。自己夜不能寐,一闭眼,就会产生幻觉,与长发飘飘的前女友纠缠不休。他痛恨自己让一个女孩子怀了孕,受了苦。迷信里说「如果你让一个女孩人流,你会不顺多年。」他一想到将要面对手术后的她,就感到害怕。他说更不想面对一个这么差的自己,不想备受折磨,所以选择了逃避…
「希望手术一切顺利。你离开医院的那一刻,我就彻底解脱了。我对不起你,但我必须止步于此了」。
那一刻,她浑身颤抖。
休息区里还剩最后两个男人。
其中一个一直在打游戏,身体不时东倒西歪,扭来扭去。稍有空闲的时候,就会抓起一把散装薯片塞进嘴里。又一辆手术车推出来的时候,他低头迎上去,跟在车后往前走,眼睛至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他的手机。
车还没进病房。混在车轱辘干涩的滚动声里,有吵架的声音响了起来,夹在狭长的走廊两面墙之间撞来撞去。
女人的声音说「痛死了。伤死了。我要告你强奸。」
「啥?!?」男人终于放下手机。他快走了几步,把脖子伸得长长的,瞪大了眼睛探看病床上的女人。从背后看,他就像一只被人掐住了颈子的鹅。
「紧急避孕药你不是自己买的自己吃的吗?」他吼。
「滚!我让你戴套,你为什么不戴?」
「情趣你懂不懂?哪有那时间?戴完我都软了!你怎么是这么个没情趣的女人?」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情趣?上手术台的是你吗?被杀死的是你吗?强奸犯!杀人犯!」
「是你自己同意留在我那儿的好吧?我拿枪逼你了吗?」
「我锁门了。」
「拜托那是我家。房子是我的,门钥匙是我的。你怎么这么天真?我就是想教会你,不要相信一个发情期的男人。」
「滚!你就是只随时随地都在发情的狗!」
「你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你都自愿让人按墙上了还要叫人住手?哪个女人没有点被强奸的欲望?越反抗越有趣。一个巴掌拍不响!你可别都赖我一个人头上。何况你不是吃药了吗?假药?这你能怪我?我大灰狼装成了哈士奇。搞不好一切都是你设计的!」
「不要脸!我自己把自己设计上手术台生不如死?」
「太夸张了吧您!谁出来不都好好的,怎么就你生不如死了?」
「滚吧!我永远也不想再见到你!」
「正好!我早就说了给你5000你自己处理,非得把我逼到这儿来让人看笑话?闲的…」
至此,手术室门口,只剩下最后一个男人。
他还在等。
他不安地摆弄着一串钥匙,目光落在别处。他有些着急,不时站起来往手术室的磨砂玻璃门里张望。他的妻子正在做一个高风险的引产手术。
孩子很早就查出来有问题了,可他们不死心,倾家荡产,一心只想逃脱「被诅咒的宿命」。
他们都已经年近四十了。如果做掉,很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再有孩子。结婚十余年,之前的一次宫外孕,让他们无法再孕育。存钱借钱,治疗,再存钱还钱借钱,再治疗…各种磨难都经历遍了,却要在胚胎的心跳声和胎动感都越来越清晰的时刻,选择引产手术。
男人喃喃自语道。
「再也不要了。老婆好,一切都好。」
阳光黯淡下去,医院里的灯更亮了。
意外也好,情趣也好,解脱也好,结晶也好,有一些孩子,从暗中走来,还来不及见到光,又回到黑暗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