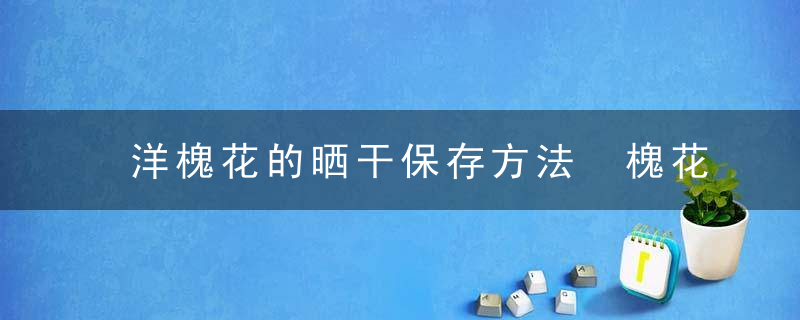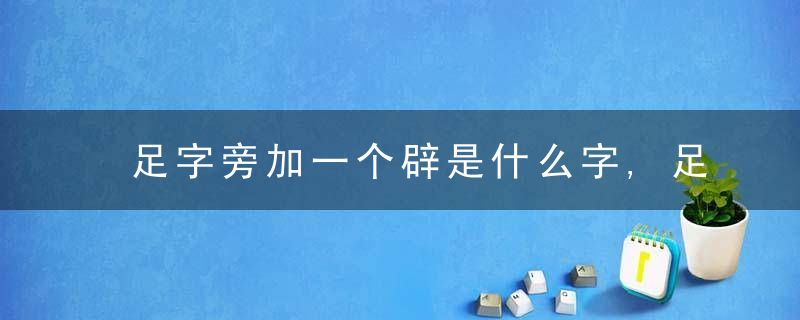你读了那么多书,赚的钱呢丨人间毕业季

“吴安宁,你记着,老子只当没有你这个儿子!你个小混账东西,现在能耐了啊!你读书出人头地了,家里的事情可以不管了啊!你尽管飞,能滚多远就滚多远!”
编者按
在这些美丽的漫长的夏日的黄昏;
但我知道,奇迹不再降临,
我也不再是那个手持鲜花
在机场出口迎候的人。
——王家新《来临》
毕业季,常逢夏日。从某一年的此刻,阳光融化了我们“学生”的身份,然后,被一份份表格重铸成各种身份,走向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
重铸的过程,或电光石火,或缓慢绵长,也许有惊喜和意外,也许还会有疼痛与煎熬。而重铸后的模样,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
是日,「人间」推出毕业季稿件连载,那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来临”。
来临:在我们毕业那一年丨连载04
2004年7月,我从荆州市长江大学毕业,到武汉谋生,兜里只有300块,还是找同学借的。因为读书,家里亲戚朋友能去借的几乎都借了,父母欠了一屁股笔债,我再也不好意思找他们要钱了。
我家在湖北省公安县埠河镇,在我童年记忆中,谁家孩子会读书,当家长的十里八乡都会有些面子。从小学到初中,我年年考第一,班长承包制,小我两岁的弟弟,也在班级前列。几个村的乡邻请客走访之间,父母也不知受了多少恭维。
可我读到高中,情况慢慢变了。村里与我们兄弟年龄相仿的孩子,绝大多数都出门学手艺、打工,年底都会带钱回家,给家里买彩电、通电话。
倔强的父亲和温吞的母亲没其他收入,除了自家的5亩责任田,还额外承接了别人家的6亩,日夜在土里刨食。父母从门口大路上去田里经过小卖部时,那些忙完农活打牌的人,看见父亲就笑着打招呼:
“又下田啊,来玩几把撒?”
“人家儿子读书厉害,现在忙,以后到城里养老享福。”
“我们反正没指望,就歪在村里算了……”
父亲通常也会笑着回敬:“你们先打,我儿子将来给我大钱打大牌,你们估计陪不起哦!”母亲则很受不了这种半玩笑、半奚落的话,后来下田回家就绕小路。
我家的光景越来越差,1998年,初三的弟弟被迫辍学,出门当了学徒,每月工资100元。我继续读书,弟弟也从徒弟慢慢变成了师傅。
熬到2004年,我终于大学毕业了,此前,教授多次劝我读研,说不要浪费自己的才气。我说:“连大学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哪里还能读研啊。”而且,因为学费没缴清,我没能拿到毕业证,得先找到工作,赚了工资回学校补缴学费换毕业证。
这些父亲并不管,只是在我毕业前夕,比以往更严厉地训导我:“总算熬出头了,家里欠的债等你来还,你要有良心。还有,你弟弟为你付出了很多,你要记得报恩!”
我要出门找工作,表示自己想要一个手机,方便与用人单位联系,挣到工资后就还,母亲想了很久,就到荆州城的姑妈家坐了半天,拐弯抹角地表示了来意:借钱。
在整个大家族看来,姑妈家“实力”最强。姑爹年轻的时候就带着施工队修路砌房,终于将家安在了荆州城——而且是买的一块地,建了三层高的小楼。姑妈家的两个表哥一个表姐,都成了衣着光鲜的城里人。
姑妈一直很疼我,明里暗里给我家也补贴了不少,很多借款甚至让我父母不要跟姑爹说。可那段时间姑妈家也很拮据,赶上刚出嫁的表姐回家探亲,姐夫得知情况后,特意到银行取了1500元借给了母亲。母亲拿着钱买布料、找裁缝,给我定做了套西服,还买了一个国产的东信手机。
“出门在外,要讲点形象。”看着我穿上西服的样子,母亲欣慰地笑了。
多年后,妻子看到我穿西服的照片,戏谑地说:“好土。”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华传奇》杂志社做编辑。
杂志社社长潘宜钧先生仁厚,考虑到新员工的困难,以杂志社的名义租了两套简单的两室一厅。4个同事一人一间“宿舍”,每月每人只需承担300元房租,比市价便宜了一半有余,水电气和长途座机费,都由杂志社担负。
平日里,4个人搭伙做饭,4块钱一斤的五花肉,2块钱一斤的白鲢鱼,就是荤。通常是周五晚上,砍几斤排骨,或者买只鸡,炖锅萝卜土豆之类,喷香。饱食一餐后还剩下些大骨头或鸡脖鸡爪之类,翌日中午再煮一次,加作料加水下青菜,直到把残汤都倒碗里就饭,照样有着吃大餐的满足感。
那时候武汉的物价不高,热干面才1块钱一碗,加个鸡蛋才5毛。当然,我是属于偶尔才加鸡蛋的那一类。
就这样紧巴巴地抠门过日子,当时月薪1600的我,居然每月都能结余。而结余下来的钱,基本是汇到老家,给了管账的母亲,好去还债。
每个周末,我都会给母亲打电话,听她唠叨:张大爷家的母猪生了几只小猪,李大娘不知得了什么病怕花钱喝了农药,王家姑娘在外打工跟了一个大款,赵家儿子学裁缝带回了一个媳妇很标致……唠叨到最后,都会回到同一个主题——谁找我家讨钱了。
“你儿子都大学毕业了,一个月应该赚不少吧,我们实在是转不开了,啥时候方便……”
“一点小钱本来不该上门的……”
“你家儿子有出息哦,我那个不成器的东西,也要结婚了……”
乡下人无其他技能,只懂得春种秋收,一年四季的劳动付出,只有秋季才能折现,手里稍微有点存款,就会急急忙忙地把房子翻新成楼房——若家里不是楼房,儿子几乎讨不到媳妇。而砌房的时候,也会找亲戚朋友借钱。
家乡有句老话叫“还账容易攒钱难”。曾借钱给我家的,已经很不容易了。母亲性子温和,就算再觉得委屈,也只是慢慢跟我叙述,并努力为债主说项:“人家都是晚上来的,怕别人看见不好,有时还带半蛇皮袋子花生、黄豆什么的,说送你爸喝酒……卖农药化肥的小王,年年年底的时候挨家挨户收赊账,可走到咱们家门口,从来都没进来过,今年咱们再也不能拖着了……”
而父亲脾气暴躁,通常在电话那头一口酒气地骂:“吴安宁,你什么意思,怎么不拿钱回来还账?人家都讨到你家里来了!你叫老子怎么做人!”
其实,父亲也知道我每月的大半工资是汇给母亲了。可比起赵家学裁缝的儿子年底带回来两三万、李家姑爷的出手阔绰,父亲总认为他的儿子应该很能挣钱,汇少了:“你读了那么多书,赚的钱呢?”
而另一边,做厨子的弟弟,彼时染上了厨子们的通病,打牌赌博,一年到头也是两手空空。父亲更为恼火,认为自己家的两个儿子都是废物。2004年团年饭,父亲喝醉了酒,把我们俩兄弟骂了个狗血淋头——他能抱怨的,无非是我们赚不到钱,把他逼得没办法,我们都这么大了,还要结婚,他也老了,奔不动了。云云。
父亲越骂越上劲,弟弟脾气跟他一样暴躁,最后把桌子掀了:“你这么有本事,怎么没把家安到城里!人家姑爹还不是农村里的,还有三个孩子!”
“你个狗日的,还说老子!”父亲暴跳如雷,捞起椅子就往弟弟身上砸。隔壁都来劝架,拉父亲拉弟弟,母亲只是哭,因为自己家在大年三十,被人看笑话了。
那年回家,我身上留了300,余下的3000元全都给了母亲。
不过,的确是太少了。
压着沉重的负担,有时候做梦都梦见被人催着要债,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赚更多的钱。拼命省,总不够。
毕业后的一年时间里,我在BBS社区写小说,点击率比较高几个门户网站原创频道特邀连载。
小说吸引了一个女孩,也就是我的妻子。她那时候大四,没什么课,就到武汉找我,发现我一贫如洗,戏谑道:“每次你到了发工资的时候,你家里准会来电话。”
我苦笑。
多年后,妻子回忆起当年,还心有余悸:“你那时候真穷啊,你还说过最怕同学到武汉来,一待几天,吃喝住的,完全顶不住,找同事借了多少次钱啊。”最多的一次,我住的房间里打着地铺,我和妻子睡床上,另一对情侣睡沙发床上,地上还横竖睡了5个人。
因为在网上写小说,四面灌水八方拍砖,认识了一帮文字江湖中的前辈大哥。有个大哥私信加我,问:“老弟,写点言情凶杀侦破鬼神,只要文通字顺,猎奇好看,就给钱,干不?”
“干!”
我不知道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谁来买单,反正我只管接活儿。每天晚上就扑在电脑上写啊写,前辈说句“那边通过了”,我就异常高兴,因为不久就有钱打过来。
2005年各类山寨杂志层出不穷,充分满足了人民群众越来越低级的精神需求。有封面上全是妖娆半裸美女的《私密情话》、《阁楼夜话》、《迷情》、《闺蜜》,也有各种揭秘类单本杂志《共和国大案》、《贪官陈XX的情妇们》等等。
“到城市混着的民工们,也要有消遣嘛。”那位介绍活儿的大哥跟我说,“老弟,你很灵光,随便都能编几个故事。”
很偶然的一次,我在火车站附近的破书摊上,发现自己写的小黄文《打工遇上了富婆,让我何去何从》,配着袒胸露乳的美女图。几个衣衫褴褛的农民工,看得一脸愉悦。
2006年,我全年工资结余两万多,基本给家里还了账。写稿的收入也差不多两万,年底我把钱全部取出来,将厚厚一叠现金递给当时还是女朋友的妻子:“来,用力地砸我,让我感受一下被钱砸的滋味。”
妻子形容当时的我,“眼冒绿光、满脸通红、言语苍白、手舞足蹈,像个十足的疯子”。
在这年年底,我准备结婚了。没有媒人没有说客,我和父亲去岳父家里提亲。在离岳父家不远的超市里,父亲圈巡着架子上的香烟,最后让拿了一条170元的蓝黄鹤楼,不确定地问我:“这个烟可以不?”这种烟那时乡下没有,只有在城里姑爹家和过年时外出务工返乡的小年轻手中见过,而父亲平时只抽3块5的蓝金龙。
一条烟加一篓桔子,我们登了岳父的家门。父亲一进门,之前的兴奋全然不见,待至岳父拿着一包30块的满天星出来招待,父亲不自然地扫视了几眼自己带进门的礼物,更是显得有几分畏手畏脚。
我们去之前,妻子就说过我家的情况,岳父岳母仁厚,半句没提彩礼,好烟好酒好菜地招待了我们父子。父亲回去后在酒桌上对着乡邻吹嘘:“抽的是满天星,喝的是15年的白云边,还特地接我去贵州花江狗肉馆里吃狗肉,真是不一般的好吃!”
父母说我们结婚要置办几套家具,空荡荡的,不像话,得花钱,我打了1万块钱回去;戒指,我们自己选的最普通的铂金对戒,光秃秃的两个圈,花了2000多一点;项链太贵,看了几次,放弃了。
对于婚礼的衣服,听说在汉正街批发市场最便宜,我们在密集如蛛网般的旮旯胡同里转了好久,反复掂量价格,最后我自己买了一整套:西服、鞋子、衬衣、羊毛衫,讲了半天价,1000元。妻子看中了一套漂亮的大衣,标价3000,也跟对方磨了许久,最低1800。妻子不舍,说1600就买。假装拉着我走,以为店家肯定会挽留。
可那次,店家鄙夷地哼了一声:“你们去看吧,谁家会比我还便宜!”
我当时以为妻子真不想要那件大衣了,继续兴高采烈地转悠,不停地给她推荐。我看中了一套粉红色的大衣,标价1200,最后谈到400,妻子没说什么,配合着试穿,买单。
在准备返回的时候,妻子突然哭了:“我觉得自己好委屈,结婚,居然这么寒碜。”
我还有点不解,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乡里人结婚就是到镇上买布做两套新衣服,哪里有寒碜不寒碜的?不知道怎么开始,我们就吵了起来,我固执地认为她高冷,妻子大哭,觉得我不通人情。路人驻足围观,有几个好心阿姨对妻子嘘长问短,后来一致批评我。
那一刻,我才想到,妻子本来就是县城里出来的小公主。岳父是公务员,且有着精明的商业头脑,在县城中心地段有着4层楼的房子,岳母全职太太,平常的交际圈子都是县长局长的夫人们。妻子从小就有个公主梦,心目中的英雄,会驾着五色祥云来娶她。
为了安抚妻子,第二天我们又去了那家店。店家说,就这独一件了,1800一分不少。妻子和店家攀老乡,讲好话,可店家始终不松口。我把妻子拉到一边:“给1800算了,难得你这么喜欢。”她恨恨地盯着我:“你很有钱啊。”拉着我蔫蔫地走了。
可是回来后,她仍然觉得舍不得,还是想要。
第三天我们又去,带了1800,店家不卖了。说已经收了别人的订金,人家下午就来取货。
当时从我们住的地方去汉正街,倒几趟公交,大概要1个半小时,往返路途就是3个小时。3天的往返在200元面前,不值一提。
我们这样锱铢必较地省,父母又打电话来,说,为了你们结婚把房子翻新了,又找谁谁借了多少多少——这回人家都很慷慨,连最吝啬的张老三,都同意把他砖厂的砖先赊给我家。老家的人实诚也狡黠:你家老大会赚钱,我还怕你们家还不起?黄沙水泥砖头瓦块,要什么来拖就是。
父亲在电话里说:“你读书出去了,不能不管你弟弟,要是房子不翻新,他讨不到媳妇。”
我默然,说是为我翻新的房子,实则是为了弟弟。
回到老家的时候,妻子对我说:“楼房修得好气派,这钱,估计又等着你还吧?”
2006年腊月二十四,结婚当晚,就有人到家里讨账,我和妻子在楼上婚房内,要账的在楼下客厅坐着不走。
母亲无奈,只得到楼上来找我们——故乡有个习俗,新媳妇进门要给全族的长辈端糖茶送鸡蛋,喝了茶吃了蛋,就得给红包。这些红包是长辈送给新媳妇的,额外记账,不在贺礼之列。
大概8000的红包,妻子一分都没要,全给了母亲:“妈,我知道你们为难,先还账吧。”
母亲红着眼对妻子说:“小莉,牵连你了,当妈是借的。”
尴尬的是,这些钱并不够。前一晚走了一个债主,第二天又来了两个。贺礼是父母收的,我们没拿,回家之前我俩带了5000,在家杂七杂八已经用了3000,回武汉还得有开支。
唯一剩下的钱,便是妻子的嫁妆,是岳父岳母给的2万。这笔钱不知怎么被父亲知道了,又在家骂:“吴安宁,你什么意思,有钱不还?你要是把家里的钱带走了,老子打断你的腿!”
母亲哭着劝父亲不要嚷,我不敢吭声,倒是妻子忍不住,进门第一天就跟公公吵了起来。
“你什么意思,他在武汉过得什么日子,你知道吗?每月的工资、稿费,大部分给你们了。他读书花了你们多少钱?零零散散还了好几万,他还要买房子还要养小孩!”妻子性格既温婉又刚烈,吵起来刹不住,“我娘家一分钱彩礼都没要,你们是想要我娘家的钱吗?”
在酒精的刺激下,父亲双眼胀得通红。可能是因为儿媳妇刚过门,他不得不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不能正面跟儿媳妇吵,只是更加严厉地吼我:“吴安宁,你记着,老子只当没有你这个儿子!你个小混账东西,现在能耐了啊!你读书出人头地了,家里的事情可以不管了啊!你尽管飞,能滚多远就滚多远!”
母亲死死拉着父亲,大恸。一群看热闹的叔叔婶婶闻风而来,将我们一家人拉开了。婶娘们纷纷劝慰妻子,说父亲酒醉闹事,别理他。妻子异常坚决:“他对我老公有养育之恩,我们自当为他养老,但这种无理训斥,我一概不理!”
乡里还有一个规矩,新媳妇进门,头一年要给父母两边的兄弟姐妹拜年。
结婚后,转眼就到正月。春节到20公里外的大伯家拜年,免不了被姐夫拉上桌打牌。牌打得有点大,一晚上输了600。
就在大伯家,喝醉了的父亲,还是没忍住,对我又是一顿痛骂:“你凭什么跟他们打这么大?你有钱不还债,装什么大爷?他们都是些牌精,就等着你这种憨货……”
大伯是个糯米菩萨,说父亲年轻时就这样,喝多了就乱来,不用理他。大妈见妻子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拿着扫把狠狠地打我父亲:“你个不清白的东西!你的账,跟儿子有什么关系!”
结婚后,就越来越不想回老家,因为回到家的话题依然是那一个:钱。
2007年春,我和几个朋友创办了一个小文化公司,连妻子的嫁妆都投进去了。不久后母亲打电话来,说堂姐家做楼房,借钱,“最好是1万,5000也行”。还补充,我当年读书时,堂姐家也借过钱给我们。
“我们实在是没钱了,刚办了个公司,您不是不知道。”我跟母亲说。
“那,你能不能想想办法,找同事或者同学周转一下?”母亲怯生生地说。
“在外谁都不容易,找人家干嘛啊?”
就在这时,父亲抢过电话,吼了句:“吴安宁,你不要六亲不认!”
我和妻子百般无奈,用信用卡在柜员机透支了5000,直接汇给了堂姐。后来慢慢用工资填上。
很多事情开了头,就收不了尾:这年8月,小舅舅也要修楼房。母亲百般为难,要是不借,小舅妈那张嘴,会让我家所有人都无地自容,我实在拖不过了,才找一个铁哥们,挪了5000给小舅舅;到了年底,大舅舅家的房子也挺不住了,可公司需要增资,我们实在拿不出来钱,便没有借。
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大舅舅、大舅妈都没怎么搭理我父母。
2008年秋,女儿来到这个世上。
岳母来武汉探望外孙女的时候,头一次看到我们跟别人合租的那个阴暗潮湿的小两房,老太太回去哭了两天:“那是住的什么地方啊,比牛栏都不如,床腿都断了,用书垫着,我们手心里宝贝着的姑娘,哪里受过这种罪啊!”
“是她自己不听话,叫她回来上班不回来,活该!”岳父嘴硬,心却是软的,没过几天打电话给妻子:“你们去看房子,首付缺多少我们来凑!”
房买了,弄好住进去,月供不算,还欠10多万的外账。岳父的钱,我也心心念念着还他,已经帮了这么大的忙,心存感激之余,更不能无耻地占着便宜吧?
为了赚钱还债,我和妻子不得不把才满百天的女儿,丢在了乡下。两手空空的我,白天努力上班,晚上拼命写字,接各种私活。
妻子上班的地方离家特别的远,要转3趟公交,单趟2个小时打不住。8点上班,5点半就要起来,不忍妻子如此折腾,我每天骑小电驴送她到武大凌波门公交站,再折返我上班的地点,让她只需一趟公交即可到办公室。
每天早上我们6点半出门,晚上7点一起回家。进家后,我立马坐在电脑面前开始码字,妻子则进厨房做饭。写到半夜2点,洗个澡睡觉。第二天继续6点半出门。
一天回家的路上,妻子情绪特别不对,各种抱怨,最后流着眼泪在车子后座绝望地哭:“你一个月3000多,我一个月2000多,加起来不到6000,月供就要2000多,还有10几万的外账,爹妈打电话的时候我还要哄着他们说我在外面很好,免得他们担心,更怕他们失望。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过成这样,整个人生都是灰暗的,看不到任何希望,这样的日子何年何月是个头!”
妻子的眼泪濡湿了我的后背,我没回头,也没回答。
不知道怎么回答,也不敢回头。
凌晨2点、早上6点半,重复着、坚持着,女儿在3岁的时候,10万的外账居然被我们还清了,没那么难过,也并不宽裕,继续上班加码字,又买了车。女儿终于可以不用做留守儿童,我们让母亲把她带到了武汉。
父亲留在老家务农,经常打电话,劈头盖脸还是那句话:“吴安宁,你两三年就在武汉买房买车,怎么不拿钱回来?”
在他看来,我成家立业了,在老家应该开个户头,各路亲戚朋友有什么婚丧嫁娶,我都应该上人情、随礼。除了正式的酒席,其实像乡里张三生日、李四杀猪、王五收鱼等这样非正式的酒席,说是面子,其实大多是聚在一起打牌的由头,我和妻子都不喜欢形式,故而没做理会。
“吴安宁,我都是跟你在挣面子!”父亲说。
我只能不吭声。我知道乡里的人情支出:一般宴请要吃3天,每天的活动就是吃饭打牌,父亲一般随300礼金,打牌3天还要输个3、400。
这只是正式的宴席,非正式的更多:张三生日,会邀请许多朋友来吃饭打牌,受邀者往往会拎点礼物,烟是硬通货,讲面子就是170的黄鹤楼,一般人家就是85的红金龙;李四杀猪,也会邀请许多朋友喝杀猪酒,不用带礼物,但是免不了要打牌,吃喝输赢之间,就消耗了本来就积累不多的财富。
父亲在乡下,各类宴请都少不了他,所谓的门面开支,花费不小。叔叔和婶娘曾跟我打电话抱怨:
“你爸真是不像话,杀一只猪恨不得喊全村的人来喝酒,人家说猪肝好吃,他就嚷着下猪肝,说猪耳朵好吃,就要炒猪耳朵。
“你妈又不在家,让我们来烧火做饭!自己颠颠的去买好酒……
“一只猪总共才多少斤?一天就吃了一半!酒喝了二三十斤……
父亲好面子,又得益于儿子的名气,各种饭局都会受到邀请。礼尚往来,他支撑不住,就会心烦。
怪我,没拿钱回去。
做厨师的弟弟,慢慢也上了路。2008年底,弟弟结婚,弟媳是邻村人,善良温和。这样一来,父母轻松了许多,但依然还是反馈:缺钱。
后来,弟弟一家到武汉,经营起一个小早餐店,缺人手,便把固执的父亲搬来了。那些只是打牌的场合,父亲再也没机会参与。有些酒席还是得吃,弟弟收回财政大权,让叔叔代着随礼,不到现场,也不可能打牌,一年下来居然没多少开销。
父亲不再骂我,可是偶尔会骂弟弟:“老子在老家,一年种田都有几万的收入,跟你做事,你请得起么!”
弟弟脾气一来,也嚷:“那你赚的钱呢?自己在老家管自己都不够!你在武汉,每天一包烟,每天三顿酒,换着花样吃,还想怎么着?”
父子俩吵一顿之后,继续该干嘛干嘛。
父亲偶尔回到老家,对着那群老哥们就开始吹牛:“我小儿子生意不晓得几好,月收入过万,我大儿子,在开公司。”
父亲的确有着吹牛的资本:2015年,我和弟弟先后生了二胎,都在武汉安了家,我的小两房换成了大三房。再有亲戚朋友借钱,两三万之类的,我们兄弟俩随手就给转了。
弟弟的店子小本经营,每月进账,可我和一帮朋友盘了个公司,却让人头疼:朋友们都是理工类博士,个个大咖,喜欢沉浸在自己的技术世界里,公司的管理、团队建设、商务谈判基本丢给了我。公司每月花销将近20万,各种欠款将近400万。我的工作不是陪人喝茶谈合作,就是陪人喝酒讨钱。最艰难的时候,我们几个工资都压着,先保障员工薪资和绩效。
可自己房贷也要还,娃娃也得养,妻子一个人,支持不了。这让我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轻度抑郁,整夜失眠。
有时候出门讨账,应酬一天,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妻子打开门,第一句话就是:“老公,今天要到钱了么?”
编辑 | 唐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