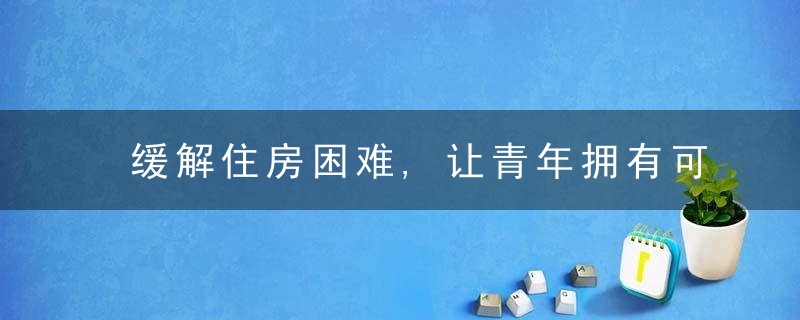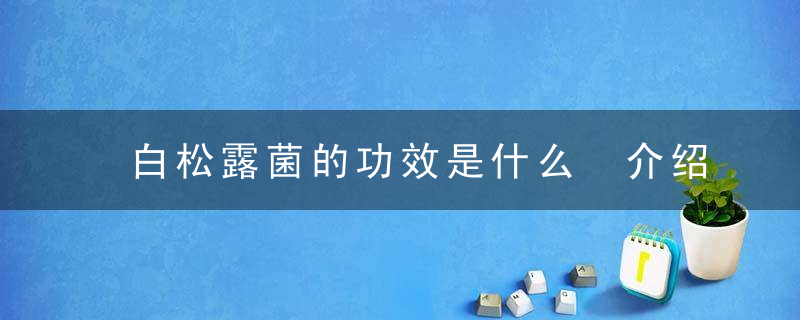城市大分化背景下的集体焦虑

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青年群体都在扮演参与和影响世界进程的角色。他们容易被煽动,也懂得独立思考;他们提供建设力,也具有破坏力;他们执着眼前,也关切未来。
刚刚胜选的新任港首林郑月娥,急需解决的就是香港青年人的“上楼无望、上流无路,上位无门”等问题,这些问题指向香港固有的结构性矛盾,是诱发青年对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的根源。
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大陆,有着和香港相似的青年问题,甚至更为严峻。由于地理面积广阔,群体的横向迁移减缓了矛盾纵向上升的速度,但不可能任凭其自由发展。特别是在80后即将步入中年,90后成为青年主力的时刻,原有的矛盾并没有解决,新的矛盾正在产生、介入,新旧矛盾相互交缠发酵作用于新的青年一代。依靠时间去稀释矛盾是不明智的,因为无论是从生理还是心理层面来看,中年问题和老年问题的本质都是青年问题。
青年问题主要见于城市新移民,他们既具有移民特质,又具有青年属性。中国压缩式的发展导致青年人在城市中打拼,却无法被城市接纳。身份认同标准和自我实现路径成为绑缚青年人的两大枷锁,引发集体焦虑,催化青年危机的形成。
首先是身份认同问题。对于投身大城市的外地青年来说,构成身份认同的要素逐渐被简化成两样东西:房产和户口。这两样硬性指标足以将徒手在北上广打拼的青年碾压得体无完肤。
传统社会学将社会分为8个阶级,但现在看来这一分法可能有点过时,有学者称现在中国社会只有两个阶级,有房阶级和无房阶级。此语虽有调侃成分,但也道出了中国社会的实情。房子相当于城市的股票,是奢侈品,也是必需品。
无法负担高昂房价的青年退而选择租房,但城市的租房市场是不稳定的,青年在与房东的博弈中毫无优势,疲于在城市边缘的不同陋室中辗转。
住房危机导致了身份的被剥夺感,据实际统计,毕业于“211”和“985”高校的北漂青年中,有20%是蚁族,他们不敢消费,更无法承担婚姻成本,导致个人和群体的生命进程延后。
至于自我实现更是道阻且长。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精英,有很多处于“在职贫困”状态,他们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受到重重阻碍,知识无法作为上升的有力支撑,通过网络(比如淘宝网店)开创事业、晋身上流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很多类似的窗口都越发饱和、限制严格,进而趋于关闭。
而家乡的低学历同侪早已通过做些小生意、投资等方式赚取了大量财富,日子富足。在巨大的心理落差和对前途的怀疑中有些人选择继续消耗,有些人则转而回乡谋生,或创业,或安于体制,是为“洄游”。
青年群体的流动直接关乎一个城市的活力,哪个城市的青年比例高就更能够赢得未来,因为相比“看透了社会底牌”的中老年人,青年人更愿意相信奋斗和理想。一线城市对青年的吸引力无法取代,二三线城市的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这意味着中国终将迎来城市大分化的时代。
青年的迁移直接造就了分化时代的定名,而这个时代正反向钳制青年流动的脚步。大城市需要新移民,但却缺乏过渡性思维,大量城市边缘的青年聚居村被拆除,实际上是拆掉了城乡之间的过渡和缓冲平台,拆掉了城市发展的发动机。
将这个中转站铲除,在住房政策上又无任何倾斜,这就逼迫青年向旁、向下流动,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引发很多问题,而大城市也终会体验到城市后续动力不足的症候。如何让青年在大城市中有融入的机会,有提高技能的途径,有现实生活的尊严,应是城市管理者、政策制定者以及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