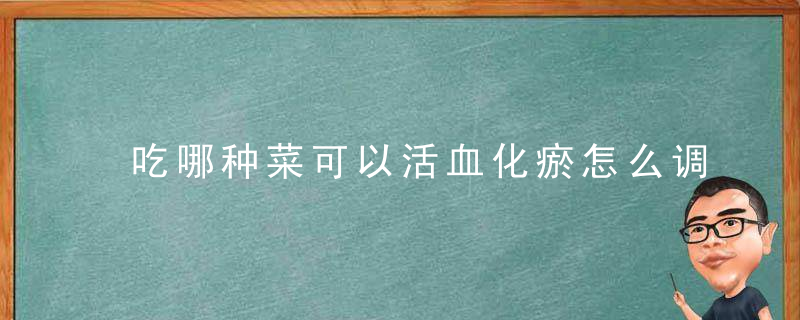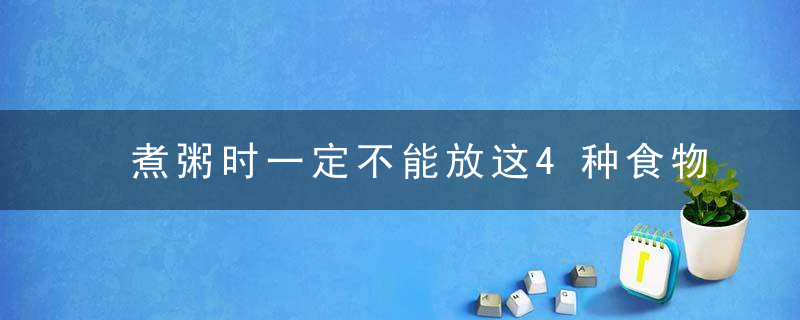迎接新文明轴心时代的来临——从“文明的冲突”到“文明的对话”

林安梧
本文作者:林安梧(山东大学海外杰出访问学者、台湾元亨书院院长)
如何免于欧洲中心主义,是以亚洲中心主义取代吗?当然不可以,应该是以多元化来取代中心主义。
“迎接”的意思是快来了,但还没来。对人类文明,尤其是对中国而言21世纪是一个崭新的年代。中国20世纪几乎一直困陷在如何追求现代化的困境中。进到21世纪,中国已经参与到现代化进程中,并且可能成为现代化的重要反思者。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别于西方,最具有机会、权利,也最具有当该去做的责任,去好好反思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现在所谓的文明冲突真的就是文明冲突吗,还是权力的冲突?
在各个领域,我们一直在西方所给予的概念范畴、理论框架和发展向度之下来思考问题。我们能不能给出新的理论框架、概念范畴和发展向度来思考问题?如果我们没办法,世界可能会陷入一种比较麻烦的境地。就目前来讲,从希腊罗马基督宗教到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发展,现在能够对整个人类文明起到较大反思作用的,恐怕只有中华文明。我认为文明冲突只是表象,表象之下是文明的衰颓。问题比较宽泛,我们抓几个要点来谈。
一、归返“轴心时代”,寻求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可能文明的“轴心时代”是1949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他的大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的。这本书将人类的历史划分为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这四个基本阶段,其中,第三阶段是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东西方同时独立地产生了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四个轴心文明。
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段时间,雅斯贝尔斯把它称作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期间人类文明取得重大突破,各文明相继出现伟大的精神导师,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他们都可谓德智双彰,参赞天地。当然,科技时代显然是以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文明作为主流。
现在所谓的新文明轴心时代,是经由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这一连串现代化发展后,也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科技时代之后,21世纪人们所要求的一种新的文明方式。新的文明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目前还在探索之中。我认为应该回到古文明,重新去寻求新的可能。
整个西方现代的主流文明已经不是原先轴心时代的文明方式了。科技时代是以科技挂帅,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已经被高张,资本主义化、消费化的趋向已经向全球蔓延。在全球化之下,人们把需求和欲望混淆了,把权力和理性也混淆了。在这种状况下,人们循着欲望之力的理性法则向前奔赴,已是一往而不复。
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认为,这正是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的时候,但中华文明本身还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不能克服自身的问题,中华文明不可能对人类文明产生正面的示范作用。回到古文明经典的范式中去,我深深地觉得这是中华文明对人类所必须要担负起的责任。
林安梧
二、反思:超越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从文明的轴心时代发展到西方的现代化,现代性目前面临诸多困境。譬如,亨廷顿所提到的“文明的冲突”,福山所提到的“历史的终结”,世界目前正陷入恐怖攻击的不安状况。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如何能免于霸权,做到王道,很不容易。西方近现代文明没有王道的概念,怎样让王道概念在中华母土上很好地生长,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参照和新的可能?这无疑是非常艰难的事业。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与现实有诸多相应之处。2001年“9·11”事件,我当时在台湾看到电视的实况播出,受到非常大的触动。
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认为在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福山是日裔的美籍学者,他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提出,有两大力量共同推动人类历史的前进:一是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一是黑格尔——科耶夫所谓的“寻求承认的斗争”。前者驱使人类通过合理的经济过程满足无限扩张的欲望,后者则驱使人类寻求平等的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股力量最终导致各种专制暴政倒台,进一步推动文化各不相同的社会建立起奉行开放市场的自由民主国家。紧随而来的问题是,在“历史的终结处”,政治经济的自由平等,是否能够产生一个稳定的社会,让生活在其中的人得到“完全的满足”,抑或,“最后的人”被剥夺了征服欲的出口,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冒险一试,让历史重返混乱与流血状态?
我认为福山对这个问题已经有非常深入的思考,但他一直处在西方的主流线索及其所面临的问题之下,这也是西方在现代化之后很多思想家思考问题的方式。他发现西方主流脉络所面临的问题非常严重,但他在寻求解决方法时,也是在这个脉络中思考的。这些思想家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不懂东方传统,对儒道佛的理解非常有限,所以他们的思考也是有限的。他们一直深陷于从古希腊巴门尼德以来的“存在与思维一致性”的传统之中。
有一次,我在路上碰到一个博士生,他在和我聊天时一直谈到这个问题。人们一直强调存在和价值是分开的,存在是实然,价值是应然。在东方传统中,存在和价值就其源头来说,特别在儒道的传统,乃至于在印度教的传统之中,二者是和合为一的。至于存在与价值的分离,是人们经由思维去控御,而切割出一个存在,把所谓的存在和主体区隔开来。
认识活动其实不是主体对客体的掌握活动,主客体原本就是合而为一的。人的参赞化育开启了主体的对象化活动,使得对象成为了被决定的定象,由此产生对对象物的认识,而我们所认识的其实是被规定的对象物,并不是存在本身。
在闽南语系统中仍然保留着最古老的认识论话语,就是“八”这个字。“八”是分别之意,“尔八否”就是“你知道吗”。认识活动其实是将总体“八”开成两个部分,是一个不断区分、不断精细化、不断定位化的过程。“一气流行”“一体之仁”的传统在人类文明中是非常可贵的,而且是最合乎“常道”的传统。
如果一开始就将问题放到主客二元对立的架构之下,放到线性的思维方式中去思考,而把通过主体的对象化活动所规约的对象物当成存在本身,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是现代性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像福山和亨廷顿所提及的问题,我们可以以不同的视野去重新思考。福山虽是日裔的美籍学者,但他对日本文明的理解有限。其实很明显,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冲突问题其根源并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霸权的冲突。如何免除霸权思考才是当务之急。这个世界已经被霸权所笼罩,这里涉及现代化发展的问题,也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严重问题。
如何免于欧洲中心主义,是以亚洲中心主义取代吗?当然不可以,应该是以多元化来取代中心主义。在文明的轴心时期,不同文明是相互隔绝的,人们不可能通过一套话语去建构。而现代性的社会中,人们是通过一套欲望之力的理性法则去建构,而这个法则又挂搭在很多很美妙的口号之上,包括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等。我当然赞成这些美好的概念,但当诸多权力挂搭在这些话语上时,这些话语就不能够依其名而如其实,反而常常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甚至因为对“名”的追求而导致更严重的“实”的毁损。
历史是不可能终结的。人类不可能用分别相、用话语去处置这个世界。这根本上是对天道的僭越,这是以话语论定为先的西方主流传统所造成的遮蔽。
东方的传统则不然,一神论的思考才会出现这种严重的问题。一神论是人类文明中一种独特的发展样态,它不能够包容其它的非主流传统。唯有摆脱这种话语的权力控制,人们才有可能回归到生命之源,回归到存在本身,才有机会免除这些争端。我们的道论传统很宽广包容,宗教形态是“教出多元”而“道通为一”。
要把我们的思想传达出去,让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
林安梧
三、中西之别:存在、思维与价值西方哲学没有所谓的工夫论,而东方的儒道佛三教,包括印度传统,都有关于修养工夫论的思考。如果没有思考到关于“戒、定、慧”,关于“正德”的问题,“公共性”可能吗?如果人伦都毁损了,人权可能吗?如果民本都被丢弃了,民主可能吗?如果人们的觉性的自觉都毁损了,请问自由可能吗?
20世纪,很多启蒙的知识分子误认为人伦是妨碍人权的,民本不是民主,儒道佛三教所说的自觉,这种精神上的自由与人权上的自由无涉。而且精神上的自由是积极的自由,如果你一直强调积极的自由,可能连消极的自由都得不到。他们强调政治社会共同体所谈论的是消极的自由。果真是如此吗?
我在台湾清华大学教书的时候,学生问我说,老师,您脑袋里装的都是很新的东西,为什么一定要打扮成很传统的样子?我说果真吗?其实我身上很多新的东西,帽子是新的,我穿的是皮鞋、西装裤啊,只是我穿了唐装,你觉得有不搭的感觉吗?不会啊,很有创意嘛。我说既然如此你们也可以试试看,他说,老师,我不太敢穿。为什么?资本主义化、消费化的欲望之力的理性法则所形成的强力的逻辑构造,已经渗入我们的骨血中,把我们彻底控制了。
1998年,香港中文大学开了一个“中国文化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那天我兴冲冲地穿着一袭长袍,我想会碰到很多老前辈,包括饶宗颐教授、钱逊先生,他们可能会穿长袍,结果那天只有我穿长袍。相对来讲,西方是理性逻辑的结构,是一神论的信靠的宗教,更强调的是“存在与思维的一致性”,而不是“存在与价值的和合性”。他们是要回到以逻辑理性为主导的强控制系统中,认为那样才能秩序分明,而我们是回到价值之源去反思。这个对比中,其本质还是“绝地天通”和“巴别塔”的区别。
“绝地天通”是在《尚书·吕刑》中所提到的,巴别塔的故事出现在《旧约·创世纪》中。巴别塔的故事中谈到,人类一旦走向理性就必然要走出原始混沦,与超越的绝对者疏隔开来,天人分离为二。而我们强调,虽然天地鬼神的通道被封住了,人类才真正迈进人的世界,但是人与天地合德,天人是合而为一的。
我们是连续性的关系,他们是断裂性的关系,我们强调人与天有一种直接楔入的互动感通,西方强调必须有中介者进行连接。我们的社会结构比较接近于费孝通所说的波纹型结构,而西方是捆材型结构;我们是差序格局,西方是团体格局。我们强调理,经由具体的感通去体证。西方强调法,戒律是来自绝对权威的命令。我们的道德实践强调的是仁,人和人之间存在的道德真实感,等差之爱。西方讲的是普遍之爱,爱作为你主的绝对权威者,并以同样的方式爱你的邻人。我们的宗教是一种自然宗教,是一种泛神论的信仰,而西方的宗教是体制内的宗教,是一神论的信仰。我们可做这样的概括。
林安梧
四、文明交谈的向度及所涉内容我很反对那些对中国文化,包括对经典的采取固守态度的原教旨主义者。这显然是不对的,当然要沟通,但我们的对比项要立稳。
如果没有对老庄和佛教的深层理解,两者能交谈吗?不可能。如果没有对儒家人伦和西方人权的深层理解,人伦和人权能交谈吗?不能。对君子对公民这两个概念没有深层理解,也不能交谈。我们这个民族是最有办法进行文明交谈的。语言的翻译很重要,但我们以存在为本位,相对于语言,我们这图像的文字更接近存在本身。
世间的常经之道需要重新去思考,亨廷顿和福山都没有思考到最根源性的常道上。在西方以话语为中心的思考中,他们没有办法展开对根源性的思考。在东方传统,尤其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这种思考并不是杂而无统的开放,也不会陷入虚无主义。我们是从“分别相”进入“无分别相”,就是存在与价值和合为一的源头。在儒家来讲,这个源头既是你的本心良知,也是宇宙天道。在道家来讲,它是真正虚静明觉的心,也是宇宙造化之源的彰显。在佛教来讲,唯有回到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的本原状态,才能够妙生如来法界,才不会有执着相、染污相,才不会陷入烦恼的境遇中。
在20世纪这些思考好像被熟视无睹,人们认为政治和道德就应该区隔开来,没有所谓道德化的政治。人们会忽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什么是“德”?德不只是西方人所说的道德,讲的是根源和本性,是“道生之,德畜之”的“道德”,是“志于道,据于德”的“道德”。现在在中国哲学界中,谈到“道德”会回到“志于道,据于德”,“道生之,德畜之”去理解的学者恐怕不多,更多人一定是从西方的话语系统展开,这是目前的现况。“德”是什么?“德”讲的是本性啊。我们的政治希望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群、每一个家庭的本性都能好好生长,是要共生共长共存共荣。如果以这样的方式去思考,这个世界可能会大不一样。以这种方式去理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可能会比较准确。如果以西方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思维去理解“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显然是错误的嘛。这不是西方的全球化思考,而接近于“在地全球化”或“全球在地化”(Glocalisa-tion)的新概念,但也不尽相同。
当我们把传统话语的意含释放出来的时候,它本身就会发生变化。譬如,我们把传统服饰长袍马褂的元素释放出来,与西装融合,可能会出现新的可能。我们把中国古代的哲学话语释放出来,参与到与现代西方哲学话语的沟通对话之中,当然也会出现新的可能。朋友们,这预示着未来最重要的哲学家将会是你们。但如果不读西方的东西,只是固守传统的话语,当然不行;如果只读西方的东西,而受到西方传统的彻底宰制,当然也不行。思想的融通,我们最后会碰到“存在与价值的和合性”、“存在与思维的一致性”的根本问题。
儒道佛三教都是觉性的宗教,不是信靠某一个超越的、唯一的、绝对的人格神的宗教。不同的宗教之间如何实现包容?何以在中国境内的伊斯兰教能够和儒教有某种融通而形成所谓的“回儒”?你到云南、贵州、青海可能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地清真寺的对联有宋明理学“天命性道”的思想和“一体之仁”的思想包含于其中。伊斯兰教中有苏菲一派可以和儒学相融通,这就是所谓的宗教的交谈和对话。其实儒道佛三教早就有很多交谈和融合。
我们有五十六个民族,语种一定超过一百种,如果用拼音把这些汉语的语种统统记录下来,那么将会形成一百种以上的文字。我们用符号去记录事物,去准确地掌握它,重要的根本不在于符号,而是回到存在本身。图像性的文字的表意方式和以语音为中心的逻辑表意方式有非常大的不同。以前读顾炎武,听说他读书是十行具下。我和朋友研究十行具下如何可能。第一,十行具下一定是竖排不是横排;第二,字不能太小,因为字很多的话,那就很困难;第三,他对这些东西熟悉到了一定程度。这真的是可能的,因为我们的文字是意象的串集,不是逻辑分析的构造。
《老子》讲“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男女如何平权,最重要的怎样可以构成和合整体的平权,而不是斗争意义上的平权,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女权运动是必要的,但是女权运动之后需要真正的女性主义运动,因为女权运动不能够取代女性主义运动。新一波的女性主义运动,有别于女权运动,他强调应该回到真正生命本身去重视,这不仅仅是权利的问题,还有更深层的问题。
我们的人文不是西方近现代意义上的humanism,不是人类中心的人文,不是理智中心的人文,不是从“我思故我在”立定一个思维之我当成存在之我的人文,而是通天地人三才的人文。“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这是程明道的诗。“有形外”不是在太空之外,分别之外,而是有形背后之无形。我们的“思”也不只是西方意义上的thinking。
我们现在被西方汉学家教导对这些东西应当如何理解,这很奇怪呀!西方汉学家也有很不错的,但多数没有真正进到中国文明的深层之中。我们常认为世界学术屋脊是哈佛大学,哈佛大学所讲的中国哲学绝对不可能比我的老师牟宗三先生讲得还好。只有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有深层的理解,我们才能立住对比项。从“存有连续观”和“存有断裂观”的向度进行对比,从天人、物我、人己三个向度进行对比。这些对比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去较量,而是要去融通。
(本文首发于2018年2月22日《南方周末》)
关联阅读:9月·武汉丨第三届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期待您的亲临见证
声明:“生命与国学”为东方生命研究院专属头条号,旨在继往开来探究古今圣学,开拓创新奠基生命文明。
凡本平台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平台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