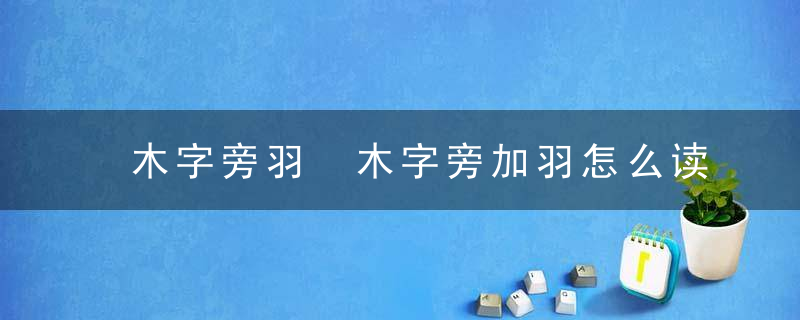飞鸟离去后

女儿去世后,母亲胡蝶尽量不再去高的地方。她的身材属于丰腴的那一类,眉宇间尚存着生意人的凌厉。现在,她给人感觉轻飘飘的,似乎身体中某种坚硬的东西消失了,在那个楼顶随女儿一同“飞”走了。
但这个冬日的早晨,她爬到浙江嘉兴的西山顶上,想用残存的重量拽住身边这个比自己高半头的男孩。
他们面前是一座六层高的深棕色木质阁楼,飞檐峭立直指天空,张临川执意要去顶上看看。他23岁,患躁郁症至少五年。胡蝶假意热络,紧贴在男孩身边,一路挽着,“其实我是一直抓着他”——她怕稍一松手,张临川就像女儿那样,一跃而下。
他们相识于一个网上“约死群”,这是初次见面的第三天。几天前,张临川网购了十斤炭,准备自杀。胡蝶骗他,自己有精神分裂症,也想死。
2017年夏天,胡蝶未成年的女儿在学校坠楼身亡。此前,她没有发现任何征兆。“那时候我真的都想死了。”为了寻找女儿离去的原因,胡蝶潜入“约死群”卧底。
“约死群”大量隐匿在社交网络的暗处,有轻生念头的年轻人在里面相约自杀。和胡蝶一起卧底的还有另外七个类似遭遇的失独母亲。
她们来自全国八个不同的省市,彼此未曾谋面,刚认识时,都失去孩子不久,最长的一年多,最短的不过一个月。她们的微信群名充满诗意,寓意为鸟儿飞走后的天空——她们说,自己的孩子都是“飞走的”。
“失去孩子实在太痛苦了,不希望再有人经受这种痛苦,能救一个是一个。”胡蝶淡淡地对《后窗》说,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值得书写的事。
被解救的自杀者大部分患有抑郁症。据2017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中国有5400多万抑郁症患者,占人口的4.2%,他们大量隐藏在暗处,连最亲密的人都无法察觉或理解。其中每年至少有数十万在自杀前徘徊。同时,三十余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带来了上百万失独家庭。这八位母亲是被双重悲剧击中的少数个体。
伤痛尚未远去,拯救别人孩子的同时,她们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孩子,心中难以愈合的疤痕被一次次掀开。“有时候(和想自杀的孩子)聊完我都想从楼上跳下去,觉得没有了解孩子。如果早就知道,不会让他们孤独绝望地走掉。”一位妈妈说。
“我明天要上路了”
炭寄到了。
下午4点,胡蝶收到微信,发信人是张临川的母亲。
张临川家位于上海周边,离县城5公里远的一幢三层小楼。一楼的卫生间狭小、密闭,母亲猜测,儿子准备等他们熟睡后,在那里燃炭自尽。
她问胡蝶,该怎么处理。
“你假装不知道,就跟他说:‘寄来的是什么东西啊?脏啊脏死了。你是想给爷爷烤火的吧?’”胡蝶让她把炭直接扔掉。
此时,张临川就在胡蝶身边,刚刚安顿下来。几小时前,他们开车回嘉兴,路上,张临川试图打开飞驰的汽车车门。
一个多月前,妈妈们在约死群里发现了张临川,那阵子,他的QQ头像频繁地在闪现,话语颓废,鼓动别人自杀,甚至约死,“咱们一块儿自杀吧,什么时候一起去烧炭?”
约死群是一种隐秘的网络组织,无法直接搜索到,群名灰色,充满隐喻——“通往另一个世界”“黑色星期六”“忘川河中恨千年”,且需要内部推荐才能加入。每个群通常有一两百人,成员大多二十来岁。每到夜晚,这些年轻人开始在群里出没,发送自杀指南、约人一起自杀、直播自杀。烧炭、割腕、跳楼是最常见的选择。一个女孩几乎在每个群里都说:“准备好了没有,什么时候上路?”
山东单亲妈妈雪珍最早发现约死群。2017年,她的儿子在家中烧炭自杀,去世时23岁。置办后事时,雪珍没舍得把儿子的手机放进骨灰盒,十几天后,她打开手机,意外发现儿子加入了一个名为“忘川河中恨千年”的QQ群,儿子的昵称是“死亡之翼”。
雪珍的儿子15岁患抑郁症,但家人以为他青春期叛逆,“隔一阵儿就闹腾,我们也很生气,电脑都要给他砸了。”有一次,正在上班的雪珍收到儿子发来的一张照片。照片中,邻居家的猫,头被剁了下来。
儿子发病频繁后,开始反复住院,药物影响了思维能力,他卖过保险、做过保安,送过快递,但没有超过一个月的。儿子的朋友告诉雪珍,自杀前几天,儿子面试被拒,雪珍推测那是最后一根稻草。她后来发现,那几天,儿子把药藏起来,没有吃。
为了寻找儿子自杀的秘密,雪珍开始翻阅群里的聊天内容,渐渐感到毛骨悚然——群里的人轻松地谈论死亡,相约自杀,鼓动自杀,还有一些割腕、烧炭的图片,“太恐怖了!”
她用儿子的账号在群里说:“你们都是混蛋!干嘛要做傻事,想不开!”没有人吱声。有人小窗问她怎么了,她没有答话。
雪珍把约死群的截图发到失独家长微信群里,大家很震惊,几个妈妈也要求加入。一位妈妈进群后看了两秒钟自杀直播,血淋淋的场面,让她“窒息得想呕吐”。
“这个群对人有一种影响力,在他们死的时候,感觉是一个很轻巧的事,从来没想过结果。”雪珍说。
聊天记录显示,儿子生前和群里一个吉林男孩“约过”。
“我爸妈白天不在家,趁他们上班,我就在家走。”儿子说。
“那你妈妈以后再也没法住这个房子了,去宾馆自杀。”男孩回他。
“这样的话对人家(宾馆)影响不好。”儿子说。
看到这里,雪珍感到心酸,“其实都不是坏孩子,还会为爹娘考虑。”
儿子的聊天记录。受访者供图
11月的一天,儿子给吉林男孩发了最后一条消息:“好好活着,不想念不悲凉。”当天,他在家里烧炭自杀。中午,雪珍回家,在小房间里发现趴在地上、僵直不动的儿子。
儿子去世一个月后,雪珍陆续把7位妈妈拉进约死群,最初她们是要体验孩子的感受,寻找自杀的答案,后来出于母性的本能,想拽住那些轻生的年轻人。为了方便救人,她们单独建了微信群。除此之外,失独群里还有二十多位妈妈间接参与了救援。
她们分工合作,扮演不同角色。有的假装求死者,有的扮演同学,有的就是阿姨。胡蝶的角色是求死者,她说自己有精分,“你到我家里来一块儿死,把电话给我”,拿到联系方式后,再进一步解救。
她们主动在约死群里寻找目标,先救群里准备自杀的孩子。张临川就是其中之一。发现男孩地址的,是周晴妈妈。
58岁的周晴生活在中部某个省份。她是几个妈妈里最后进入约死群的。群里鱼龙混杂,张临川的谈吐显得素质较高,吸引了她们注意。
因为哭得太多,周晴眼睛不好,看不清屏幕,只能用语音跟张临川聊天。一天,张临川在约死群里发了一张淘宝订单截图,上面是他网购十斤炭的记录。
“我明天要上路了”,他说。
动画片《自杀专卖店》。图片来源网络
随时随处都在思考死亡
周晴吓坏了,立刻把截图发到群里,想办法解救。唯一的线索只有截图里的收货地址。姐妹们在网上搜出男孩家所在居委会的电话,但一直没人接听。
她们需要赶在快递之前找到男孩的父母。第二天中午十一点半,离男孩家最近的胡蝶和丈夫开车从嘉兴出发——不能再等了,他们要亲自去一趟。
到达上海已是下午3点半,胡蝶按照地址,在一条小河边找到男孩家。男孩妈妈出来洗菜时,她赶紧上前询问,“是张临川的妈妈吗?”胡蝶把她拉到远一点的路边,低声说:“你儿子要烧炭自杀”。
“怎么可能?不可能啊!”
回忆起这个场景,胡蝶轻叹一声,“要是当初,我女儿死前几天有人要是这么告诉我的话,我是死都不会信。”
胡蝶把事情经过告诉女人,还把淘宝截图找了出来,对方才确信。
第二天早上7点,张临川的父母来到宾馆,敲开胡蝶夫妇的房门,两对父母聊了两个小时。张临川的母亲说,平日他们忙于工作与儿子很少沟通,儿子发病厉害时会打她,甚至说过要杀了她。父亲说,儿子确实说过“不想活了,去上吊好了”,他当时还说,“那你去吊啊”——他觉得儿子不敢。胡蝶感觉,张临川父母对儿子想寻死的事仍没有太在意。
她用自己的经历劝说张临川的母亲,不要被孩子的表面迷惑,抑郁症的孩子有可能一面在笑,一面又很痛苦。“像我女儿就是特别乖,什么都听你的”,胡蝶的女儿从来不用她操心,学习优异,乖巧懂事。一旦有让母亲失望的地方,会特别内疚。“太懂事的孩子内心压抑很大”,胡蝶的语气中难掩痛苦。
放心不下,胡蝶提出,想去看一眼张临川。来上海前,她试探着说,想去上海看病治疗精分,请他推荐个医院,顺便来看他,“我不可能见人”,张临川很排斥。
再次来到三层小楼门前,一个白白胖胖、戴着眼镜的男孩从屋里走出来,“我第一眼见他,感觉他蛮可怜的,眼睛里面很迟钝,没有表情。”张临川看起来有点难为情,“阿姨,你怎么来了?”男孩母亲假装不认识她,招呼他们去院子里晒太阳。
太阳底下,男孩不敢直视胡蝶,说自己想寻死。胡蝶告诉他,“你这样想是不对的,爸妈这个年纪要是小孩没了是很不容易的。”男孩没有理会,说自己没有未来。
胡蝶决定带他回嘉兴散散心。第一天,他们在月河街上吃嘉兴肉粽,“他高兴得要死,一直说‘好吃好吃好吃’,那么大的粽子,吃了两个”。之后他们又去了南湖,男孩的脸上渐渐有了笑意。胡蝶还带他去健身房,陪他剪头发,也给他妈妈发了张照片,他妈妈说,“人精神多了”。
嘉兴南湖边,胡蝶搂着男孩拍了张照片,两人都难得地笑了。但她感觉到,男孩寻死的心从未停止。在湖边走着,张临川会突然问:“湖水有多深”,还问“嘉兴最高的建筑是什么”。他对胡蝶说:“阿姨我是想死,但是我不敢,怕痛。”为防止意外发生,晚上,胡蝶的丈夫陪男孩一起睡。
“我感觉想死的人,他可能随时随处都在思考(死亡)”,胡蝶感到后怕。
嘉兴西山。图片来源网络
尽人事,知天命
一个月后,另一场紧急救援发生在三千公里外的大西北。
王进年近30,大专毕业,失业在家,爱好写作,已尝试点过两回炭,至少五个妈妈先后用QQ与他聊天,有时候聊到晚上两三点。
一天,王进突然跟周晴说:“阿姨,感谢你一路陪伴我,但是我还是要去死。”周晴吓了一跳。
为了拖延时间,妈妈们给王进发了60元红包,王进说要拿这个钱去洗澡,他已经好多天都没有洗澡了。
距离最近的妈妈李芸决定第二天早上就去找他。
王进的家位于一片棚户区内,那时正是四九,温度接近零下30度,积雪厚的地方得有半米深,李芸用了四个小时才赶到,但地址终止在一条巷口。
她给王进打电话,一直关机,“坏了!”她有种不好的预感。群里慌乱起来,有人猜测,王进昨天说去洗澡,是不是准备上路?
李芸在巷子附近的小店挨家询问有没有人认识王进。天冷地滑,太阳落山了。她跑到一辆巡逻车外,吐着热气,请求民警帮忙,几乎要哭出来。
“我就想到我的孩子在那个时候有多无助。”
群里的姐妹们也开始打电话报警,她们也感同身受——“如果我们自己的孩子有这样的机会,也是能救下来的”。但警方拒绝的理由很多,包括不是当地的不能执行。妈妈们很失望。
两小时后,李芸终于打动了巡逻车里一位年轻警官,通过王进的照片确认了他的身份,并确保他平安。
一周后,在民警带领下,李芸见到王进。
当时是下午3点多,但一进楼道门,什么都看不见,楼梯不到一米宽,又窄又陡。
王进的房间不到十平米大,墙上很暗,上面潦草地写着“尽力了,一定要走……”辞职后,王进就搬到这个屋子,专门从事写作,但作品一个都没发表。
李芸邀请王进和警官一起去餐馆吃了顿饭。王进走路佝偻着,眼睛里没神,脸藏在毛衣和羽绒服的帽子里,吃饭都不曾摘下。
“我的心老了,就像老树的根”,饭桌上,王进对李芸说。一直在出租屋吃泡面的他,那天要了一盘香菇青菜。
他们在餐馆里聊了三个多小时,王进妈妈也在,“但根本劝不动,他发表起自己的观点滔滔不绝,拒绝就医,拒绝吃药”,李芸回忆。
劝说寻死者的过程并不愉快,“跟着急,钻牛角尖”。有人得知她们的身份后还会爆粗,“你怎么不去死啊?”“在群里放什么屁?”
胡蝶曾和一个孩子聊起跳楼的事,劝完以后失声痛哭。
雪珍妈妈用儿子的QQ,劝解有轻生念头的年轻人。受访者供图
偶尔也有让人宽慰的时刻。胡蝶救助过一个辽宁孩子。“男孩”30岁,胡蝶43岁,“他叫我老妈。”他对胡蝶说:“阿姨你真好,你一定要想开点”“只要我不死,一定养你老,当你的孩子。”
不止一个孩子对伪装成求死者的妈妈说:“阿姨,你有家庭有孩子是有希望的,还是好好活吧。”
三个月里,妈妈们通过报警,在珠海救下一人、在北方某个城市救下两人、在上海救下两人,其中有男有女,多是二十几岁。
也有没救下来的。
有一次,两个男孩在徐州一家宾馆里直播烧炭,妈妈们只有他们的QQ号,没有地址,警察找到时,他们已经走了。
那段直播自杀的视频至今还停留在胡蝶的脑海中:他们在宾馆的洗手间里,用胶布把门封好,炭放在盆里点燃,视频里没有人出现,也没有人说话,只有炭在燃烧。后来她才知道,约死的原本是三个人,其中一个中途后悔了,“你说他走了要是立马报警就好了,偏偏到第二天才报警”。
“眼睁睁看着两条生命流走,无力感一次一次的”,周晴说,声音里透着疲惫。
因为出了事,这个约死群很快被封。但没过多久,妈妈们又被群主拉进另一个新的约死群里。
那天的饭桌上,王进用轻松羡慕的语气描述了和视频里一样的场景,“把门封上,盆里面放上炭,倒上酒精,点上火,噌地一下火着了……”他还想说下去,被李芸打断,“你不要说了,太恐怖了!”
分别时,李芸主动说,“来,跟阿姨拥抱一下”。王进放下手里的东西,上前给了李芸一个正式的拥抱,在她耳边说,“阿姨,我非常感谢你”。
李芸当即有一层冰冷的感觉,那是告别—— “我还是要走”。
“哎,我当时就想,那只能尽人事,知天命。”
心里一次次在流血
从嘉兴回来后,张临川的母亲开始花更多的精力照看儿子,男孩渐渐参与到家庭生活中,前段时间奶奶住院,他也去医院看望。前几天,张临川的父亲发给胡蝶一张照片,张临川和妈妈正在健身器械上锻炼。对父母和胡蝶,他不再提自杀了。
缺乏至亲的理解,让孩子在堕入黑暗后找不到出口。无论胡蝶,周晴,还是雪珍,都是在救援中才明白这一点。
王进已经很久不和妈妈联系。他恨母亲,自己每天关在屋子里吃方便面,却从没得到母亲的关心。
王进的母亲年过五十岁,是个本分勤劳的人,普通柜员,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一开始她不相信儿子生病了,也无法理解抑郁症,认为他懒惰,逃避社会,“作”。
在李芸的劝说下,王进母亲终于带儿子去了一趟医院。医院诊断为,“重度抑郁症”。王进母亲在电话里对李芸哭了一场,最终接受了她们的建议,给他更多的爱和关注。如今,王进开始回父母家吃饭,主动和阿姨们聊天,邀请她们来玩。
2月7日,王进妈妈带来一个好消息,儿子不再提自杀了,并决定年后去内地打工,开始新生活。
“直到这天我们才知道,孩子救出来了。”李芸长舒一口气。
但周晴担心,王进并没有表现得那么开朗,抑郁症患者的负面情绪会时常反复。
她很矛盾。一方面放不下这些孩子,跟他们有一种深刻的感情,彼此理解,无法言说;又不想再多联系,她们救了别人的孩子,但是自己的孩子却走了。
救援过程中,很多妈妈出现了抑郁症状,失眠、消沉、崩溃。
“跟他们聊的过程,我自己也是一次次心里面在流血,因为必须要把自己的情况感同身受地跟他们说,但是每次说就是在撕开自己的伤口,很疼。”周晴有几次跟约死群的孩子聊到夜里两三点钟,之后通宵失眠,安眠药从一片加到两片,“身体和精神都受到摧残”。
做的越多心情越差,一位北京妈妈总结,“因为接触的都是负面的心情,大范围地谈论死亡,谈话很压抑。”
预想中的自我救赎并没有来到,反而带来更深的自责。“做父母的直到当时孩子走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感觉很愧疚”。
周晴和四个人深入地聊过。有些谈话片段让她觉得更理解自己的孩子,理解抑郁症患者无法和亲人沟通、无法解脱的痛苦。她把这些记录保存下来。
“我无时不刻、分分秒秒,除了睡着,整个心胸都充满对孩子的怀念和爱。”
近年来,很多媒体关注过失独家庭,图为《南都周刊》2012年的报道。
无法原谅自己
春节前夕,“姐妹群”里开始商量怎么躲过热闹的人群,同时退出约死群。胡蝶回了老家,在山水间消遣;李芸和丈夫去了外地,等春节热乎劲过去了才回家,“不想听见鞭炮声,他人欢乐独我痛苦”。
除了偶尔和王进联系,周晴已经不再和任何孩子聊天。有的孩子叫过她“妈妈”,但周晴委婉地拒绝了。心里的痛苦太多,她无法再承受这样的重担。
对于她们来说,“飞”走的那个孩子,谁也无法替代。
北京妈妈方希想过再要一个孩子,但她已经丧失生育能力,“哪怕要生孩子,也是为了纪念我们的上一个孩子,但我们又觉得上一个孩子是无可替代的,领养我是不能接受的”,她平静地吐露这段话,最后声音像被什么吞掉,沉默下来。
女儿去世后,方希改变了信仰。“我以前是信佛的,但是孩子死了之后我就不信了,在这些传统的宗教里面,包括基督教,自杀以后,都是要下地狱的,这个我无法接受。”
出于保护自己,她也不打算再参与救援了。
在失独父母群里,妈妈们互相打气,发正能量的话,只有在姐妹群里,她们才会一起哭泣。她们是“同命相怜、永远走下去的姐妹”,“是彼此理解的最后的家园。”
“失去孩子的痛苦,真的是没有办法描述,以前觉得孩子可以陪你一辈子,可以慢慢地去爱他,谁知道突然就没了……什么都没了”,胡蝶说。
女儿离开半年多,胡蝶多数时间都在床上躺着,晚上睡不着,“我现在也还是迷茫的,以前很喜欢做菜,现在就随便煮个面,或者稀饭年糕吃吃。对未来没有规划。”女儿的日记已被丈夫删去,无论何时,胡蝶只要一看就流泪。
夜深人静,想起女儿,她总忍不住问:“你说这件事跟父母有关系吗?”
她也考虑过要个孩子,但很快打消了念头,她没有心力应付,医生也提示了高龄生育的风险。“但是,没有孩子日子又很难过”。
熬过后半生、平静地生活,为父母活下去,这是她们仅存的愿望。
正月里,胡蝶在老家屋里吃饭时,一只蝴蝶突然飞进来,落在桌子上。还有一次,在车里,一只橙黄色的蝴蝶飞进窗子,在她身边停留了很久,迟迟没有飞走。胡蝶觉得,那就是女儿的化身,她回来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作者简介